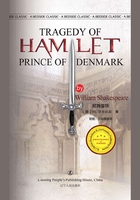献给我六十岁的哥哥
他在讲话,我却在思考那些由人生演变成的故事,以及由故事演变成的人生。
——内森·祖克曼,《反生活》
亲爱的祖克曼:
你知道,在过去,相关事实始终是我笔记本中的随手记录,也是我小说创作的必由之路。对我来说,或对大多数小说家来说,每一个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事件,无不起源于具体的事实,而与哲学、意识形态、抽象的东西无关。然而,出乎自己的意料,我现在似乎要写一本绝对是本末倒置的书。要拿起冥思苦想之后定了型的东西,榨干其中添加的水分,再让体验重新回到虚构前的原始真实。为什么?为了证明我这个自传写作者,明显不同于人们所想象的?为了证明我从生活中汲取的信息,即我小说所呈现的,是残缺不全的?如真是这样,我不会自找麻烦;因为细心的读者如有足够兴趣,满可自己找到答案。没人吁求这样一本书,也没人下令,更没人上门来向罗斯索取。假如真有这样的命令,早在三十年前就已颁布了;其时,我的某些犹太长老质问,究竟是哪个小子写出这样的文章。
恰恰相反,它的诞生似乎出于另类的必要,给你看这份手稿——就是否应该付梓征求你的意见——就是促使自己作出解释,到底是什么导致我以这样的散文体来毫无掩饰地袒露自己。迄今为止,除了其他的用途,我过往的经历一直被当作转型和巧妙解说自己人生的基础。我在非想象的世界中,基本上从不向严肃的听众赤裸裸地宣扬自己的私人生活(或扮演一名强加于人的电视人物),时至今日却在众人面前呈现转型之前的自我,那是为什么?自我暴露的钟摆两端,一端是梅勒型的积极暴露,另一端是塞林格型的与世隔绝,我占的位置居中。在公共场合中,我既抵制无端的窥探或自我梳妆,又不在保密和隔离上故作神秘。事到如今,为何又追求起履历的知名度?况且,我受到的教育让我确信,小说的独立现实才是唯一重要的,作家应该躲在幕后。
好吧,让我开始回答——此时此地,我计划中的自我暴露,其主要对象还是我自己。你已年过五十岁,亟需面对自己;数月前,它就发生在我身上。其时,我身陷无奈的混乱,再也无法弄懂曾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为何从事如此行当?为何选择如此居所?为何与如此人士分享生活?我的办公桌已变成一个可怕且陌生的所在。我生命的早期曾有过类似的危机,当老方法不再奏效——无论是针对大家都要面对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还是专业性的写作问题——我就会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去投入人生的重建。但这次不同,我开始相信自己已无法东山再起,非但觉察不到重塑的可能,反而觉得正在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我在叙述一次精神崩溃,没有必要在此详述细节,但我会告诉你,那是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即我十年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原来的一个小手术演变成了一场持久的体力考验,遂又引发极度的抑郁,在情绪和精神上将我推到崩溃的边缘。在崩溃后的冥想期间,随着疾病的缓解,思路重返清晰,我开始不由自主地聚集几乎所有的清醒时辰,来关注自己身处数十年的世界——回忆自己的出身和现状的起源。宛如你丢失了什么东西,就会说,“好吧,让我们回忆一下已发生的每一步骤。我走进屋子,脱掉衣服,来到厨房”等等。为了找回丢失的,不得不返回开初的那一瞬间。但我找不到那一瞬间,只找到一系列的瞬间,好比一部包含多种起源的历史。那就是我现在记录下的,为了重新占有人生。正如我所说的,以前我只是在寻找可获转型的,从未像现在这样,竟在测绘自己人生的点点滴滴。为了返回先前的生活,找回活力,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我开始让经历回复到它转型之前。
也许我想蜕变成的,甚至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在上大学之前的那个小男孩,或是在操场上与邻里伙伴玩耍的那个小男孩——即返回原点。几近崩溃的我,又满怀感激地投入普通生活,那是一段最平淡无奇的生活。我猜,我是想返回一个再出发的起点,一个较为普通的罗斯的起点。同时,我又想重历那些使人定型的遭遇,回味那些最初的斗争,走进那个斗志昂扬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我想象力狂躁的一面狂飙突起,我因此而变成自己的作家。我回到原点,并不想寻觅素材,只是为了出发,再出发——燃料已经耗尽,现在回来是为了嗜饮有魔力的血液。你祖克曼,在《反生活》中通过英国妻子获得新生;你的兄弟亨利,与西岸激进主义者一起在以色列追求新生。你俩在这同一本书中都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理所当然的,我像你们一样也应获得新的机遇。我忙于写作时,可能看不清自己到底要什么,现在则恍然大悟。这份手稿体现了我的反生活,是我所有小说的解药和答案,有关你的小说则是其中的高潮。如果说《反生活》可被理解为有关结构的小说,那么这份手稿便是一副光秃秃的骨架,即人生的结构,不带任何的小说成分。
事实上,那两部关于你的篇幅略长的小说,我已足足写了十多年,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对自己生活作进一步的虚构已让我颇感厌倦。我将一名与自己经历相仿的角色,软磨硬泡地引入这个世界;所不同的是,他魅力更大,经历更加活力四射,更加充满乐趣……在这段时间,我则很大程度上都是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与打字机做伴,毫无乐趣可言。我自己设定的规则——必须想象出某些情节,让它们发生在犹如我的投影或代理人身上;那些情节——既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不是从没发生,更不是绝不可能发生——已把我耗尽。如果说这份手稿传达了什么,那就是,我已筋疲力尽于面具、伪装、扭曲和谎言。
当然,即使没有几近崩溃以及由之而起的自我审视,此时此刻,我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挥动鞭子,操纵事实,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精彩感人。我颠覆,美化,重组,渲染有关的经历,使之转化为一种神话——三十年之后,即使处于最理想的情形之中,我似乎已经受够了。去神话化,实事求是,让身历的事实与陈述的事实并排陈列,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即使不是我唯一可做的事。此外,我自觉转型的能力和相关的想象力仍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几近崩溃的其余功能,也在直觉地告诉我,只保留作品中朴实无华的独特,是补救我损失的必由之路。它是我复原的手段和坚强起来的途径,甚至容不得我的自由选择。我需要尽可能多的澄清——去神话化,以帮助铲除我的病态。
这并不表示,我无须抗拒如此的冲动,即让不够戏剧化的东西戏剧化,让基本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让很少暗示的东西变得寓意深长——我如能硬下心肠,克服小说家的精神疲劳,还会联想到另一种诱惑,即一旦事实不引人注目,便索性抛弃这些事实。几近崩溃之前的几乎每一天,在我看来,有些事非做不可;现在要从中逃脱,总的来说,比我想象中的更为容易。一是采用非虚构的态度,既不引人注目,又不凶相毕露;二是给内心的火炉鼓风,设法从经历中冶炼出更多故事。两者相比,或许前者更能使我走近真情实感。我既不想争辩,有一种存在只能在小说中找到,在真实生活中却是不存在的;也不想争辩恰恰颠倒过来的情形。我只想简单指出,存在这样一本书,不含想象的愤怒,忠实于提炼出来的事实,就可以解读在小说中遭到混淆、夸大、扭曲的真谛,还可以击中相关的感情要害。
我承认,这封信中所用的“事实”二字只是它的理想形式,比它在标题中的意思更为单纯专一。很明显,事实从不自行走到你的身边,它的组合全靠你自身经历所养成的想象力。对过去的回忆并非对事实的回忆,而是对你想象中的事实的回忆。像我这样的小说家谈到,要展示“毫不掩饰”的自己,要描述“没有虚构的生活”,其中未免有天真的成分。我曾宣称,搜索事实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治疗过程;这招致了读者过分简单的理解,却不是我喜欢的初衷。你搜索过去,因为头脑中存有一定的疑问——哪些事件导致你产生这些具体的疑问。这并不表示,你在自传中让你的思想从属于事实;而是表示,你构建一系列故事,以一条颇有说服力的假设将相关事实串在一起,以揭示你个人履历的意义。我想,给这本书冠名为《事实》已引出这么多疑问,改之为《征求疑问》岂不更令人啼笑皆非。
最后一个看法与促使《事实》一书出版的苦衷有关;这之后,你便可不受干扰,继续你的阅读了。我不敢完全肯定,只在私下思忖,写出本书是否因为,我不仅疲于制造那些虚构的自我传奇,不仅视之为自己几近崩溃的自发治疗,而且把它当作一种慰藉,因为在我心中,母亲似乎死得莫名其妙——在一九八一年她七十七岁时,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激励,让自己鼓起勇气走近八十六岁的老父亲。他知道生命的尽头已在迫近自己的脸庞,犹如他用来刮胡子的镜子(不同的是,不管白天黑夜,在他眼前的死亡之镜是永不消失的)。尽管在别人眼中不甚明显,但我认为,母亲的过世在大家的潜意识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观察到,省吃俭用、卓有远虑的父亲都不愿作长期规划了。他虽然健康,但已龙钟老迈,因染上不治之症而心绪不宁。像其他身患绝症的人一样,老人知道关于死亡的一切,只是不知它前来叩门的时间。
我不知道,一名五十五岁男子对父母的渴望因自己的几近崩溃而获得爆发,能否成为这份手稿的罗塞塔石碑[1]。我也不知道,当本书叙述的事件发生时,我们大家都还在场,没人离世或濒临一去不复返的边缘,这算不算是一种安慰?尤其是现在,我仍在试图恢复自己的精神平衡。我更不知道,重回过去那一刻,是否让我颇获安慰?因为在当时,因父母过世而激起的悲伤是无法想象、出乎意料、毋庸讨论的;而自己的死亡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父母像是在小孩周围设立了一个保护圈。
我想,这差不多就是我写本书的全部理由。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我自己,为何还要让他人来阅读?尤其是我承认,他们已在其他地方获悉不少同样的信息,只是以不同的名义;尤其是我认为,一部分是由于这一次努力,我再一次与自己的目标珠联璧合,重新投入生活;尤其是本书似乎是我第一次在不知不觉中写成,听起来又像是二十五岁年轻人的声音,不像是专门叙述你行状的作者的口吻;尤其是本书出版后,会让我感到赤身露体,我并不特别希望如此抛头露面。
此外,还有暴露他人的问题。我在写作时向大家坦承自己的私密情感,因此愈感忸怩不安。我回过头去,修改了与我交往人士的真名实姓,以及几个可作识别的细节。这并不表示,我的修改可以保证完全的匿名(在他们的和我的朋友眼中,这些修改无济于事),但至少可提供点滴的保护,以躲避陌生人的骚扰。
除了这些给出版带来麻烦的考虑,我还有更大的疑问:这本书到底好在哪儿?不过,我在此无可奉告。因为对我来说,《事实》的意义比显而易见的更为深刻;还因为在我先前的创作中,你、波特诺伊、塔诺波尔、凯普什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保持坦率。
真诚的,
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