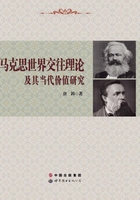【原文】
庄暴[1 ]见孟子,曰:“暴见于王[2 ],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3 ]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4 ]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5 ]?”
王变乎色[6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7 ]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8 ],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9 ]之音,举[10 ]疾首蹩頞[11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12 ]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13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14 ]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15 ]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16 ]矣!”
【注释】
[1]庄暴:齐宣王的宠臣,即下文提到的庄子。
[2]见于王:指被齐宣王召见,或者是孟子进宫朝见齐宣王。
[3]好乐:喜欢音乐。
[4]庶几:差不多。
[5]有诸:意为“有这回事吗”。
[6]变乎色:变了脸色。对于这句话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齐宣王认为喜欢音乐是不正经的事,因此面露愧色;二是齐宣王恼怒于庄暴将他好乐的事告诉了孟子,因此面露怒色。
[7]直:不过、仅仅。
[8]独乐乐:独自一人欣赏音乐的快乐。
[9]管龠:泛指乐器。管是吹奏的乐器,龠是管乐器之名。
[10]举:全、都。
[11]疾首蹙頞:指因头疼而皱眉头。
[12]极:穷困,这里引申为极致、极端。
[13]欣欣然:得意、高兴的样子。
[14]田猎:在野外打猎。
[15]旄:旗帜,在这里指仪仗。
[16]王:称王、统一天下。
【译文】
庄暴来见孟子,说道:“大王召我进宫,告诉我说他喜爱音乐,当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回答他。”
随后,庄暴问孟子道:“大王喜爱音乐,先生认为这件事怎么样呢?”
孟子道:“如果大王真的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恐怕就很有富国强兵的希望了!”
后来,孟子觐见齐宣王,问齐宣王道:“我听说大王曾经对庄暴说喜爱音乐,有这事吗?”
齐宣王听了,不禁脸色一变,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所喜爱的音乐,不是先王喜爱的那种清静典雅的音乐,我只是喜爱现在流行的世俗音乐罢了。”
孟子回答道:“如果大王非常喜爱音乐,那么大王的国家应该治理很不错了!这样看来,现在世俗的音乐和古代的高雅的音乐是一样的。”
齐宣王好奇地问道:“这其中又是什么道理呢?老先生能告诉我吗?”
于是,孟子问道:“大王觉得,独自一人欣赏音乐所获得的快乐,和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想了想,回答道:“和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又问道:“那么,和很少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与和很多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又回答道:“和很多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便说:“那就让我给大王讲讲关于欣赏音乐的道理吧。假如大王现在命人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萧奏乐的声音,个个愁眉苦脸,相互奔走道:‘大王如此喜爱音乐,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假如大王现在正在这里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是愁眉苦脸,相互奔走诉苦道:‘大王如此喜爱打猎,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
“大王只是喜爱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好的影响呢?这都是因为大王不能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假如大王现在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萧奏乐的声音,个个欢欣鼓舞,高兴地奔走相告道:‘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不会有什么疾病,否则他怎么有心情欣赏音乐呢?’假如大王现在去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纷纷欢欣鼓舞地议论说:‘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没有什么疾病,否则他就不会打猎了。’之所以产生这么好的影响,只是因为大王能够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如果大王能够和百姓们一起享受快乐,那么就可以统一天下了。”
【阐释】
在本章中,孟子着重阐述了“与民同乐”的问题。关于“与民同乐”的问题,在上一卷中孟子觐见梁惠王时已经谈到过。在这一章里,孟子又跟另一位国君——齐宣王说:无论是先王高雅的音乐,还是齐宣王喜欢的“流行的音乐”,只要能与民同乐,都是好事。
在孟子看来,夏桀、商纣只知道寻欢作乐,不顾百姓的疾苦,这是“独乐乐”,是错误的;相反,国君只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就可以在全天下百姓面前称王,才是真正的“与民同乐”。后来,孟子由“与民同乐”的思想出发,结合对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进一步提出了“仁政”思想,希望借助“仁政”的力量,实现“与民同乐”。
历史上,因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而闻名于世的士大夫,除了孟子,还有北宋的范仲淹,而且,比起孟子的快乐观,范仲淹的更具有超前意识。在《岳阳楼记》里,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这显然是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阐发而来的。自范仲淹以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已经代替了“与民同乐”的思想,称为最具忧乐意识的“与民同乐”。
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为“与民同乐”,但也是逐渐注入了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
【原文】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1 ],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2 ]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3 ]往焉,雉兔者[4 ]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5 ]?臣始至于境[6 ],问国之大禁[7 ],然后敢入。臣闻郊关[8 ]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9 ]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10 ]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注释】
[1]囿:蓄养禽兽的猎场。
[2]传:典籍文献。
[3]刍荛者:割草砍柴的人。刍,割草。荛,砍柴。
[4]雉兔者:指猎取野鸡和兔子的人。雉,野鸡。
[5]不亦宜乎:不也是应该的吗?
[6]境:边境。这里指齐国的国境。
[7]禁:指政府颁布的禁令。
[8]郊关:国都郊外的关口。
[9]麋:鹿的一种,也叫“四不像”。
[10]阱:陷阱,在这里指陷百姓于死地。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听说周文王有一个面积达七十里的狩猎场,这是真的吗?”
孟子回答道:“是真的,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又问道:“面积真有七十里见方那么大吗?”
孟子回答道:“是的,不过百姓还嫌它小!”
齐宣王听了,疑惑地说道:“可是,我的狩猎场的面积才四十里,百姓们都觉得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尽管周文王的狩猎场面积有七十里,但是如果百姓要砍柴割草,也可以去那里;如果百姓要抓鸟打猎,也可以去那里。因此,周文王的狩猎场可以算是与百姓共同分享的公共财富。如此一来,百姓们嫌它小,不就很合理了吗?
“我刚到达齐国的边境时,在打听清楚了贵国所有重要的禁令以后,才敢进入齐国境内。后来我听说,在都城的郊外有一片面积达四十里的狩猎场,大王规定说,如果有人杀死了那里的麋鹿,就如同杀死了人一样,要判重罪。这样一来,这个区区四十里见方的狩猎场,就像是大王设下的一个用来坑害百姓的陷阱,百姓能不觉得它很大吗?”
【阐释】
在这一章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即周文王方七十里的园林与齐宣王的方四十里的园林相比,哪个最小?结论是几乎是齐宣王的两倍的“周文王囿”小于齐宣王“方四十里的囿”。因为“民犹以为小”,因为周文王的园林是与民共有的。
由此可见,这一章的主旨也是讲“与民同乐”,不仅如此,还上升到了“与民同有”的高度。对于百姓而言,听音乐和享受欢乐都过于有些遥远和不切实际,只有共同享有森林、江河,能在森林和江河里任意砍柴和钓鱼,以供生活之用,这才是实际的。因此,百姓才担心周文王的园林太小了,以至于木不够砍,鱼不够钓。而齐宣王的园林却由于不准百姓进入,在百姓心中成了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自然越大越不好了。
有人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氏族部落制时代,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国君离百姓较近,有可能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财富不断增多,国君的权力逐渐变大,与百姓的距离也拉大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周初时,周文王可以与民同有园林,而数百年之后的齐宣王就做不到了。
不论是与民同乐还是与民同有,出发点都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和“保民”思想,哪个国君能够实行“仁政”,他就能够与民同乐;哪个国君能够拿出自己的园林与民同有,他就做到了“保民”。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1 ],文王事昆夷[2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3 ],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4 ]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5 ]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6 ]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7 ]。”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8 ]云:‘王赫[9 ]斯怒,爰[10 ]整其旅[11 ],以遏徂莒[12 ],以笃周祜[13 ],以对[14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15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16 ]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释】
[1]葛:即葛国,商为诸侯国时的邻国,故址在今河南省宁陵以北。
[2]昆夷:即混夷,周朝初年时我国西部的一个部落。
[3]獯鬻:又称猃狁,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