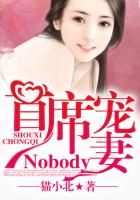家乡是温暖的,牧羊从北方回来的第一时间就有这样的感觉。列车到站已是翌日黄昏,踏出车厢的那一瞬,一股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已是深冬,却让他如沐春风。华灯初上,G市自不甘寂寞,如流苏般挂满行道树的彩灯,幻化出绚丽的城市生活。然而牧羊无心观看,这些强加于自然的外物在他的眼里不过是增添给行道树的累赘。
坐在前往H城的公车上,牧羊内心说不出的郁闷。他原本的计划是在G市小玩一番再慢慢回家,可惜他并没有时间,因为乘坐的列车不孚众望的晚点了。据说这是社会的一大不公平之处,乘客迟到哪怕一分钟就连列车影子都看不到,还得自己承担损失。火车晚点倒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一个小时不够,还可以再晚一个小时嘛!反正浪费的是乘客的时间。
出了G市,夜晚才真正属于黑暗,厚厚的云层透不过一丝光亮。车窗外的景色已经看不真切,远远的只依稀辨得出山脉的轮廓。牧羊心里的山还在前方,他是这条路上的归人,一圈一圈临近,车轮下的里程全是碾碎的流光。
午夜的H城是寂静的,至少在严冬里如此。牧羊背着一个书包,里面有一本书,一双鞋,一套换洗衣服。回家是不需要带太多东西的。
客运站外是Y广场,牧羊关于高中的很重要一部分记忆产生在这里,触景,伤情。他没有急着回家,反而是坐在了广场的石凳上,有点冷,至少屁股是这个感觉。以前坐在旁边的还有两个女孩,现在位置正空着,她们不会再来了,也没有人来补上。有人说怀旧是一种病,牧羊如今已然是一位患者。
“我回家了。”牧羊给陈玉玲打了电话。在他的心里,想要联系的第一个人其实是李一凡,可是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抑制着他的行动,无论思念多么强烈,他最终没有拨通李一凡的号码。
“嗯,我也回家了,可是我现在不在H城,过了年可能会去玩几天。”对面的声音很平淡,没有一丝涟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对于牧羊与陈玉玲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牧羊突然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高中时候可以整晚的聊天,说不完的话,现在竟似乎只能互道平安了!
“那,预祝你新年快乐!”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谈下去,也许打这个电话是错误的吧!
“谢谢,也祝你新年快乐!”陈玉玲回答道。
听到她说谢谢,牧羊就知道与她的关系,今后只是认识而已。他困惑,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曾经他们也有那么要好的时候,如今却只有两句话可说。我回家了,代表了现在,祝你快乐,代表了未来,从此不念过去!
回来第一天打的第一个电话就这么结束了,牧羊收起电话静坐在广场上,大脑空荡荡的,像一片寂静的旷野。
良久,旷野里的枯树与山峰与湖,都化作了桂树与高楼与广场。他开始四处扫视,看到报亭的时候突然笑了,于是似乎有月光照耀过来。
假期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做,作为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代——中的一个,不说全能那也得是多面手。牧羊还顾不上好好休息就被他哥叫去照顾他刚出生的小侄子。
看着怀里不足三天的婴儿,牧羊心里有种兴奋的感觉。这是特别的一天,今天小家伙的名字正式取定,叫做牧星河。当然这是牧天华取的名字,想想家里人,牧羊有时候搞不懂自己老爸怎么想的这些名字,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全有了,这就想着冲出地球了?
牧金鳞特地把牧羊叫来的原因是今天小家伙要去医院抽血。到了医院门口,牧金鳞看着满满的停车位发愁。现如今,车是平常的东西,反倒是停车位一位难求。门口保安没开门让他们开车进去,反倒是一个劲地撵他让他把车开走。牧羊坐在副驾驶听着就觉得来气,你一个保安还牛气哄哄的跟朝鲜主席似的,略微一想他就释然了——这里毕竟是医院。
终于找地方停了车,牧金鳞和牧羊抱着孩子去了妇产科的护士站。护士长让他们去打印孩子的出生证明,牧金鳞交代了牧羊几句后就出去了。
牧羊抱着孩子进了婴儿洗澡室,但来这可不是为了给小家伙洗澡,为的乃是给他抽足血。他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抽血,护士长提了一句,牧羊没记住,似乎和遗传病检查有关,医学术语实在太拗口了。他只知道单据是他签的,留的也是他的电话,到时候若是检查出孩子有问题,医院会打电话给他。当然,他是不希望接到医院电话的。
负责抽血的除护士长外还有三个小护士,但牧羊疑心她们三个是见习的,因为她们三个发挥的作用和牧羊差不多——看。不过彼此的态度倒是截然不同,牧羊觉得抽足血是对孩子的虐待,因为孩子喝的温开水少,扎了三次也没抽好。那几个小护士就不一样了,三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俨然围成了一堵墙。然而就在护士长扎第四针的时候,小家伙突然就是一泡尿。三个小护士躲避不及被淋了个正着,立刻惊叫着直往后退,拉着护士服抖个不停,拿出纸巾一个劲儿地擦拭。
牧羊险些让她们撞上,他让在一边,看着三个护士的举动,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只是对她们刚才那仿如小鬼见了钟馗似的尖叫,牧羊心里不免觉得可笑。
“叫什么呢,给孩子抽血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略有责备,却仍旧是很温柔的声音。
循着声音,牧羊的目光留在了护士长身上。此时,护士长前额的头发上正有液体滴下来,牧羊知道那是什么,护士长当然也知道,但她仍旧专心地给孩子抽血。瞥了一眼旁边的三个护士,牧羊心里升起一股敬佩之意。
抽血结束,护士长拿走了试纸,给了牧羊一张小纸条,告诉他一个月后可以登陆网站查询结果,如果有问题,医院也会给他打电话。牧羊接过纸条,躬身对她说谢谢。三个小护士回了护士站,牧羊抱着孩子在护士站外面的椅子上坐着。孩子不哭不闹,牧羊就这么看着他,突然想起来一首舒缓的英文歌,他唱了几分钟,小家伙就睡着了。
看着怀里的孩子,牧羊突然觉得心里很平静。这不是强大者对于弱小者的保护欲,如果非要说保护,现在提供保护的反而是牧星河。就这么看着他,牧羊内心的躁动就能渐渐平息。
“嘿,你肯定记不住今天吧!没关系,我帮你记,出生第三天就完成如此壮举,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抱着孩子的牧羊突然想起苏木来,那是苏木三岁的时候,每次牧羊一去他姐姐家,苏木就会跑过来,“歪歪,舅,歪歪。”然后拉着他去不远处的便利店。直到怀里再也抱不下,苏木这才会心满意足地跑过来让牧羊结账。亲眼看着牧羊付了钱,苏木就把商品都递给牧羊,喝着爽歪歪拉着牧羊的手一路走回来。
“抽过血了?”牧金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牧羊的身边,手里拿着一张纸。
“抽过了,一个月之后出来结果。”牧羊把护士长给的小纸条递给牧金鳞,压低声音回答道,“到时候上网看结果,我也给医院留了电话。”
听完牧羊的话,牧金鳞仔细看着纸条上的网站,片刻,他收起纸条说:“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二楼一趟。”
“嗯。”牧羊点头,他知道在医院里办事情的麻烦程度其实不亚于政府乃至银行。
待得牧金鳞上楼,牧羊又开始轻声哼起歌来。
“你是他爸爸吗?”突然有人问道。
牧羊抬头扫了一眼,面前站定一个小护士,稍微探着身子,有点婴儿肥,眼睛水汪汪的,至于别的特点就不太看得出来。这也难怪,除了护士服,他看得到的只有脸和鞋。虽然小护士挺可爱,但是那几分可爱还不足以抵消牧羊心里对医院的负面情绪,于是他面无表情地答道:“刚刚过去那个是他爸爸,我是他叔叔。”
“哦!这孩子睡得真香,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牧羊正欲说,心里又想她问了多半也记不住,理那么多作甚,况且名字是牧星河自己的,与她说什么,于是只回道,“你要不问问他。”
“诶,他叔叔来了。”小护士指着楼道那边说。
牧羊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牧金鳞正从那边走过来。随即开始冒黑线,他叔叔来了?他叔叔不是抱着他吗。牧羊本不欲分辩,只是又怕待会儿这护士闹出笑话来,倒可能让大哥取笑一番,想想还是说道:“那是他爸爸!”
“啊,我记错了。”小护士捏着手尴尬地说道。
“处理完了,走吗?”牧金鳞看了那小护士一眼,随即笑着冲着牧羊扬了扬手里的证明。
牧羊抱着孩子起身就走,到了医院门口,牧金鳞去取了车,一路开回家。
次日,牧星河在医院的壮举就已经传遍了牧陈两家。牧羊不曾料到的是这小子刚出生那天就已经对产科大夫做过同样的事了。由此可见,牧星河对于医院恐怕是不太喜欢的,否则怎么会一而再的这么对付那些医生护士呢?
随着牧星河的壮举一同传开的还有一则谣言——据说牧羊在医院看会儿孩子的时间还不忘挑逗小护士。对于这则传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作为散播者,抑或说造谣者,牧金鳞自然是表现得深信不疑,撒谎嘛,就是要连自己也骗住;他的妻子,牧羊的大嫂陈意涵对这事却是没有一个分明的态度,此事真也罢,假也罢,总还有人去探究,轮不到她来计较;牧天华却没给牧羊什么好脸色,他并非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同女孩子交往,但拈花惹草的事不能有,这是原则;与牧天华相反,顾宗芸却是笑得合不拢嘴,叮嘱牧羊把人带回家里来让她看看。牧羊听着也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尺水翻腾做了百丈波,自己即便不淹死,呛几口是免不了的,还是不开口为妙。
在家呆了几日,心中觉得甚是无聊,看书也看不进去,一个个字都像是长了脚在书页上漫无目的地乱跑般的,想要把它们组织成一篇文章,没有过硬的组织能力以及充足的耐心无异于痴人说梦。股票?牧羊不想看,从高二开始接触炒股到现在,尤其是上大学这半年,炒股炒到疯魔的时候闭上眼睛都能感觉到无数根线在脑子里钻来钻去。
这日突然来了兴趣,他起身套了一件外衣就踏出门去。不过显然,这不是一个好天气。层层叠叠的云从天边压过来,在冬天的H城,阳光是最为奢侈的享受。昨晚下了一场冻雨,叫人走起来提心吊胆,可是已经出了门,自然不能轻易就回去,否则又是居家冷鲜好几天。
到了路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见到一辆公交车正驶过来,牧羊毫不犹豫钻进车里,找了个空位坐下来。坐到终点站,然后再花一块钱坐回来。他本来打算坐回家,然而车开到Y广场的时候,不知哪来的力量将他赶了起来,直到赶下车才罢休。
Y广场还是以前那些人,只不过把夏装换作了冬装。秃了顶的老头子没跑步,现在已经太晚了,他正牵着孙子闲逛,戴着一顶皮帽子,牧羊险些没认出他来;打牌的仍旧堆在一起打牌,这一份坚持,也许终生不变,人类对于一些事总是有特别的毅力;摆地摊套金鱼的倒几乎绝迹了,零下二三度的气温里实在不适合做这等买卖,况且来年可还望着那一条条小鱼养肥自己哩;用枪打气球赢奖品的倒是多了,佳节将近,人们手里总显得比平日阔绰许多,花些钱打几个气球也就图一乐;不远处的小情侣正咬着耳朵窃窃私语,爱情的力量总是难以估量。Y广场,一切好像还都是那种慢条斯理的样子。可是不和谐的画面毕竟还是有的——一个匆匆忙忙的中年男人,脖子缩在宽大的黑色大衣里,面无表情地从广场上走过,眼睛与肩膀之间只看得见一圈圈围巾。
看着他消失在大楼拐角,牧羊的目光收回来,最终留在报刊亭。然而报刊亭没有营业,穿粉色衣服的女孩今天没有来,至于可口可乐,他已有许久不喝了。那是一桩回忆,对于牧羊来说,可口可乐在自己的生命里只活了不到两年。第一次喝是受李一凡的影响,和她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被逼着喝下去,最后一次喝是去跆拳道馆回来,从广场去李一凡家的五分钟里,开始与结束,全是一个人的身影。
“下雪了!”一声稚嫩的欢呼惊破了牧羊的遐思,他抬起头,看着飘然而落的雪。就像是变戏法般的,昂头看着像是灰尘,落到眼前时却突然变得那么皎洁。牧羊伸出手,雪花却不肯顺他的意,偏偏执拗地砸碎在他的袖子上。
见过了北国的雪的那种狂放不羁,牧羊愈发觉得H城这雪下得美,静静的像是女子着霓裳轻舞。这风亦不似北国的风般嘶号着奔腾而来,它尽管寒冷,但不碍温柔,一如仙袂飘飖。
对于同一样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
秃顶老头正拉着他那恋恋不舍的孙子回家去,为此恐怕要说些“感冒了要打针”之类的恐吓的话;打牌的抱怨了几句,不情不愿地挪到广场边超市的屋檐下;打完气球的都丢下枪走了,剩下摊主在那里盯着天,还有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气球;对于情侣来说,下雪是一件极富浪漫气息的事,围巾充当了一次红线,缠在了两人的脖颈上。这实在是妙极了,因为这彰显了他们共患难的决心。试想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另一个人无论如何是要如影随形的,至少脖子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
广场不是一个寂寞的地方,牧羊没有理由多待。他想回家去了,还要去照顾风信子,谁让他舍不得扔呢。打定了主意,拦了一辆出租车就走。路过汽车修理厂的时候,他坐到右边侧着身子看着外面第二层楼的一扇窗,那是路小希卧室的窗。好几年来,他经过时总要看那扇窗,这俨然成了习惯,可惜从来只看得见紧掩的窗帘。路小希早已举家搬去了别处,也许是G市,牧羊知道路小希考上了G市的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