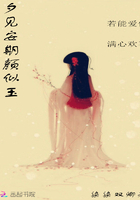一场仗的工夫,再回到平城皇宫,北魏的天下已经彻底换了旧主,崇光宫中先皇的痕迹在大火中灰飞烟灭,如今高台上坐着的皇帝神采奕奕、器宇轩昂,他的内心也因身份的变化而渐渐去除了父辈的影子,决心要成为人们心中新的王。
在这乱世里生活久了,自会将死生看做最容易的事。
“微臣慕容白曜,叩见太后、陛下,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常山随着他的节奏也跪了下去。
“爱卿平身,都起来,都起来。”拓跋弘因突然下旨即刻成婚,本就对他心怀愧疚,现在见到他乖顺地跪在眼前,不仅没有半句怨言,还帮他打赢了这场硬仗,心中更是不忍,只想着日后能尽自己所能好好补偿他。
冯太后沉默不语,今日看起来,她的脸色有些不好,身子斜倚在座椅一侧,双腿用白鹅绒毛毯盖着,赵黑弓腰站其身后一直为她揉着太阳穴。
她拜一拜手,赵黑就停住了动作,退到一旁站着,冯太后先是咳了几声,然后才慢慢睁眼看向台下站着的二人。
常山一进崇光宫的大门,心脏就提到了嗓子眼,她一直低垂着头,将视线定格在足前的一块石砖,尽力配合慕容白曜的动作。好在他做什么之前都会先照顾到她,她也就安心了许多,只是这位冯太后却又让她觉察到一丝不安。
“太后近日精神不济,总觉心口发闷,太医院瞧过后开的竟是些安神助眠的药,服了也有一阵子了,平日这个时辰,太后都在寝宫休息,这不,看在慕容爱卿为国立功,又带着公主登门拜见,才刚服下一剂提神醒脑的汤药,好来迎接你们。”拓跋弘打着圆场,笑着说道。
慕容白曜闻言,侧身对向太后,常山有些慌乱,也忙侧过身去,二人又再次下跪,“太后对微臣的爱戴,微臣感激不尽,来日定将报答您的无上恩德。”说完,紧跟着叩了三个响头。
冯太后看着他们二人,满意的一笑,她支起身子,想要坐直了说话。
“哎呦,太后,您小心着些。”赵黑像被摁了开关,突然动身去搀扶她。
“无碍。你们起来说话。”她坐直身子,稳了稳呼吸,慢慢说道:“曜儿,哀家从小看着你长大,早把你当做玉儿的亲哥哥,虽然中间分开了数年,可母子连心,哪能说断就断啊!”所有人都听出来她着重强调了“亲哥哥”三个字。拓跋弘瞥了眼慕容白曜,见他眼神不偏不移,直直看向冯太后,又想到这几日拓跋玉儿和母后愈发难以调和的关系,他无声地叹了口气,顺手拿起茶盏,抿了口茶。
常山在一旁默默地听着,虽然跟她没有什么关系,但也对冯太后口中的“玉儿”产生了几分好奇。
冯太后顾自说道:“做母亲的,哪个不盼着自己的儿子能早日成家立业,将来分开了,还能有个体己的人替哀家好好照顾你,曜儿,你可明白哀家的良苦用心?”
她越往下说,越逼问他,慕容白曜就越回想起自己这桩婚事的种种不对劲儿,常山身上的谜团又笼罩在他的眼前。
“微臣三生有幸,能由常山公主陪伴在侧,这是太后为微臣费心争取而来,微臣,明白。”
他说这话时,语调平淡压抑,相同的话如果放在马车里,一定不会是这种语气,现在倒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到底几时的他才是自己面前的他,常山陷入了沉思。
“抬起头来。”冯太后话音一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而投向她。
常山感觉到周身突然出现的几双眼睛,赶忙抬起头看向冯太后,刚对上她的双眼,就被她尖锐的视线吓得回避了眼神。
“嗯,早就听闻柔然四公主忠烈节义、为国献身,如今一见,还是个美人坯子。”
“太后谬赞了......”常山这才觉察出自己已经失去了他的保护,整个人紧张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冯太后和拓跋弘都看出来这个柔然公主有些问题,柔然和亲北魏的公主大有人在,他们见得也不少,印象中都是些尊贵高傲,还带着些难以驯服之意的野蛮女子,像她这样唯唯诺诺、少言寡语的还是头一个。
慕容白曜高昂着头,没有做声。
“常山同意和亲,远嫁而来,你夫君的功劳簿上也有你的名字,朕和太后都非常欢迎你,所以在我们面前,不用太过拘谨。”拓跋弘只当她是腼腆性子,出言宽慰。
还没等常山开口回应,冯太后接着拓跋弘的话茬继续说道:“既已嫁进北魏,你此生就是北魏的人,和柔然再无半点关系,日后该如何取舍,你应该清楚,不用哀家再费口舌了吧?”
拓跋弘刚调节好的气氛又因这句话给搞砸了。慕容白曜眼波微动,当年父亲投靠北魏时,是否也被告知了同类的话,父亲的心情会是怎样?他又会如何回答?只可惜,那时的他还太小,对父亲的遭遇根本不知情。他斜眼看向她的侧脸,见她因笑而鼓起的两腮渐渐退了回去。
“太后的意思,常山清楚。常山自幼受母亲教导,有些话,母亲一直让常山记在心上,常山本不解,但现在明白了。”
“什么话?说来听听。”
“母亲说,我们脚踩的这片土地,本是一体,人们封邦建国、各立为王,用士兵和城墙圈起一块块地,阻挡所谓的‘入侵者’,用炮火和鲜血抢占更多的土地,成功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失败的人就要面临骨肉分离,甚至是死生不复相见,每一个亡国的消失,新国的诞生,都是在画地为牢、自相残杀,最后的结局将会是你永远不知道坐在你身边的人到底是亲人,还是仇人。”
话已说完,宫内仍一片寂静,就连御前侍奉的几名女婢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不敢动身。
慕容白曜怔怔的看着她,他怎么也不会把眼前这个娇弱的女子和说出这番话的人联系到一起,听完后,他的大脑也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宫里除去那些个下等奴婢,只有赵黑是能在这种场面说上话的,他没什么学识,更不懂什么家国大义,能混到如今的位置,全靠审时度势、讨主人欢心,常山的这番话,他多半没听懂,但那几个刺耳的字眼还是让他警惕起来。他斜眼看了看冯太后,又看了看拓跋弘,二人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又或者是犹豫着不知该谁先说,他慢慢举起胳膊,颤抖着兰花指指向常山,声音不似以往那么洪亮的说道:
“大......大胆!你个......妖妇!你想......想干什么?”
“这座宫殿里的所有人,常山不敢断言除了陛下真正是北魏的子民以外,其余的人都本有自己所属的国家,但常山确定,”她重新看向冯太后,迎上她几近失去光泽的目光,高声说道,“太后,还有公爷,与常山都是一样的。”
慕容白曜的手已经向她伸去,他像经历了滔天巨浪,满面的震惊和害怕展露无疑,从头到脚都在说着“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呵......”一声冷笑从高台之上传来。
“予成可敦的教育方式真是令哀家涨了见识,教出来的女儿果然非同凡响,你说对吧?皇帝。”冯太后看向身旁的拓跋弘,神态自如的问道。
可拓跋弘仍沉浸在刚才那番话里,久久未缓过神。他十六岁就做了一国之主,即使凭借这场战役建立了几分威信又能如何,坐在这帝王宝座上,他还是没有安全感,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可以随意利用。那些熟悉的字词拼成的一句句闻所未闻的话,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有他自己知道。
“皇帝?”
“什么......”拓跋弘突然看向她,此时的神情里却不再是尊敬和顺从,而是恐惧和猜疑。
“微臣无能,没有管教好内妾,才使她口出妄言,扰了太后和陛下清净,微臣甘愿受罚,还请太后、陛下降罪。”慕容白曜说着,粗暴地拉下常山的衣袖,要她和他一同跪下。
常山知道自己说的这番话确实不合时宜,更是对太后和陛下的大不敬,她理应听慕容白曜的话,叩头请罪,她也照做了,但她跪的绝不是高台上的二人,而是身旁的他,不为别的,只因她了解他,所以爱他、疼他,即使他还不能理解她的心意,她也要拼死在他们面前说出这些,尽力去提醒他。
“常山不才,会错了母......可敦的意思,若有不当之处,恳求太后、陛下原谅,常山日后一定恪守北魏皇室妻子的本分,不敢逾越。”
“是罚还是不罚,皇帝该拿个意思了,哀家一介俗妇,可没有予成可敦的韬略,实在不懂这些个笃论高言。”冯太后撂下一句话,闭上了双眼,疲惫地倚回座椅一侧。
拓跋弘觉得心里累极了,他只想被人认可,却觉得肩上的重担愈发压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今日本该高兴的,朕不想毁了这气氛。在座的都是朕的亲人,朕权当是寻常百姓家唠闲话了......都起来吧。”
“谢太后、陛下。”慕容白曜心里松了口气,站起时还是把要扶她的手收回去了。
“哦,朕差点儿忘了,慕容爱卿头天上任尚书台,还未见过杨大人了吧?说起这个杨保年,朕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罢了,好歹也是老一辈功臣了,去看看吧。”
“微臣遵旨。”
“你也退下吧。”拓跋弘看向常山,想再说些客套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语气中也不自觉的透出一股揣摩不透的深意。
“常山告退。”
二人转身的一瞬间,常山抬眸看向慕容白曜,看到的却是冷冷的一撇和匆匆的背影。
“送夫人回府。”
“是,属下再来接您......”
“不用,看好夫人。”
郦范闻言,已看出些端倪,他偷偷看向常山,见她只是凝望着将军,许久才收回目光,苦笑着说道:“我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