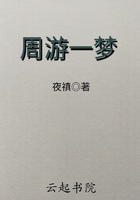昨夜的大雨甚是滂沱,冲洗着每一青砖青瓦,京城里的每一府邸都被着大雨洗了个净。这雨下得必有许多喜羡花木的夫人叹天,这好好的花儿,被这淋漓大雨给糟残咯。
而坐落在京城偏向南的大府邸里,里头传来阵阵好不畅快的呻吟,与男子沉重的低喘声,许久才停。“婵夕,楚然可有半点消息?”“老……老爷,臣妾……臣妾有有罪啊,楚然,楚然……那深山的每一个石缝臣妾都派人寻过了,今日已寻了五日,却连……”还未说完那被称为婵夕的女人身未着半缕的“扑通”一声跪在那男人身旁,泪声一同泣下。
本躺在那床上的男人见她满面纵横的如风中摇曳的梨花似的,心中本就不舍的怜心立刻便在心口旋浮,起身怜爱似的搂过跪在那被面上的女人,把她抱在怀里,“婵夕别伤了身心,若曾……寻不到,楚然,楚然那婚事……罢了罢了,如若再寻三日未果,我便顶报皇上,是老臣……老臣的过错啊”余钟说道,泪也流了下来。
在他想来,前五日一同去庙里祭拜,二女儿余楚然与马车一同滚落山底,待他急忙派人去寻时,除一个早已散架的马车,余楚然连个尸首都没有寻到,要他怎能相信楚然已经死了?
那天本就是为了她婚事之事去庙里求光,因皇帝允诺道,四皇子王妃之位一直善存,皇帝相中余钟二女儿余楚然,将余楚然许给他四皇子,余钟肯定认同,虽四皇子不受皇上的恩宠,但二女儿博得一个正妃之位定是不委屈了她,也给他这老脸上涨了光,本是喜事,却没想到竟会如此!那天本就下了毛毛细雨,山间之路滑,楚然所坐马车车轮无路纹,若要是在平地之上,尺许小径又算得什么,可那是青苔石坂,要滑得许多,他怎会如此的糊涂,从小便陪伴在自己身旁的闺女儿,就丧命于世间,叫他如何安得了心?
躺在他怀里的谭婵夕听他如此说道,目光厉然,神色显然的发冷,垂着眸子盯着那紫红梨为低料的地板,哼,那贱婢都寻了五日,没有任何的消息,想必早已被那山间野狼野狗吃了罢。
想到这儿,谭婵夕紧咬了一口牙,想必要出更一点好的法子,打破他对余楚然还活着的念头。
谭婵夕一副哭肿双眼的模样,从余钟的怀里抬起头来,手因哭泣而控不住的颤抖抚上余钟流满泪的脸,声音带着哭腔,“老爷……楚然一定会寻回来……定会寻回来……明日,明日我们便派人去那村庄底下去寻问……看那时常出入山林的山野农夫有没有瞧见楚然……定会寻回来……老爷好好的休息……可莫……莫伤了身子……”
谭婵夕说着说着,声音还哽咽了起来,话卡在喉咙说不出来,手用帕子擦过余钟那老脸上的泪痕,自己又说哭了起来。
想必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虽然老夫与你只有一面之缘,只是恰巧救了你一命,如今老夫已经深受剧毒,已没有多少时日……可老夫不甘啊,老夫门第被灭,门第上下几百号弟子,就这么死于帝王之手,老夫的仇还未报,怎么就这么甘了心?老夫也救你有了好几日,却没见你家人来寻你,可你衣着也不像……”说话的人突然停顿,猛的从胸中吐出黑红的血水。
爬满皱纹的脸此时苍白如絮毛一样,又断断续续的喃喃道:“你若……若听得见……记得,老夫把全身内力全授……授于你,可想必你……你也全身是伤,你承受的住,便……便可……走了出去,记得……若记得老夫说过的话,便把老夫的仇给报了,老夫……老夫在九泉之下,也算得是安息了……”
说完之后,那人巍巍颤颤的把一旁睡在草堆上的一女子扶了起来,那阴沉沉的光射进来,可见那女子还死沉于痛梦之中,没有半点清醒之色,只隐隐约约感受到鼻间呼吸的轻微起伏。
那老头儿用自己中过箭的,血肉模糊的手掌扶起她,将那女子打坐起来,便也坐到她的身后,将自己那深厚的功力一丝一缕的传送给那她。
几个时辰后,老头儿从口中泛出一大口的鲜红鲜血,本应早坚持不住,一想起自己妻儿和一门人被屠杀,意志强撑着,把那女子伤痕给愈好后,把自己的内功全传送给她。
那一口血喷向那泥糊的壁上,一抹浓浓的血腥味在空中里散发。呵,没想到老夫比你死得还要早些,这下做阴间之魂也不会放过你了,哈哈哈哈。
老头儿倒地,嘴角扯着奸暗的笑,鼻间断气死去。
可那女子嘴角有一淌血缓缓流下,倒向了另一边,鼻间缓缓的没了气息,七窍皆流下了血,因功力太过于深厚之多,在经脉上乱撺,全身上下的所有经脉全断,痛苦可想而知。
又怎么会是一名弱女子承受的住得的?
此时,山洞的外面,有一个与夜色融为一体的人影悄悄掠过,来到那女子和老头儿的身旁。
他从衣襟里摸出烛火点燃,照亮了半个山洞。
“王妃?”那男子的目光落在女子的惨白的脸颊上。此时爬满了整个脸颊的血已经干透,印在苍白的脸上,着实吓人,但依旧看得出五官。
男子试探的把手伸过去,探了探她的鼻息。
鼻尖还有微弱的气息传来。男子又伸手探了探倒在一旁的老头,此时老头早已全身冰凉。
“还是来晚了一步”男子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把倒在一旁的女子扶了起来,探了探经脉,突的脸色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