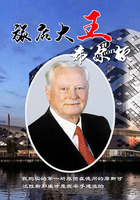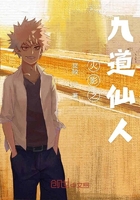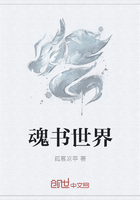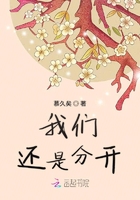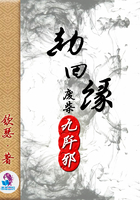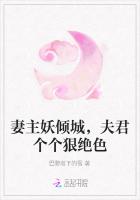由于多数暴政以压制少数人的权利的局面,不仅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且易酿成‘革命’或‘暴动’发生,盖少数人的意见及其利益,决不能完全置之不顾……” 森口先生曾留法多年,以他本人在观察法国议会选举状况时,发现就是采用的这种“比例代表法”;不过,森口先生也发现其中的弊端:“比例代表法”虽民主之至,却容易造成“小党林立”的态势,如果没有一个党派可顺利获得半数以上,势必就是一个“联合内阁”,这对于一届政府制定或贯彻其大政方针来说颇为不利,而且内部结构也不会稳定。森口先生撰文立说严谨精道,讲课时却不甚简洁明了,有其重复和罗嗦之嫌。尽管如此,雷震在法学部政治科毕业后,即申请进入“大学院”,仍是选择森口繁治先生作为自己的指导老师。
佐佐木博士讲授《行政法总论》和《行政法各论》,一生致力于行政法学和宪法学的研究。著有《日本行政法总论》、《日本行政法各论》、《警察法概论》等专著,仅《日本行政法总论》一书就在七百页以上,被时人称为“权威之作”。与森口先生不同,佐佐木先生授课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语言生动,大受学生们的欢迎,每次上课“几乎座无虚席”。虽然佐佐木博士有“总论”和“各论”两大册在手,却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循序渐进地解释其原理和原则,并尽量举例加以一一说明。每次开课,雷震总要抢得头排位置,“……我最佩服佐佐木老师的学问和风度,不仅好好的去听讲,且从不缺课,对于他的《日本行政法总论》一书,我仔细地读过好几遍。为使容易记忆和下次翻阅起见,在书本上用红墨水打了许多红线条,并在每页书头上写下了许多‘眉批’和‘注解’来表示个人的意见。” 抗日前夕,这本《日本行政法总论》被中央政法学校的教授刘百闵 借用不还,雷震因“舍不得自己的眉批和注解”,再三索要,刘竟不予搭理。
1933年,京都帝大爆发震惊全日本的“泷川教授事件”。
泷川幸辰先生是一位富有自由民主思想的青年教授。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学校军国主义化”教育,同时采取各种手段以取缔当时的“左倾思想”。所谓“左倾思想”,实际上指的是“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基本政治诉求。泷川教授的《刑法读本》系自由主义的刑法学说,他在这部书中强调“……犯罪的最大原因,是由于环境不良和社会的不健全,要减少犯罪的人,应从改革社会环境入手”。因为泷川教授具有“左倾思想”,成了当时日本政府打压的对象。教育部长鸠山听命于军方,将泷川教授赶出京都帝大。法学部全体教授因同情泷川教授遭受无端迫害而提出集体辞呈,以迫使政府收回成命。
当时政府强硬态度,导致法学部森口繁治、佐佐木、宫本英雄、末川博、田村德治、恒藤恭等教授愤然离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政府才承认其处分不当,泷川教授得以复职。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以“泷川教授事件”为背景,执导了战后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我于青春无悔》,获当年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大影片第二名。不过,这是后话。在当时,京都帝大法学部老师们的这种学人风骨以及对学术自由理念的坚守,对每一位莘莘学子来说,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这种环境熏陶下,有助于雷震汲取自由民主与宪政主义之观念;雷震不屈服于权威的个性,更因为教师们的言教与身传,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雷震自己也说,“森口师之教诲,所受之时间虽不多,而今日之笃信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而牢不可破者,自不能不说是受到他的意见的影响。”
奈良位于日本中西部,距离京都很近。从京都乘坐火车前往,只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对于喜欢旅行的雷震来说,奈良就像是京都的近郊,“晨往而夕返”,可以尽情游玩许多著名景点,如祭奉着日本最大的佛像,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东大寺,一直让雷震“叹为观止”。 奈良公园是日本当时最大的公园之一,以天然林木为主,约占奈良市区的三分之一。苍杉古松,树木葱郁,春樱秋枫,景色十分迷人,是一般游人不可不去的地方。雷震在此期间,先后去过奈良三次,前两次都是游历名胜和瞻览古迹,第三次是在京都帝大法学部的安排下,与几十位同学一起参观了在当时被认为是日本监狱管理制度最为完善和最见成效的奈良模范监狱,从学习法律的角度来讲,无疑是他“政治课程”中的一部分。
走进这所模范监狱,环境与设施之好,同学们不胜惊讶,根本不像是一座阴森森的监狱,“一如学校式的生活,绝无坐牢的意味,犯人也无脚獠手铐之事”。监狱长是一位法学博士,对监狱管理订有一套完整而充满人性的制度。在这位博士监狱长的监管理念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犯人也有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人权自由。对于狱方来说,应当根据每一位犯人的技能及自己的志愿(而不是强迫)分配适合的工作,不能不考虑每一位犯人的实际情况。在这所模范监狱中,除了正常管理之外,还有许多由狱方出面安排的团体活动,名目繁多,内容生动,其目的是为了“让犯人被囚的身心在一种集体的相互关照下感到几许温暖”。
对于那些信奉宗教的犯人,狱方会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满足他们提出的正当要求,指定牧师、神父以及佛教的和尚,按时前来给这些人做祷告或念经;他们自己每天早晚也要诵读圣经和佛书,以便在服刑期间,首先在精神上获得一种自救,然后对其罪责有所反思,真正做到洗心革面,悔过自新,出狱之后,方能自觉地成为一个守法有理智的公民。狱方还提供大量的文艺书籍或专业参考书供犯人阅读,若哪位犯人想研习专门的学问需要参考书籍时,尽可开出书单让狱方代为购买。
这位博士监狱长谈吐儒雅,为人真诚,给人以一种信任之感。
雷震了解到,狱中的犯人对这位监狱长无比尊敬和拥戴,“他对于犯人十分亲切,照料周到。每周一到周六的午餐,和他们会餐,每次约有一百五十人,他坐在上头,面对着犯人,用日本吃饭时的小茶几,吃的东西,完全相同,吃完了谈笑风生,他把所有犯人视为兄弟”,这种监管方式,雷震等人闻所未闻。这位博士监狱长对前来参观的学生说:这所监狱的犯人,有很多人在刑期不到三分之一之时,就已经忏悔改过,并表示出狱之后,将努力做一个遵守法纪的人。而法院的判决却“刑有定期”,对狱方来说,只能依照判决之刑期对其继续执行禁锢,而不是根据犯人的悔过表现,由狱方提出或建议,予以提前释放,或暂行开释。日本现行刑法固执刻板,法理陈旧,无视人性可以回归的这一基本事实,既残害了犯人的品格,也伤害了犯人的情感,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在人的资源上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更何况,岁月蹉跎,人生几何,不能因为一个人偶尔失足或犯罪,就要长期受到身体乃至精神上的折磨,从而消耗了一个人的大好时光。
这位博士监狱长主张修正日本现行刑法,在他认为,今后法院的判决只要判出一个“最高年限”和“最低年限”就可以了,其改造过程及自省效果,可以由监狱方针对每一位犯人在狱中的实际表现、忏悔程度,核准其释放年限,以求真正达到“改过自新”、“刑期无刑”之目的。这一番话,让雷震等人茅塞顿开,“印象极深而迄今不能忘怀”。雷震当时就认为,这是日本“监狱理念”朝着法治和人道主义方向转变的一种努力,在这所模范监狱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与中国传统中的“牢不可破”的监狱观相比,更具理性和人性化色彩。
雷震还说:“中国人过去把监狱叫做‘牢’,‘监牢’,‘牢’者,饲养牲畜的圈子,所以有‘牢头禁子’之说。有关‘牢’的术语,如‘坐牢’、‘监牢’等等,似对人有侮蔑之意,盖把人当作牲畜看待也。现在法律上称‘牢’为监狱,我觉得‘狱’字也有些不妥,使人联想到‘地狱’上去,倒不如称为‘监屋’为佳,或‘民监’、‘军监’亦可……”若干年后,当雷震坐满蒋介石的十年大牢之后,以其亲身经历深感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牢头禁子在观念上,一般的是没有把受刑人当作‘人’看待,其心目中认为‘受刑人’简直就是一个‘祸害’,……像奈良模范监狱长对待受刑者的温暖,一点也没有”。
1925年秋天的“奈良模范监狱”之行,可以说,成为雷震一生考量“监狱理念”的一个重要标尺,这是他在后来之所以猛烈抨击国民党牢狱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堂意外的“政治课”对他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