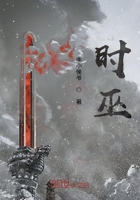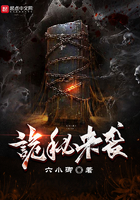初中我在八班,而小太妹是六班。
我一直对她有模模糊糊的好感,高挑的个子,有着那个年纪女生不该有的潇洒,又或许是喜欢她的无忧无虑,早早的褪尽了青涩。跟一般的遇见不同,我第一次看见小太妹的时候她在跟人打架。在学校的东北角,我远远地愣在那里看着她跟一个丸子头吵架,不敢走那条路,只见吵着吵着,那个盘着头发的女生先是双手重重的推了小太妹一下,小太妹踉跄几步站稳,似乎又挑衅了几句故意激怒对方,那女生气的飞起一脚,结果没扫上被小太妹偏过去了,踢上了窄路边一根竹子,一会儿工夫就被小太妹一扭掐脖子压在了学校的围墙上,一只腿的膝盖狠狠地怼在那丸子头的腰间重心处。“服不服?”“服你大姨”丸子头骂了一句换来的是更有力的压迫,疼的龇牙咧嘴。
虽然结束的这么快,但还真是看得我惊心动魄。之前我还以为女孩子打架就是相互扯扯头发,用指甲抓抓,用嘴咬咬。
那个女生,从地上爬起来。发酸的插着腰指着小太妹“你给我等着!”而她不屑一顾的回头瞥了瞥她,右手食指垂直指向地“有种别靠男人,老娘等着呢。”
她往这边回走时。我抱着那个年纪本能的还接受不了的微妙的厌恶感立刻逃走了。
没多久后的一次大课间,各班人都闲在走廊趴在栏杆上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她,这一次就像找到了这个世界里独一无二的一件不得了的宝物。只有我知道的宝物。她那时还跟他们班男生勾肩搭背,闲扯着。真是的,我明明很小心的,但她还是似乎被我的目光触碰了一般,神一样的精准看向了这里。周围的人都在言语热烈。而她,收回自己的手臂,叠在了栏杆上,把头缓缓的靠在了白皙的小臂上,歪着头,看着我笑,不,是眼睛在笑,盯了我一会儿,然后好看的嘴唇微开微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周围的人依旧叽叽喳喳的热烈,可我的世界一片安静。空气中燥热的水分子逐渐冷却。那时的我一定是静若木鸡的。很呆很傻的那种。不会错的。所以,最后我也傻傻的对她笑了。
把所有的事藏在心里。小小的心小心翼翼孵化这些稚嫩的经不起推敲的酸甜情感。我那时就很清楚,我的这份情感和我对Sun小姐的是绝对绝对不同的。
初中时脑子少根筋。做什么事都是半吊子。一次做广播操的时候我被班主任揪出队伍,说我做操像残疾人,罚我站在队伍最前头做一周的操。当时每天出操对我来说都很痛苦,因为我的脸皮很薄,受不了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那是我觉得我不管我怎么认真的摆臂,伸腿,原地跳都觉得自己像个滑稽的小丑。那几天害怕听到打出操的铃,一天出操的时候,六班的队伍经过,我感觉有人从后面拍了我的肩膀,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呀,认错人了,不过你这表情好挫啊。”笑哈哈的走开。
最后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糟。那周星期五下午班会课上,老孟(我们班主任)在最后突然来了句,“经过一周的刻苦磨炼,今天我要恭喜一位同学从残疾院成功出院,他现在做操可标准了。小君同学,你能照这样保持下去不?”我羞红了脸,像蚊子一样哼了一声。“什么呀,还像小丫头一样不好意思,你们大家也给点鼓励”。大家起哄,浮夸掌声把我淹没。
那次值日后很晚,我去车库取自行车回家,发现她靠在墙上,两手交叉枕在小腰后,吹着泡泡糖,正是符合老师口中放学不及时回家在外逗留的‘坏学生’形象。一缕细长的刘海自额间垂至鼻尖,有一点点湿润了,我平时是很喜欢沿着车库的斜坡撒着欢跑下去的,那种单肩包拉着我的肩膀紧追着身后轻飘飘的感觉很好,啊,还有冲到底停下时它重重的拍我屁股那一下。可当时步子越来越慢,直到停下。瞧着她俏皮的刘海,很仔细很仔细的瞧,瞧的她有些不好意思了,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的看一个女生。春末的落阳暖暖的热。顺贴着墙照下。斜的灰色白色金色的光影被拉的长长的相互交替。她站在这些纵横间,朝我招手,“嘿,过来过来”我那时候发现女孩子流汗时会有一种淡淡的好闻的味道。而母亲呼哧呼哧跪着擦地板的时候身上的气息是醇厚的。她看看我,越凑越近,就快要贴上我的脸。嘀咕了一句,‘皮肤真嫩’。人家都往回走了,我居然被吸引的一般跟着她走出了车库,都忘了去取车。她听见身后轻轻的脚步声,她停了下来,回头看着我,我也立刻停下来,眼巴巴望着她。真像一只招呼一下就摇着尾巴跟过来的流浪小狗。我没有被人贩子拐走能安然无恙长这么大真是个奇迹。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会哼哼,点点头,摇摇头,和傻笑。“嘿,你带钱了吗”她很自然的来了句,然后又意料中的看我摇摇头,“我有哦~”那时候袋装汽水是三毛一袋,五毛两袋。小卖店老板好黑心哦,小学的时候周围小贩都是两毛一袋的卖。她买了两袋,自己嘴里叼着一袋另一袋伸给我,‘喏,姐请你的’。亮晶晶的液体装在透明的袋子里还有一些小气泡紧紧贴在朝向你的这面眼巴巴的等你咬开想要出去。这对当时的我好奢侈啊。我在想她会不会和我聊一些那时经济生活台放的动画片,然而她没有。
我们就那样出了学校,在校门口她和我说了再见,我看着她斜过了马路,她的家还在人民西路更西的地方,那儿应该是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方向。我总感觉我拿了什么东西但翻翻口袋什么也没有,但我是清楚知道我的自行车还在学校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反身去讨。我就那样往回走,天色渐渐暗,路灯一盏一盏的亮了起来,向远方望延伸到镇上。后来夜色彻底深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西路的两边那时都是推平后还未开发的土地,两边黑漆漆的,我只敢低着头看着地下走,从这盏灯椭圆光圈里的亮处走到暗处,再渐渐走到下盏灯的亮处,就这样循环着好像怎么也不会累。人民西路还不叫西街的时候,很破,绿化带都没有,两边没有总是亮着光的24小时便利店,没有钱江酒店没有潭河公园。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些光秃秃的路灯。我在长大,西街也在变化,她变的整洁了,变美了,变的奢华了珠光宝气,而我还是那副蠢样。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妈怎么骂的我我都没听进去。
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以至于这一天我像休克一般对这件事没什么感觉,直到睡一觉起来后的第二天我才兴奋起来,持续了好几天,那些天被批评了都超开心。那时和小太妹眉来眼去看着她冲我笑就已经很幸福了。
还有能想起的就只有初二苦夏,拥挤喧闹的走廊上我遇见的搬着高高生物作业的很是吃力但是挂着无奈微笑走过的天使。天当时已经很热了,我穿的是露大腿的马裤,而她穿的是奶白色的长裙,光着两只白皙的手臂。我从没见过她,我就想她那么美,为什么周围熙熙攘攘的同学没有被惊艳到呢?他们都看不见的嘛?
我去送重抄后的笔记本时,还絮絮叨叨的跟同桌啰嗦“我好怕呀,一个人不敢去办公室~要是老孟还说我笔记不行还要重抄怎么办呀~”同桌耐着性子安慰一遍遍。结果最后给老孟送去,她看了后还表扬了我。我经过六班时还趴在窗台上踮踮脚尖望了望里面,小太妹不知去了哪里,不在座位上。“你找我们班谁啊?”一个男生和气的问,我不好意思的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便往回走。
一定是因为她来了,她在的世界里人们都变得温柔。
现在想想不可思议。她居然是用走的。真low~她可是天使啊。也许是因为只见过一面所以我到现在都觉得她是我见过最美的人。到现在都觉得是梦。因为后来我不管多少次站在走廊上,或是头探出窗外都没有再见过她。这种超自然常理的现象我喜欢把它归结为是神所为。
我恨不得把那见到她的那一刻,周围所有东西,细到每一粒尘埃都是闪着恩泽的。写一遍。每个瞬间都要撰写成诗句,捻成碰触心底的柔软。
没有名字的天使来了又走,情理之中。可是最后的一个夏天,小太妹也走了。
拍毕业照的那天,离中考已经非常非常近了,离校只剩几天。大道上搬了一排一排的桌椅,大致是两个班拍一轮这样子。
我好想去看一眼小太妹,我已经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拍毕业照她一定会来的吧。
轮到我们班拍时,老孟让排好队去中央大道,而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偷偷摸出教室往大道上狂奔,不抓紧的话六班就该散场了。
我在一波一波人堆里,找着她的身影,找着微微黝黑的皮肤,找着那俏皮的刘海。
“同学同学,你们班那个喜欢穿破的牛仔短裤,头发有点黄,那个她来了吗?”那个她。是啊,那个她,我连她名字都不知道。
“她呀,她这几天没来。”
没来。我自顾自在马上要拍毕业照的空椅子上蹲下来抱着膝盖犯呆,四周的人们都忙忙碌碌,我只好脸埋进窄窄的臂怀间,不知道要做什么,憋的呼吸难过满脸通红时,眼皮惺忪无力,看着大道上的人来来往往。
你不来了么,真的再也不来了么,那你之前来干嘛呢。我看着远处模糊的整齐长队的同学们,老孟走在最前面好像找我算账来了,我无心把头平歪到一边躺在胳膊肘上,看到不知哪里的一片黄色树叶悄悄的落,在这个明明不会掉落叶的夏季,天热了一阵子,我晕乎乎了几天,写了几张熟烂透的卷子,不见了Sun小姐。结束的夏天湿热,如同那句月色真美,没牵过的手,未送出的四叶草,遮满别人背影的大道,独对着世界的小小心绪不了了之,一切忽然间匆匆离去草草收场永远关上了门。然后我那无味白蜡般的初中和少年时代就迎来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