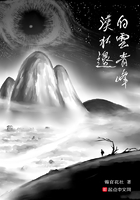音州帝都,谛寰殿上。
雄浑脆远的编钟悬磬之声宛如金声玉振,自高广的聆啼台上鼓荡开,向帝君脚下的都城宣告朝会的开始。
随着金朱玉门缓缓大开,早于殿外守候的百官朝臣们或三三两两,或鱼贯而入。
八根云饰雀绕的擎天拱柱撑起了谛寰殿的辉煌,由凤凰围盘作边的七个藻井自殿门直沿深处的云陛,七颗头颅大小的辉泽珠从天顶投下了如日光明。
辉煌富丽的朝殿没有因为百官的进入而显嘈杂,空旷的大殿之内只闻声声脚步的回响。
按职各列其位的百官已然就绪,耳边犹有钟磬之音声声回荡,可那该在云陛之上的人却仍未出现。
众百官之位首,才刚近半百便银发簇生的苏家家主苏贤儒看了眼立于云陛之畔的中常侍,略一犹豫后,便向云陛之上的御座遥遥作揖,同时口中问道:“杨常侍,朝时已至,为何仍不见帝君踪影?”
云陛下的人立得有些远,待中年男子礼毕起身再看向他时,才微微躬身作答:“冢宰大人,帝君今日延请天师入殿,天师难得作应一次。今日,这朝会怕是,难见帝颜了……”
尖细的身音从远方传来,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之内,引得数声低惆的叹息。被称为冢宰的男子虽未发声,却显而易见地面露无奈。
“既然帝君未得空,那苏大人,不如我们便先开始吧。”
中气十足的声音忽地从殿右响起,苏贤儒不由移目看去,只见一位袖袍藉以鸾鸟装饰的紫衣男子正微侧着身子,半笑地斜睨着他。
“王公子此言未免不妥,帝君不临朝,我等臣子又怎敢妄启朝会?”
对于苏贤儒的话,紫衣男子面上在某一瞬微露嘲色,继而不紧不慢地道:“帝君未至朝会的情况今日可并非首例,难道以往你们这些百官便将朝会搁置了么?”
“自然不是,但今日……”
还未等苏贤儒的话说完,那紫衣男子身后便有人截口打断:“苏冢宰,今日这朝会可不同往日,一刻都耽误不得。既然帝君不得空,我等臣子便更不可拖沓,我们大可以先行商议,待达成一致后,再上奏帝君,这样又有何不可?”
唇上和颌下各蓄着一把胡子的大司货一脸精明,此刻,他言语之中已是带着些迫不及待的意味。
苏贤儒对此并不意外,他微皱着眉头,刚要驳斥,那紫衣男子便又再度开了口:“苏冢宰,司货大人说得不错,你应当清楚今日我们为何在此。这样的大事,可是耽误不得啊。”
经他这一句,大殿中顿有数道声音随之附和,这不由让苏贤儒面色微紧。
许也是见不得这大殿之中些微躁动的趋势,已是耳顺之年,掌天下教化的典业监大司徒穆色肃声开口:“朝堂之上,怎可如此喧哗?尔等可有对帝君与朝殿的敬畏之心?”
老司徒显然在百官之中颇具威望,他这一开口,周围窃窃私语的声音都小了许多,那些随声附和的人也都不由噤了声。
紫衣男子向着站在苏贤儒那一侧的大司徒点头致意,微微笑道:“还望大司徒莫要生气,我们也是心有所急,想必在场的各位也多少都对今日所要商议之事有所耳闻。此事,也确实是从速决议才好。司徒大人身为宗室长辈,遵从礼数人所共知,但帝君此刻正繁务琐身也是事实,我们总不能特意闯入聆啼台去,在他面前争论这些不是?”
年迈的大司徒对于紫衣男子的话显得极为不耐,不仅未对他的话回一句,甚至在他说话时也未投去一眼。但视线虽不曾触及,耳朵却是捂不住的,紫衣男子的话让他更是不免阴郁了面色。
苏贤儒无言地回顾了一圈殿内百官,也是心知拖延之法不妥,并非良策,于是便待出言启朝。
远扬清脆的钟磬之声猝响,自云陛之后的殿墙外渗进了广殿之中。直入神魂的音透进心底,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浑身一震,尽皆不由自主地向云陛之上躬身作揖。
立在陛下的杨常侍一听见那钟磬之声响起,忙自云陛的侧阶拾级而上,匆匆地赶到云陛上的后室锦帘之前。抬手卷起重重帷帐垂帘,口中尖细的嗓音也随之传彻了整个谛寰殿:“帝君临朝,恭迎帝君——”
“臣等恭迎帝君——”
陛下百官闻言下拜,唯有那紫衣男子肃色站着,直到看见那重重锦帘之后的身影后,才不得不略显僵硬地深深作揖:“臣弟拜见帝君……”
九重云陛之上,着深红鎏金色宽袍的男子极不情愿似的从帘下走出,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厌烦和不耐。随着他散漫的动作,其衣袍上的展翅凤鸟栩栩如生般扇动着羽翼,翩翩地落到了云陛之顶那尊崇无比的帝君之位上。
看着陛下拜倒一片的人,他无聊地叹了一声,又转头看向随着他从那锦帘之后走出的人:“天师啊,这朝会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是您偏要让我一起过来,我才懒得看他们这些官腔官调的嘴脸呢。”
头顶上传下的声音令拜倒的所有人都不禁诧异地抬了头,当看到云陛之上的场景之时,几乎在场的所有百官尽是五味杂陈,不知该如何言道这心中的感觉来。
代表着九州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御座上,坐着的人散漫无状,除了那躬侍一旁的中常侍之外,竟还有另外一个与朝堂毫不相干的人。那人一身白衣云袍,周身不缀一物,那素衣真如天边浮云般清淡无色,别无所饰,恰是一个仙风道骨的谪仙模样。再加上与其青年面相极为不称的一头奇异长发——乌发与银丝错杂而有序地成缕夹杂着,又被一顶高冠结束,有别于常人的状貌确也有些教人隐生敬畏。
但是,这一幕在一些恪守礼法的百官们看来,是一件极为挑衅的事。
紫衣男子嘴角微不可觉地笑笑,重新直起了身。
“多日不见帝君,臣弟甚是想念。似乎,帝君的气色要比往日更好了。”
听到云陛之下传来的话,冕服袭身的男子这才注意到那个陛下唯一直起的身影。
“哦,是昭治啊。我没来朝会那么久,当然气色好了。哎,对了,刚才我说的那些让人生厌的官腔官调里,可没有你啊。”
冕服男子无忌地与陛下的身影笑言道。
师昭治闻言,也随之笑起来:“臣弟明白,而且,帝君怎样说臣弟都是无妨的。”
“帝君,国有国威,礼制为先。九重云陛之上,理当只有您能站在上面,为何这个道人会与您一同出现?”
苍老而年迈的大司徒气得浑身发抖,看到那个被尊为天师的人站在象征着至高权力的云陛之上,本便已是怒得心肝皆颤,此刻又看到他与师昭治旁若无人地谈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更是忍不住,终于截口打断了两人的闲聊。他的这番话,其他百官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心底不无赞同,却到底是不敢显露。
被扫了兴致的冕服男子自然是心有不满,同时也几乎是勃然大怒,在看清陛下那颤颤巍巍的佝偻身影后,说出的话更是有些不加顾忌:“大司徒,我是帝君,这九重云陛之上我想让谁上就让谁上,怎么就只能我站着了?再说了,怎么不见你说杨常侍也不许站在这呢?你身为大司徒,掌天下教化,平日又这么地循礼节,怎么反倒对天师言语无礼了?”
大司徒闻言,顿时浑身发颤,显然是被气得不轻。眼看着他血气上冲,涨红了脸就要晕过去,一位背着药箱的中年人急忙上前扶住了他,接着又在其面部几大要穴上连施几针,才让他堪堪缓了过来。
场中的这一番变故电光火石,殿下的百官都是暗自摇头,站在大司徒周围的苏贤儒等人更是无奈地默叹。
“哎,大司徒怎么还突然发病了?杜先生,还要多谢你对大司徒施以援手啊。他可几乎是宗族里硕果仅存的长辈了,真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气出个病来,我可就要对不起先祖了。”
“帝君!你……你……”
大司徒又是一阵翻白眼,杜家医官连忙再度施救。
“哎,大司徒怎么又晕了,他是不是今日身体不适啊?那个,杜先生,要不你就先扶大司徒下去休息吧,免得他再操劳过度。”
杜家医官闻言,微微致礼应是,便与几个医芸馆的人一起带着陷入昏厥的大司徒下去了。
这一场闹剧很快落了幕,可却在在场的许多百官心中蒙了一层阴郁。
年轻的天师淡漠地看着这一出风波缓缓平息,待场面安静了下来,他转向宝座上的帝君道:“未料本道的存在让诸位建苍百官感到如此不适。帝君,本道还是与他们一样,站在这云陛之下的好。”
见天师如此说,帝君慌忙劝道:“天师莫要生气,不过是些墨守成规的老家伙而已,您不必动怒的。您就留在这云陛上吧,适才您与我讲的道法我还没听懂呢,这朝会要议的事,就任由他们吵去。杨常侍,快给天师移座呀,还站着干嘛?”
侍立一旁的杨常侍称是,立刻便去取了宽榻来。
“帝君也莫要肆意随心,在这朝殿之上,您还是顾及着臣子们的心态才好。这云陛本道确实不该立足,唯有云尘之下,方可修纯道法。帝君既然想听道法,那之后本道再与你讲便是。”
说完,年轻的天师一步步踏下了九层云陛,又盘膝坐于杨常侍命人移来的榻上。风轻云淡之状,更似堕尘之仙。
云陛上发生的事,台下的百官尽收眼底,他们或久或短地暗自窥视着阖眸打坐的人,唯有摇头不已。
师昭治冷眼看着发生的一切,心底嗤笑连连,已是懒得去注意向那个在他看来完全是故作姿态的年轻人。
苏贤儒默然观察了那天师几息,终于缓缓收回目光,抬眼看向云陛上的帝君。御座上的人依旧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心底不由又是一声哀叹。再次顿了顿,他清了下嗓子,向九云陛上作揖请命:“帝君,今日朝会,可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