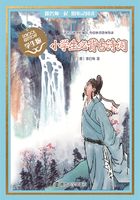曾经有一部法国影片,叫《上帝创造女人》,是著名艳星碧姬·巴铎主演的。其寓意无非是说,女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而碧姬·巴铎的脸蛋和身材,也恰好佐证了这一点。这部影片看似是对女性的极大恭维,可骨子里却包含着对女性的极大歧视。因为,它承袭并放大了以往的偏见,这种偏见从来都是把女性当作被创造的客体,而不是视为创造的主体。
生活中有一些男同志,是所谓的妇女爱好者,说得更严重点,是妇女崇拜者。但他们的热爱,仍然只是落实在身体层面,他们喜欢的是作为性别符号的女性。换一种方式热爱一下,怎么样?也就是说,进入精神层面,像喜欢她们的容貌和身体一样,喜欢她们的智力和精神,喜欢作为创造主体的女性。
这里得老实供认,作为一位男士,我也曾常常将“女人不适合从事创造性活动”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幸运的是,在我对于女性的认识过程中,每当快要误入歧途时,总会出现一些极杰出的女性,将我“挽救”过来。
先看思想领域。以前我不相信有女思想家,直到出现了苏珊·桑塔格。这位美国现代女思想大师,思考的疆域之广、开掘之深,让人吃惊。更难得的是,她始终坚守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敢于向主流舆论叫板。伊拉克战争爆发期间,她率先站出来质疑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国内我佩服的是李银河。她的思想解放程度超过大多数男学者,而且许多复杂的问题,她自有两三句话就点透的本事。
接着看文学领域。我曾经以为,在诗歌这一最纯粹的文学活动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十分有限。毫无疑问,诗是人类高等的智力活动之一。首先,诗歌是一整套独立于日常语言的自足的话语系统,这一点接近于数学;其次,诗歌是对于世界万物之间关系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命名,这一点又接近于物理。正是因为特别看重诗歌的“数学血缘”和“物理血缘”,我也形成了两个偏见:一是偏好以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重理、重智的英美现代诗歌,正如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偏好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一样;二是狭隘地认为,诗歌这一人类高等智力活动的最高等殿堂,是男性的天下,对于女性则是“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狄金森率先打破了我的偏见,她的诗同样是重智的英美一派,但其中的智慧在女性的敏感、纤细、绝望等包裹下,放射出别样的光彩;而彻底打破我偏见的,是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她让我无奈地感到,诗歌中的智是另外一种智,而且可能是一种更接近女性的“智”。茨维塔耶娃自己说“诗歌以星子和玫瑰的方式生长”,她就像一位女巫,与万物起舞,她掌握了诗歌领域最高的“智”,星子的规则,她明了;花朵的公式,她也知晓。这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直觉,不如说是她找到了一种在比俄罗斯魔方更复杂的时空结构中行走的秘诀。惠特曼、艾略特、奥登这些男性诗人,他们在大自然、历史、书本中跋涉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的地点,茨维塔耶娃(也包括狄金森)凭自己的“轻功”很容易就能到达。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曾说茨维塔耶娃是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吗,布罗茨基有点恼火地说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恐怕真的如他所言吧。
再来看幽默领域。幽默,仿佛一直都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只有被逗笑的份儿。但现在我们不仅有宋丹丹这样的女笑星,还有像洪晃这样的幽默作家。这半个月来,我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洪晃的博客上去看一看,并预先做好到地上找牙的准备。此外,《BJ单身日记》《爱是妥协》等一批英美经典浪漫喜剧,其编剧都是女性。将浪漫和幽默结合得如此之好,倒真是女作家的专长。
最后再来看科学领域。进入这个领域说话千万要小心一些,因为哈佛校长萨默斯刚刚踩了地雷。这位仁兄说妇女在数理方面与男人相比,存在着先天的差距,结果导致舆论大哗,不得不含羞辞职。从表面上看,女物理学家中叫得响的就是居里夫人,女数学家中叫得响的就是海帕希亚,后者还被反动势力用火刑烧死了。但这不应该归结于“先天的差距”,而应该归结于“机会不均等”。如今,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成为女性的狂欢节,女性在阅读量、动手能力、注意力集中程度、耐心等方面都在赶超男性。可以预见,她们的身影将更多地出现在一切尖端创造领域,当然也包括看起来最困难的科学领域。
遗憾的是,还有不少女性,没有认识到从创造中获得乐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她们只等着上帝来创造自己,想都不去想自己也能创造包括上帝在内的所有事物。她们的精力耗费在闲聊、家务、相夫教子等琐碎的事情上,正如阿根廷漫画家季诺笔下的玛法达所言,“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女人应该扮演的角色,她们都用一块抹布代替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所不能赞成的。
是甩开那块抹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