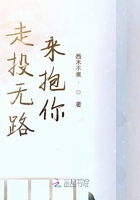老嬷嬷喏喏道来,“奴家的儿媳妇,曾经与老奴提过,京城里的花街柳巷,小倌最为之赚钱了,那些烟花之地,是一捆钱一捆钱地进去。”老嬷嬷说着的时候,眼睛都是直的,此刻的她幻想着眼前摆着满地儿白花花的银两。
不过,没等季清芜会过意,老嬷嬷神情便也怏怏的,眼神黯淡了下,透着惊愕的错然,“老奴该死,老奴该死。这些是烟花之地,只会败坏了王妃的名誉。”她真的是老糊涂啊,王妃是何等人物?她一介下人,居然敢叫王妃下青楼,下小倌?
她吓得一把屈身跪在地儿上,等着王妃的降罪。
季清芜一听,嘴角儿一勾,勾勒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笑容,“老嬷嬷,你这个点子极好了。本王妃就在京城最为繁华的地段,开一间小倌。”
她拍手叫好,连连称赞着老嬷嬷的点子好。
她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上呢?还亏她是个拥有这现代人思想的灵魂啊。
她所开的小倌,与外边的情色交易是有所区别的,她所经营的必须是通过各种筛选才得以持有由她所颁发的上岗证。
她得物色上等的好货色,才貌双全的美男子,才可以起到镇倌作用。
这点子是有了,但是这美男子上哪儿找去?
这开小倌子,得融入更多的资金,人力资源,很多繁琐的事情都得亲自去做。
想不到自己创业是如此地艰难啊,还未着手,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啊,回想现代很多富翁都是白手起家的,她真心是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她的手指焦急如焚地在桌子上弹着,愈弹心腔一股莫名的怒火渐生而起,叹着闷气。
真他娘的憋屈啊!她可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却要拱手相让三百两黄金给那个大恶棍?
苍上怎么如此待她不薄?
她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儿去聘请美男子开张啊。
她一挥手,让影儿将小木柜里的木匣子拿了过来。
开启木匣子,摸了一把那些珠宝,问了句,“影儿,这么点首饰可换多少银子?”
她甚是不舍,毕竟这是她来到此地的第一笔横财,居然就这么快便化为乌有了。
她觉得一定是她与王爷的八字相冲,这是前来给他还债的。只是这一笔债务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当务之急,唯有多开拓赚钱之道,尽快将银钱还了王爷,赎回自己的自由身。
影儿做了个手势:小姐,万事开头难,我们小心为好,若是传入了王爷的耳里,又是一番麻烦啊。
影儿既是支持季清芜这念法的,可一想到了王爷那冰冷的面颊,她便替季清芜忧心起来。
季清芜转个脸,“影儿,这个毋须担心,我在想着怎么收纳才貌双全的美男子。”这美男子上哪找啊。
她用力地冥思,冥思,希望能想出头绪。
啊,影儿一个激灵,打了个手势:早些年,有个画师给小姐画了一幅美人图。
季清芜激动地起身,“画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画师?说到画师,脑中忽然想起了在宫中时遇上的画师,那画师犹如自画中走出来的美男子,美得没有一点儿的瑕疵。
他能背请入宫中为各位嫔妃作画,想必一定也是讨得更多人的爱戴。
这么想着,季清芜那舒展不开的眉宇,这会子一下子明朗起来。
继而,脑中也逐渐地浮现了其他两位不同风情的美男子,一位是十三王爷,则另一位便是她的恩人聿修。
她爽朗地笑着,这人选倒是都有了,但怎么请君入瓮又是一个难题,这事情怎么一件接着一件,永无休止?
她得发出邀请,请这三位美男子出师才是。
“影儿,这画师可是唤作画弦大师?”季清芜隐约感觉到是同一人,她将木匣子盖好。
影儿惊呼,手停在半空,打了个问号,在问着,小姐怎么知道画师的大名?
季清芜一见这情形,眼睛放光,“影儿,若是,我待会做个邀请信笺,你替我送到画弦大师的府邸。”
她在琢磨着怎么出府,将邀请信笺交到聿修的手上。
十三王爷现在深居皇宫中,她又怎么样才得以联系上十三王爷?
她现在是有夫之妇,与其他的男子交往若是过密,会被说闲言闲语,她得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去游说这几个极品男助她一臂之力呢?
她需要人才啊,没有人才,谁人帮她招揽生意啊?
季清芜在书斋外来回踱步,掰着手指头,忽而觉得一阵寒气吹拂而进体内,她伸手去拢了拢衣裳,揪紧了些。
这会子,书斋的房门被打开,季清芜一个激灵,躲进了石柱后方,探视是何人?
她藏好后,伸头出来窥觑了一下,见是管家,她走出了石柱,唤住管家的脚步,“管家,王爷可在书斋?”
管家转过身子,福身作揖,“奴才见过王妃。”顿了顿,“回王妃的话,王爷正就寝中。”
去书斋,得经过东苑,所以当祈天澈下了早朝后,踏着脚步声经过东苑的回廊时,季清芜正躺下榻上,听着外间的一动一静,她屏住呼吸说着祈天澈的步子声,在他经过房门的时候,明显的停顿了一下子,在他停下的那一刻,她连最后的那一丝呼吸都被抽走了。
在整颗心提上桑眼的时候,正担心他会破门而入,他却提着步子离了去。
她的心中有股失落而寂寞的感觉在流窜着,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再也不进东苑半步了?这让她很失望,但是也很侥幸,这心里真的是上下不是个滋味儿。
季清芜一拂手,“我进去看一下王爷。”便让管家退下去。
管家用着疑惑的眼神睇了一眼王妃,心里腹诽着:这是打哪儿刮起的风?王妃居然说要看看王爷,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水火不容的吗?
管家轻叹了一口气,也不作多余的掺和,毕竟那也是他们两夫妻之间的事情了,与他这个下人无关,更与旁人无关。
季清芜轻手轻脚地将门推开,进了去。
抬起眼眸,便见祈天澈正襟坐于案牍前,手撑着面颊,眉头是深锁不展的。
她一看,岁与他之间有着些不明理的过节,但是见他这般摸样,心里还是会一紧。
徙步走至窗棂前,这个管家真是粗心,王爷这不是在休憩中吗?炉子也不暖火,窗棂也不关上,是想王爷患风寒吗?
她伸手将窗关好。
打了帘子走到了里间,捡起一件灰色大毡衣,披在他的身上。
她来是做什么?她本是想来找他,问他借点资金,和捎个信给天雪公主,她得赌一把,女人的直觉告诉她,天雪或许会帮她这个忙,不帮也说不定。
她定定地望着祈天澈的侧脸足足有一会子。
从未这么打量过他,一直以来两个人之间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现在这么近距离地窥看着他,熟睡中的他,依然是绷紧着脸,冷冷冰冰的,让人看着心中就来火,真想上前海扁他一拳。
他才下了早朝,这会子就窝在书斋打起盹了,想必他一定是劳累了吧。她也不忍心去打搅他休息了。
然,季清芜那道斜长的影子投到了案牍前,他是感觉得到,呼吸也急促了些许,他正掂量着她要作甚么,想不到她会如此轻柔地为他披上大毡衣。
这小小的举动却感染了他,之前的纷扰,早已在她给他披上大毡衣的那一刻,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