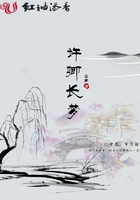“祈天澈,你净会欺负人!”看着那被滚烫的茶水烫伤的手,她再也坚持不住那颗一直被自己捍卫得坚固的心,眼泪珠儿也压抑不住地往下滑落。
祈天澈转身欲要离去,季清芜却心一慌,“喂,你真的走了啊。”她有点低落,居然为了一支破簪子和她晦气,还将她推到,对不起也没一声。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而后又继续地向前迈步,季清芜这会心里可是不好受,看着他决然而去的身影,心里空虚的紧。
只有自己坐在桌子前,她将烫伤了的手放于冷水盘里,感觉才稍微好了一点儿。
她咬牙切齿,在心底里咒骂着:好你个祈天澈,居然敢为了一支簪子和我做对,居然伤了我的手就一走了之,还将影儿给支走,摆明是想她自生自灭。
当豆大的眼泪珠儿再次夺眶而出时,她低低地呜咽着,转瞬之际,门被吱呀地推开,她来不及收住眼泪,扭头便看到了夺门而进的祈天澈,因被泪水模糊了,她只能见到眼前模糊的人影在重叠着,正缓缓向她走来。
“芜儿,你莫哭,我这就给你上药。”他突然醒起,自己的别苑里珍藏了一支御用的烫伤膏,他这会子不是取来了么?
他蘸着一点药膏,将季清芜的手从冷水盘中取了出来,放置自己的跟前,轻轻地抹上去,他的眉头一直是紧蹙着,却没有丝毫的松弛。
在与那冰凉的药膏相碰时,她的手轻轻地一缩,而祈天澈却没有有让她躲开的意念,而是紧紧地抓住她的手,来回地轻轻抹着,“芜儿,你要是怨恨我,你可以将所有的气都撒在我的身上,但是你不可以这么动心肝火气的,气坏了身子那可怎么是好?”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低缓,但季清芜依然是低低地抽噎着,肩头也随着轻轻地轻颤着,被他握着的手,似乎有股麻痹的电流在身体内迅速地流窜着,被电触一般,她不禁地颤抖着身子。
她抹了一把泪水鼻涕,而后是毫不顾形象地将鼻水吸回去。
噗嗤——
是祈天澈发出的笑声,她蹙眉瞪着祈天澈,冷冷地问了句,“你笑什么啊?”
祈天澈抬起凤眼,凝视了一会季清芜,敛了笑,“你看你,鼻涕都流出来了。”说着不嫌脏地伸出手托着她的脸,而后是用力地抹去那鼻涕痕迹。
“不准笑。”季清芜愤然地呵斥着。
祈天澈无奈,只好憋着笑,眼里也是溢着满是笑意。
季清芜只道他是在取笑着她,她心生羞怒,欲要抬手就是给他一拳,却被紧紧地接住,“芜儿,你刚受了伤,你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加之,昨晚的事情,你更是身体不适了,更要多加休息才是啊,怎么还是这么多力气与我争个不是?”
季清芜脸蛋倏的绯红,直到脖间也收藏不住她的娇羞,她心里既是怒又是喜。
“既然你说你是被我冤枉的,那你就拿出证据来证明我的悖论,别在这里装好人,我打心底里一点儿也不觉得你有多么的真诚。”
她嫌恶地道。头也别去一边,脸上也随之露出了淡淡的冷然。
他看着她脸上表现出的淡然,心里也是一阵不安,失落的感觉顿然遍布了全身,“好,我一定会拿出证据的。”他按着她的手道。
他即使能拿出证据来,她也只当是他伪造的,祈王府是他的地盘,他说一句,有谁敢多言?他说得如此轻松,还不是想为自己找着说辞。
“若是让我知道谁这么大胆子下药,我一定问候他祖宗十八代。”她咬牙切齿狠狠地道。
这会子从外头进来的影儿一听此话,手上拿着的药瓶哐当地掉在地上,那乳白色的药膏随至袒露在地上,飘着淡淡的清香。
季清芜与祈天澈闻声望了过去,先是季清芜道了声,“影儿,你怎么了?今天你精神恍惚,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影儿跪在地上啊啊地叫着,像是在跪谢,打破了药瓶,王爷一定会生气的。
季清芜晓得影儿在害怕什么,“影儿,你先起身,一瓶药而已,毋须这么大惊小怪的,这王府里,有我罩着你,没有人可以再欺负你了。”说着瞟了一眼沉着脸的祈天澈,这话儿摆明是说与他听的。
祈天澈又怎么会不知道季清芜在说着什么呢,“免了,王妃都发话了,你还愣伫着那儿是作甚?将摔了的碎物都收拾一下退下吧。”他一摆手,轻轻地道。
影儿将地上的残迹收拾后,这才提着裙子缓缓地从地上起身,低垂着头退出了屋里。
“在东苑里的丫鬟都是我的人,你以后可别再去吓着她们了。”
季清芜缓缓地说着,却不去看他的脸。
“芜儿,为了你我愿意改。”
“哦,是吗?那我还真得拭目以待了。”
“……”
又变回了冷场。
仿佛是停止了似的,谁也没有再动,谁也没有说话打破这份静谧。
季清芜将手往回一缩,“你该走了。”她下了逐客令。
这里都是他的家啊,怎么却被赶了呢?
“芜儿,让我留下来照顾你。”他急急道。
“你不是还有其他妾侍的吗?去找她们便是了。”留在这里,她看着他就想将他碎尸万段,但是他是高高在上的王爷,她只是一介小女子,动不了手。
“刚儿不是你唤我别走的吗?此时怎么舍得将我请走了呢?”他低语。
“谁舍不得你了?我恨不得你永远都别出现在我的跟前。”
“除了宓儿,现在只有你是我想要去珍爱的女人。”他顾不上地将她轻揽入怀,将头轻轻地抵在她的头顶上,轻柔地说着。
季清芜却在他的怀里挣扎着,靠近他的肌肤,会让她无耻地想起昨晚被他侵犯之事,一想到这心中就燃起了一股怒火。
“你这个登徒子!净是趁人之危!你那么舍不得你的宓儿,你去找她得了啊!别将自己说得那么委屈,爱我让你受委屈了是吧?”她的声音一点儿也不温柔,还略带着丝丝的醋味。
“使不得,我现在只将心与你,宓儿,已是过去,纵使我再留恋她,那也是过眼云烟了。我只想好好地珍惜着你。”他还是将怀里乱动着的娇美人按住,让她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胸脯前,听着他心跳的律动。
“好啊!你居然这头说爱我,那头便忆起你的旧情人?果然是个寡情之人!”
她用着没受伤的手将他就是一推,从他的怀里跳了起来,瞪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