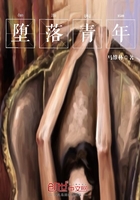八
消息终于还是传来了,聂红柳捏着这一纸书信,眼里泛出冷泪。
“宝莲,我们走。”
聂红柳站起来披上披风,面上冷光,眼里决绝。
宝莲一下便猜出了这封信的内容,心知小姐终于忍到头了。
宝莲看着眼泛泪光的红柳,见小姐手攥着披风有些抖,却还是竭力压着,便轻声开口:“老当家的?他?”
“爹走了。”聂红柳眼皮微颤,手摁着床站起来。
外面已完全黑了,灯笼光微微晃着,晃掉红柳一滴眼泪。
“你收拾东西,在屋里等我,小三子和你到底怎么着?你想好了告诉我,我去要休书。”
聂红柳说完就往走,宝莲一声“小姐”刚出嗓子,冷风就灌了进来,聂红柳已推门出去了。
聂红柳见沈素节书房灯还亮着,推开门便说:“我要休书,你刚好在写字,顺便写了吧。”
沈素节抬头见是红柳,笑刚露出来就卡在脸上,手下一哆嗦戳断笔杆,落了一滩墨,污了画上人面。
“写完休书我们便各自两清,从此以后你沈大少爷的夫人就不再是土匪了,我也不会再污了你沈家门楣。”红柳说着坐下来看着沈素节,脸上决然,大有指挥千军万马,身坐帅位之势。
沈素节看出了她的急切,又不知发生了什么,竟然要一纸休书?她向来不胡闹,除了那次凌然骑马出走,还没有这样一次突如其来的发作。
“你先......你到底怎么了?”沈素节刚一询问,红柳便站了起来,似是一刻也等不及。
“没怎么,过够了。”红柳说着咽下一口眼泪,瞪着眼睛仰头、低头,眼光总也落不到沈素节脸上。
“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沈素节看不透这个女人,既然不想搭理自己,那好好的做沈家少奶奶不也挺好的吗?
“现在你要休书,你拿了休书去哪里?再回山寨?做土匪?”
“对,就是做你看不上的土匪。”聂红柳回了回去,语气硬得让沈素节无话可接。
“我不是......看不上土匪,而是你......”
未等沈素节说完聂红柳就接了上来:“你不是看不上土匪,你只是单纯看不上我是吗?我粗鲁不知礼仪,我不是名门闺秀,赶不上你那个心心念念的青梅竹马还是一见钟情,张爱玲是吗?她现在在哪?你可以去找她了,你爹走了,我爹也走了,不用再做戏扮夫妻了。”
沈素节听了这话只觉哭笑不得,哪里又扯到张爱玲了,人家是......真是解释不清。
“我都没见过她。”沈素节只能这样解释。
“呵,见没见过,那与我无关了。”聂红柳立着眼睛看前面,尽管沈素节已离开桌子站到了她身边,她仍是没转头看他。
“你刚才说岳父没了?”沈素节才抓住轻重,气急分辨之下竟险些被她带沟里。这才是大事啊,解释什么张爱玲啊。
“你着急回去?”沈素节继续询问,语气更是软了下来。
聂红柳落下眼泪,忙抬手擦擦,点点头答:“嗯,你快写休书吧。”
“我先陪你回去,休书的事以后再说,好吗?”
沈素节伸手抱她,被聂红柳推开。
聂红柳推开沈素节甩身走了,脸上都是泪。
聂红柳当夜跨马就往寨子赶,沈素节急忙也让老管家带了马来。
他不会骑马,横在马上颠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浑身都冻透了,顶着雪倒在了寨门前。
红柳一身素白跪在聚义堂灵棺前,一众兄弟跟着她跪在后面。
路子本就是聂大当家的义子,现在接了山寨,跪在灵前抗幡尽孝。
三五巡山将素节扛了上来,聂红柳看着三五肩上已晕过去的沈素节,又转过身对着灵棺哭。
路子摆手让三五把人先扛下去,等醒了再说,估计红柳心情不好,也就不让三五多说话,顺手将一些好事的都打发了下去。
“哥。”红柳倚在路子身上,眼泪顺着脸划下来。
“他妈的沈素节,老子的妹子,就给他这么祸祸,都瘦成骨头了。”路子看着瘦成一把骨头的妹子,再想想当初上马提枪的大小姐,那是何等威风,心里更是骂“他妈的姓沈的”。
“哥,我,我不想,回去了。”
“不想回去?”路四海扶起妹妹仔细看着她眉眼问:“不想跟那孬种男人过了?”
“他不孬种,只是不喜欢。”红柳含着泪,声音哽咽。
她还是不能说他孬种、不好,他秀气涵养,只是不喜欢。
“傻丫头,过日子哪有那么多喜不喜欢,只要他不敢打你骂你,这不就挺好?”
红柳又落下眼泪,爹也是这么说的。
那次红柳深夜骑马回来,爹便对她说:“当匪终究不是长法,更何况是一个女孩儿,还是要找个好人嫁了。”
那时她便失神地想“好人,好人,他确实是好人,但不喜欢,他不喜欢我。”
现在哥哥又这么说,到底要过什么日子,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红柳说不出来,只倚在路四海身上哭,哭了一天觉得憋屈,起身到后面练枪,震得林鸟乱飞,一地野鸡、兔子乱窜。
沈素节远远看着发疯的聂红柳,忽有人拍上他肩膀,回头一看见是路四海。
素节轻声跟路四海说话,路四海拍他肩膀让他往前看,点拨一般地说:“这样的女人还不好?是野了些,比不上你们那些大家小姐,但不矫情不闹妖,我妹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她为了你,连胭脂水粉都擦上了,难道不让你打心眼里喜欢?”
“为了我?”沈素节疑惑地看着路四海,原来她以前是不抹脂粉的。
“我妹妹,从小骑马,劫富济贫,不怕死不怕伤,自从见了你,学着小步走路,学着涂脂抹粉,学那些什么千金小姐说话。她并不是全为了匪商联合才嫁给你的,她是看上了你小子。”路四海顿了顿,脸上现了匪气接着说:“否则,管他什么联姻,就是我义父也降不住她那性子。她手上可是沾过血的,哪管你什么父母之命。”
沈素节远远看着在林子里骑马横冲直撞地聂红柳,心里起伏了很久。她心里肯定很委屈,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正眼看过她,现在想要夫妻和谐,又不得其法。
沈素节知道这其中的关窍在于自己从没将她放在心上,未曾了解,便轻率定论。
沈素节心里感慨:“我浪费了三年好时光,她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