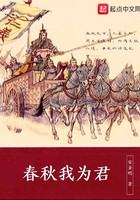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八月二十四,中秋已经过去了十天了。为了不让黎潇潇黏上他,段凌云天不亮就出门了,不到中午就到了清江浦。
用完晚饭后,闲来无事他想去街上走走。
盛四叔的酒铺在石码头街的中间,老远就能看到一个大大的”酒”字招牌。
看到段凌云,盛四叔热情地打招呼:“客官是要打酒吧?小店的绿豆烧,纯豌豆酿造,配以红参、当归、杜仲等50多味草药,不光好喝,还可以舒筋活血!给您打点?”
“那就给我打个两斤尝尝?”
“好咧,六十制钱一斤,两斤,一百二十个制钱,客官酒您拿好。”
“这是一两,不用找了”段凌云放了一两银锭在桌上,“掌柜的,打听个人。”
“客官太客气了,您要打听谁?”盛四叔满脸堆笑道。
“有个汪公子不知道你认识吗?听说经常穿一件淡青色的缎子长衫,每个月都会来你这打几斤酒。”段凌云问道。
“今天是怎么了,上午也有一个生的很俊的小公子也在打听他。”盛四笑道。
“哦?”段凌云忙道,“那人长啥样?”
“十来岁,模样长得很俊,嘴很甜,衣服料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只是眉毛弯弯的有点太像女孩了吧。”
段凌云已经知道是谁了。
“这个鬼丫头,还是没躲掉。”他心里骂道,“这位公子,掌柜的知道他住哪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他问完,就往西街走了。”
段凌云好奇道:“他问了什么?”
“他就是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汪公子名字,哪里人,住在哪,还有赌场的传言是不是真的。对了,说到赌场啊,”盛四忽然神秘地看着段凌云,“您还不知道吧,明天泗淮帮的段七爷还要来和这位汪公子过招呢。”
“您怎么知道的?”段凌云皱眉道。
“陈小四说的啊!汪公子在他们赌坊的事可不都是他传出来的嘛。”
“这个陈小四!”段凌云心里骂道,后悔自己怎么就忘了多提一句。
泗淮帮在这一带的势力虽大,但黎老当家却一直告诫他们为人低调,如果这事传入爹的耳朵,一顿臭骂那是免不了的。
“是嘛,那我肯定是要去瞧瞧热闹的了。”段凌云苦笑道,“对了,你是怎么回那位公子的?”
“汪公子的名字,这条街估计也没人知道,住的地方听说是登甲巷。这位汪公子不爱说话,不过他说过喜欢喝我家的酒,你别看他年纪不大,酒上却是行家。他提过以前经常喝琼花露,还有点扬州口音,我猜他可能是扬州来的。”
琼花露是扬州名酒,早在宋代,有人取扬州大明寺号称天下第五泉的泉水酿酒,取名琼花露,味极美,名闻海内。
“是的,琼花露是扬州的酒,您继续。”段凌云道,心里愈加怀疑了。
“这位汪公子第一次来我这打酒是去年腊月,,那时他在街西头摆摊代写家信状子之类,生意挺好的,人们都说他文章好,字好,价钱也公道。”盛四忽然低声道,“只是今年过完年,本县的知县换人了,新任周知县公告说严打诉棍,民间就不给写状子了,他的摊子也给拆了…现在要写点东西只能去县衙找衙门的文书,价钱要三倍以上…”盛四说完摇了摇头。
这种事情段凌云见的多了,已是见怪不怪了,“他的摊子拆了后呢?”
“他之后他就很少在这条街上出现了,只是定时每个月底,会来我这打几斤酒。哦,中秋那天,他还来过,向我赊一斤酒来着。你说这个汪公子真是奇怪,非要把自己活成这样,陈小四说在他们赌场,只要他真想赢,一晚上千八百两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盛四叔摇摇头,一脸的不解。
“多谢掌柜的了,今天陪我聊这么久,耽误您做生意啦!”
“客官客气了,不耽误,不耽误!”
“那掌柜的生意兴隆,咱们回见。”
“谢谢客官,您慢走!”
盛四叔看着段凌云的背影,喃喃道,“这个汪公子到底是什么人呢?”…
八月二十五,大行皇帝驾崩民间三十天的国丧期终于过去了,石码头又恢复了往日的灯红酒绿。
清江客栈每天下午酉时初营业,段凌云吃过晚饭后就早早到了。客栈的吴掌柜正在二楼的一间雅间陪着他。
清江客栈一楼的大厅摆着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已围满了人。天还大亮,但赌场关门了一个月,赌徒们早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这个雅间的位置绝佳,大厅里进进出出的人可尽收眼底。
两人在雅间说说笑笑,但段凌云的心思却明显不在这边,不时地看着门口。
酉末时分,他还是没看见黎潇潇,正焦躁着,忽然听见楼下一阵骚动,传来了陈小四兴奋的声音,“汪公子,您来啦?”
段凌云赶忙起身,扶着雅间的栏杆向门口望去。
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瘦削颀长的身材,棱骨分明,面色苍白,穿着一身青灰色的棉布长衫,正目不斜视地缓步进来。他的穿着虽然普通,但举手投足之间却有一股不凡的气宇。
正是陈小四口中的那个怪人!
怪人见陈小四跟他打招呼,点点头,笑了笑。
人们见他过来,都不自觉的让开了一条路,他也不客气,径直走着,在一个牌九桌前站住了,那张桌子的人都停了下来,看向了他。
有个人起身,“我今天手气不好,不玩了,汪公子您来。”
“多谢。”他向那人拱了拱手,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四人的桌子,玩的是小牌九,小牌九只凭运气,输赢立现,在本地最为流行。
出门坐着的那位明显局促起来,他和这个汪公子交手过几次,但似乎已经有阴影了,“汪公子…我今天手气背…也输了不少了…你看…”支支吾吾道,他倒不是输不起几两银子,但和他交手那种被支配的感觉可比输点银子难过多了。
末门的一位掌柜模样的中年男子很直接:“咳咳..汪公子,我就是手痒过来瞎玩玩,您是高人,犯不着赢我们的几个小钱啊,要不您屈尊去别桌看看?这五两银子不成敬意,您请笑纳!”他今晚手气好,已连赢了好多把,可不想此时触这个霉头,坏了运气。
人群一阵骚动,五两银子不少了,是一个小康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这位掌柜已经很有诚意了。
看着左右两门的怂样,天门的络腮大汉一脸的鄙夷,“你们两个怂包蛋,竟怕成这个鸟样!他不也是两只肩膀就顶着一个脑袋么,有什么好怕的?”
转向怪人:“我听过你,你就是那个姓汪的小子?”
怪人淡淡道:“抱歉,打扰各位兴致了,各位继续。”
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就要走。
“你坐下。早就听说这里有个高人,我早就想见识见识。”看了左右各一眼,大声道:“你们两个坐好,陪爷再玩几圈,赢了算你们的,输的算爷我的。”
人群又是一番骚动,此时更多人都围了过来。
赌徒最要面子了,两个人的脸色霎时变得非常难看,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尴尬不已。
就在这时,有两个人走了过来,一个掌柜模样的抱拳道:“两位兄台,鄙人是这里的掌柜,今天正好有位朋友过来,对这位汪公子倾慕已久,不知两位兄台可否割爱,位置让与我们两人?”
来人正是吴掌柜和段凌云。
两人正是求之不得,起身回礼,:“既然是掌柜的说话了,这个面子自然是要给的,两位请。”让开了座位,站在了后面。
“多谢!”吴掌柜和段凌云同声道。
“汪公子请坐。”吴掌柜示意。
怪人坐了下来。
吴掌柜坐在初门,段凌云在末门,天门是那个大汉。
周围的人立刻围满了一圈,霎时间大厅已经水泄不通。
段凌云看了怪人一眼。
这个人眉如剑锋,鼻梁直挺,一张脸棱角分明却并不生硬,似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
“鄙人段凌云,对兄台,神交已久,今日得见,兄台果然是霁月清风,器宇不凡。敢问兄台哪里人氏?”段凌云拱了拱手道。
“足下过誉了,鄙人只是一介村夫,怎敢担足下如此评价。四海为家,也无所谓来处,足下请。”怪人回礼淡淡道。
“是在下多言了,玩牌玩牌。”段凌云忙道。
“第一局我看就由汪公子做庄,两位意下如何?”段凌云看着吴掌柜和那个大汉道。
“汪公子虽然不常来,但大名在本店也是如雷贯耳,汪公子坐庄那是自然。”吴掌柜道。
“我没意见。”那个大汉道。
他们都想看看这个怪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如此在下就却之不恭了。”怪人向三人拱拱手,开始洗牌。
这是副牛骨牌,背面是竹片,正面是牛骨,材料很普通,但整副骨牌明显是精修过的,没有任何瑕疵斑点。
三人盯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指瘦长纤细,指甲也细致地修剪过,一双手正在骨牌上摩挲,动作并不快但手法熟练,牌已经完全打乱。
段凌云突然闻到一股清香,扭头一看,黎潇潇果然来了。
黎潇潇今天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绸缎长衫,头戴一顶瓜皮黑色小帽,显得英气逼人。
她其实早就来到赌场了,也在楼上的一间包间里,见段凌云和吴掌柜下楼,就尾随他们下来,好不容易才挤进来。
看到这个怪人,她的目光就再也离不开他了,她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怪人就是汪家大少爷汪连章了。
来清江浦之前,她已经去过扬州了。她去了静园,向多人打听了汪大少爷的模样。
说到汪家大少爷,无一人不摇头叹气。扬州府会达殷振,人文鼎盛,但上一个状元也是百年之前的事了,大家都看好汪家大少爷是最可能成为下个状元的扬州人,但没想汪家却一夕败落,汪家大少爷也不知所踪,怎能不让人唏嘘!
静园高墙深院数百米见方,但已然物是人非。大门上两道封条已经枯黄,大门口满是枯黄的败叶,从门缝里望进去,园内的荒草已有半人高…
段凌云见着黎潇潇,刚想开口,黎潇潇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示意他怪人已经码好了牌。
“三位还要不要再洗洗?”怪人扫了一下三人,问道。
段凌云和吴掌柜摇摇头。
“我来。”那个大汉道,随即上下左右换了换牌。
“请下注。”大汉道。
“一两。”怪人掏出一锭一两的银子放在桌上。
“我跟一两。”吴掌柜道。
“一两。”
“一两。”
大汉和段凌云也下好了注。
怪人不紧不慢地抓起来两只骰子,随手掷了出去,三人盯着他的手目不转睛。
骰子碰撞骨牌后迅速停了下来,三、四七点,天门右起三列揭牌。
大汉拿了两张牌,右手抓着,左手食指轻轻地抹了一下牌面,放在了桌面上。今天运气还不错,一张板凳,一张杂五,四五九点,他略有得意地看着对面汪连章。
段凌云和吴掌柜也看过了牌,放在桌上,看不出来牌色如何。
“我先开!四五九点。”大汉道。
段凌云也翻开了牌,一张板凳,一张丁三,七点。
吴掌柜的牌面是一张长三,一张梅花,六点。
怪人慢慢地掀开了牌面。
“地高九!”有个人惊呼。
地高九自然通吃,怪人这局赢了三两银子。
“汪公子,运气不错!”段凌云道,“请。”
示意他继续洗牌。
这里的规矩,庄家如果通吃,将继续坐庄,直到有人赢了他为止。
怪人不紧不慢地码好了牌,示意三人切牌。
“我先来。”大汉道。大汉这次明显认真了很多,他自信他这次的切牌已绝无规律可循。
“我也来一下。”段凌云道。
段凌云的手法就比大汉熟练多了,只见骨牌在他的手里上下翻飞,一道道的白光让人目不暇接,人群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须臾之后,两排骨牌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牌桌中间。
他已经打乱了所有骨牌原先的位置,他自信以他的手法,怪人想记住原来每张牌的位置,已绝无可能。
段凌云示意吴掌柜再切,吴掌柜笑着摇摇头道:“汪公子请下注。”
“一两。”汪连章还是下了一两。
三个人自然也全部跟了一两。
怪人拿起骰子,三个人全都盯住了他的右手。
只见他右手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头搓起了两只骰子,两只骰子在空中飞快地旋转了着,同时碰撞在骨牌上,“啪”的一声,停下来,五,六十一点,还是天门的牌,左起5列揭牌。
大汉不敢再托大,两张牌拿在手心看了看,放在桌面上,看着怪人。
怪人面沉如水,看不出任何表情。
段凌云和吴掌柜也翻起牌的一角看过后合上,一起看向他。
“天杠。”大汉拿起牌,站起身来,重重地拍在桌上,显然对这局他势在必得。
段凌云翻过了牌,面色微红,显然有些激动,有个人发出惊呼:“天王!”人群顿时一阵骚动。
看到段凌云的牌后,大汉泄了气,坐了下来。
吴掌柜的牌是二五七点,自然最小。
全场的目光盯住了怪人。
他还是那副淡然的表情,似乎一切跟他没关系,慢慢地翻开了牌。
“双和!”人群中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大叫。
自然又是怪人通吃。
段凌云激动的心瞬间掉落下来,觉得这个怪人似乎真有些门道。
但这个怪人却忽然站了起来,拱手道:“各位承让,今天多有得罪,在下家里还有事,恐怕要回去了。”
人群顿时嗡嗡起来,这个怪人又要走!
“不行,老子输还没输个明白,你就想走啊,摆上,摆上,继续!”大汉不乐意了。
段凌云也是一惊,“是啊,这才刚来,在下屁股都还没坐热呢,汪公子怎么也得陪我们再玩几局吧。”
吴掌柜站起来,打着圆场,“两位可能还不了解这位汪公子吧,这位汪公子一向只赢几两就走,可从不愿在我们这多呆的,人家那是不想多赢我们的钱,哈哈…”
随即转向了怪人,拱手恭敬道:“这位段七爷是从淮安慕名而来的,汪公子可否赏在下一个薄面,咱们就再玩一局如何?”
段凌云马上道:“是啊,就再玩一局!”
人群中也有人起哄,“汪公子,再玩一局!”
怪人看了看三人,慢慢坐了下来。
“老子还不信了,砌牌砌牌。”大汉撸了撸袖子,示意他洗牌。
怪人双手抓着牌,不紧不慢地洗着,码好后,示意三人切牌。
“汪兄弟,我可不可以要求换副新牌?”段凌云忽然道。
“当然。”怪人还是那般淡然。
新的一副牌很快就拿来了,怪人慢吞吞地洗着,一会儿的功夫就重新码好,示意他们切牌。
“这位兄台,你要切吗?”段凌云问那个大汉。
“我不用了。”大汉道。
“吴兄,你要切吗?”段凌云转向吴掌柜。
“汪公子高人面前,鄙人就不卖弄机巧了。”吴掌柜笑道。
“那我再来切切。”段凌云道。
他的手上加快了速度,一片白光闪闪,众人眼睛都花了,但汪连章眼睛一动不动的,根本就没看,不由地心道:“难道他已经记下所有牌了?”
“汪兄,请下注。”码好后,段凌云示意。
“一两。”怪人还是下了一两。
人群里又是一阵骚动。
“我跟一两。”大汉道。
“我也是一两。”段凌云道。
“一两。”吴掌柜也是。
怪人抓起了筛子,随手掷了出去,这次是三五八点,末门段凌云揭牌。
段凌云用手抹了牌面一下就放在了桌上,不动声色,他知道他起到了双天。唯一比他还大的只有至尊,这个汪公子能发给自己至尊吗?
“鄙人双梅。”吴掌柜一脸兴奋,人群中发出啧啧的声音。
“娘的,真晦气!”大汉把牌往桌上一扔,他起了一条板凳,一条长牌,十点,肯定是最小了。
段凌云双眼盯着怪人,翻起一张天牌,然后慢满的翻起另一张牌,“双天!”人群爆发了,但立刻又静了下来,大厅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能听得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所有人都在盯向了怪人的牌,“会是至尊吗?”人群中有个人忽然道,在静寂无声的大厅里显得分外刺耳。
他慢慢翻开了他的牌,二四、丁三。
“至尊!至尊!”整个大厅疯狂了,没有人还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今天在下的运气好,对不住了!三位请继续。”怪人扔下一两银子,这是赌场的一成的抽水,站起身,作势就要走。
现在就是周围的看客也都能看的出来,他能赢绝不是靠运气了。
段凌云忽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掷点数简单,他段凌云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掷出想要的任何点数。牌是特制的新牌,没有标记,但每一张上竹子的花纹终究有细微差别。如果一个人真记住了每一张牌,那自然不可能会输。
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凭这些微小的差别就记住每张牌,这份眼力和脑力可就太可怕了!
但这却激发了段凌云的血性,他胸中的一股豪气瞬间迸发出来,大声道:“兄台请留步。
兄台刚才坐庄的风姿实在让人倾倒,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见识过兄台闲家时的风采。”见怪人停住了,继续道:“兄台可否与在下单独再玩一局,这局在下做庄,如果兄台赢了,这一千两恒升号全国通兑的银票在下双手奉上,如果在下不小心赢了兄台一点半点,在下在临江楼订了一桌便饭可否请兄台移驾一叙?”
这个条件实在不是条件。
人群中有不少认识段凌云的,开始交头接耳,嘴里发出啧啧艳羡的声音,能和漕帮第一大帮的段七爷攀上一星半点的关系都足可让人羡慕,更不必说段凌云的意思已这么明显。
“在下只是一介村夫而已,实在不敢高攀兄台,也无意兄台手中的银票。在下家里还有点事,就先告辞了!”怪人笑了笑,向段凌云拱了拱手,脚下已经迈开了步子。
人群爆发出一阵哄哄的声音,都觉得这个怪人肯定是一个傻瓜。
“兄台可是扬州静园的汪家大少爷汪连章?”见怪人要走,段凌云一急,脱口而出。
怪人身子颤了一下,停住了,慢慢转过身来,盯着段凌云:“兄台是怎么知道在下的?”
言语间已经默认了,他就是汪连章。
段凌云其实早就认定此人一定是汪连章无疑,但又心存侥幸,等一切尘埃落定,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凌潇潇看着汪连章转过头来的那张瘦削苍白的脸,眼圈里含了一晚上的两滴泪终于忍不住地掉了下来。
“额..额..兄台果真是汪大少爷,刚才在下就有些冒失了,这场赌局怕也不太合适了…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汪兄可否借一步说话?”段凌云摸了摸鼻子,轻声道。
众人面面相觑,都被忽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就在此时,只见一个衣衫褴褛,黑瘦的少年,用力拨开众人,扑通一声扑倒在地,抱着汪连章的双腿就放声大哭,“哥,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连升?”汪连章定睛一看,大惊失色。
来人正是汪连升,汪家前管家汪荃之子,小汪连章两岁,十一年前去世,留下独子汪福,后被汪之敬收入汪家族谱,齿序列为次子,改名汪连升。
“哥,家里出事了!”汪连升抽噎道。
汪连章眼前一黑,身体晃了一下,赶紧用手撑住圈椅的靠背。
众人也被这突来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大厅里鸦雀无声,都呆呆地看着他。
汪连章定了定神,向段凌云抱拳道,“兄台,请问高姓大名?”
段凌云抱拳回礼:“不敢,在下淮安河下镇泗淮帮段凌云。兄台家门变故,在下之前也略有耳闻,既然兄台的家里人来了,在下也不便再多说什么,希望兄台多多保重。兄台的为人和风骨在下佩服,今后只要有需要在下的地方,请随时言语。”
他今天确实想交下这个朋友,但此时似乎已不合时宜。
“多谢兄台,在下改日定当拜谢!”汪连章向段凌云微微垂首,拉起汪连升大步地离开了。
大厅里轰地一声炸开锅来,知道扬州静园的人顿时成了人群的中心。
而凌潇潇一时还没有从这个变故中回过神来,望着汪连章离去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