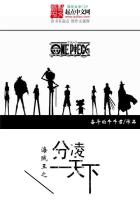天女之怒,罗刹之怨,只见又一根金丝飞出,只是这一回,目标不再是耳垂了——
“啊啊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那许季泽完全来不及闭眼,金丝便准确地穿过瞳孔,刺进他脑中,一只眼睛顷刻废了,大脑被刺穿的痛楚也随之炸开!
“啊啊啊!我的眼睛!我的头好痛,好痛!”
“还有一只眼睛,说与不说,你自己选!”
“我说,我说……十六年前的夏天,父亲病重,多次想把我们三兄弟召齐榻前,可那时大哥正出战东海,与鳄鱼帮战事胶着,难以脱身。我和二哥都知道,父亲是在等大哥回来,好将庄主之位亲传于他。其实,大哥许孟泽是归风山庄第十四任庄主的不二人选,这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人人都说好,人人都心悦诚服,可我和二哥偏不服!”
许铭扬似乎想起了什么,却不肯相信,瞪大眼睛:“不可能!父亲他一向敬重大伯父,叔父也是,大伯父是英雄……不可能!我不信!”
“铭扬,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儿子,归风山庄总有一天都是你的,所以,你永远不会懂兄弟之情的复杂和矛盾。是,大哥是长子,品行是出众,人人都夸他,可长子如何?品行出众又如何?凭什么一母同胞,他许孟泽就得父亲青睐,就得众人青睐,而我和二哥却只能做灯下尘?你知道什么是灯下尘吗,明灯下的灰尘……因为有了那盏灯,灰尘的平凡渺小就被无限放大,被人笑,被人骂,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角落里,一行清泪从一个美妇人的眼角滑落。
“所以,那天夜里,当二哥偷偷来我房中,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为了庄主之位,必须除去大哥,而我,为了……夏紫,只会比二哥更欲除之而后快!哈哈哈!”
许季泽狂笑着,瞎眼流出血来,像是鲜红的眼泪,狰狞可怖,令人胆寒。
“于是,二哥写信给大哥,想派山庄精锐前往东海援助,好让大哥早日得胜归来,还能见父亲一面。可怜许孟泽到死都不知道,许仲泽派去的不是什么山庄精锐,而是重金悬赏的杀手,杀的也不是东海鳄鱼帮,而是他这个大哥!哈哈哈!”
“我不信!呜哈哈哈!我不信!我父亲光明磊落,不会做这种事,永远不会!”
许铭扬凄声大笑,他的父亲,是堂堂归风山庄十四任庄主,教他广结良友,教他锄强扶弱,告诉他做一个大伯父那样的英雄儿郎,这样一个父亲,怎会做这种悖逆天伦的事?
他不信,他许铭扬不信!
角落里,一个美妇人有些异样,身体似是在动,准确地说,是在痛苦地颤动。
中了她文锦绣的软骨香,就算是绝世高手,那也是丝毫动弹不得,怎么,那个人,身躯里似乎承载着巨大的痛苦,连药力都压制不住了。
文锦绣走近几步,只见一张女人脸庞,虽然上了年纪,留下岁月的痕迹,但依旧美丽动人的脸庞,这一刻,竟满是泪水,眼睛里是深渊般的哀恸和恨意!
“你,你要做什么?!有什么冲我来!离她远一点!”
狡诈贪生如许季泽,见文锦绣靠近那女人,却焦急如焚,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救,再看那女人的眼神,恨意决绝,文锦绣只觉当中有趣,一根金丝飞出,缠上女人右腕。
“妖女!我杀了你!放开她!”
脉象看来,这女人非练武之人,也罢,且放了她,看看这当中有什么故事。
文锦绣玉指一弹,一滴晶莹的液体便落在金丝之上,顺着那金丝滑至女人腕部。
液滴触及皮肤就迅速沁入,女人只觉一股凉意从腕部化开,直至肘部、肩部,直至五脏六腑,最后整个身体都能动弹了。
软骨香已解,不过身体的麻木感还没完全过去,那女人挣扎着,才能勉强起身。
“夏紫……”
许季泽用一只眼凝视着女人,轻声唤着,声音充满柔情和担忧,似乎还有一丝愧疚。
“婶母……”
许铭扬也看着她,步履蹒跚,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瞎了一只眼的夫君。奇怪的是,婶母眼中,不是为叔父担忧的神色,那种感情,那种强烈到无以复加的感情——是恨!
“你杀了他?”
她的声音,并不像她的眼神那样决绝,听起来还像少时初遇,她粉颊梨涡,清浅笑语,还像今日早晨,她为他盛一碗小米粥,轻言一句当心烫。
她无疑是爱着大哥的,否则她的眼中不会有那样的决绝恨意!
然,她并非对他无情,否则,她不会在真相昭昭之后,多此一问……
许季泽叹了一口气,用那只独眼凝视着她,轻声说了一个是。
她没有骂,没有哭,唯一行清泪从眼角滑落。
是啊,她有什么资格骂,又有什么资格哭?作为许孟泽的遗孀,她带着他的孩子,嫁给了他的弟弟,她自己认贼作夫,还让孩子认贼作父!
想到这里,夏紫忽地想通了什么,一双美丽的眼睛,带着惊愕和质问,直勾勾地盯着他。
她说不出一句话。
她想问,又不敢问,只怕问出的答案,真是自己猜中的那一个……
“夏紫,我对不起你,博儿也是我们杀的……”
这下子,女人完全崩溃了,疯狂地捶打那人的胸口:“你为什么杀他,为什么要杀他?!博儿他才十二岁,他是我的孩子啊,你怎么可以杀他?!”
夏紫彻底崩溃了。
如果说听到许孟泽死亡的真相,她的心是燃起熊熊怒火,那么,当得知儿子许铭博是死在许季泽手下,她的心就是从一把火烧成了灰,彻彻底底,一团死灰。
“夏紫,博儿是你的孩子,为了你,我也一直努力着,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但这么多年来,许铭博,他对我是那样冷淡疏离,像插在我们之间的一根刺,时时提醒我,大哥他曾怎样占据你的心,占据你的身体!我恨,除去许孟泽这堵墙,我们之间却还有一根刺,这根刺在一日,你的心就念他许孟泽一日,你永远不可能完完全全属于我……”
一旁的许铭扬,听到许铭博三个字,一时失控了,那个教他认字、教他算数的明朗少年,那是出头为他抱不平的铭博哥哥啊,眼泪早已夺眶而出:
“所以,当年祭风大典,铭博哥哥不是自杀,而是叔父你……”
“不,把他推入湖中的人,是你。”
“我没有……”
没一会儿,许铭扬似乎明白了叔父所指,一双清亮的眼睛慢慢枯空了,自言自语道:
“没错,是我,如果不是为了保我庄主之位万无一失,父亲他就不会对博哥哥下手……没错,就是我,是不是我推的,都没有分别……”
“啊哈哈哈,哈哈哈……”夏紫已然疯了,笑得凄厉诡异!
随即,她拔下头簪,铆尽全力,插进了那人的腹中。
那个,背弃了良心和人伦,只为爱她的男人。
许季泽受此重创,呛出一口血来,气息奄奄:
“我怕死,可是我不怕死在你手里,如此,你眼里有我,我死而无憾……”
“哈哈哈哈!你错了,你说你是灯下尘,恨明灯放大了你的平凡渺小,所以你们集结起来,蒙住了那盏灯,可你忘了,没有灯,没人看得见尘。”
“夏紫!”
不甘,不舍。
男人用独眼凝视着她,铆尽全力喊出这个令他魂牵一生的名字,终于咽气,死了。
“婶母——不要!”
可惜,已经晚了……
夏紫又将簪子扎进自己腹中,血,汩汩流淌,人,倒在了男人身上。
尘,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无时无刻,不在我的生命里。
就算有一天,我容颜老去,腐化成泥,它还在那里,与我相拥,永世长眠。
也许,我也错了?尘,我早已习惯它的存在,我以为自己看不到它,其实,我满眼是它。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许铭扬颓坐在地,嘴里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对一个从来无忧无虑的人,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撕碎他眼中那个光明美好的世界,彻彻底底,不留一丝余地。
在他心中,归风山庄是何等神圣,那座忠魂故里的牌坊,是他许铭扬一生最大的荣光。他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铭扬你要成为大伯父那样的英雄,那个人仿佛一盏明灯,即使遥远,也能照亮他的方向,而父亲还经常拿伯父的品行事迹来鼓励他、教育他。
可笑啊可笑!父亲心里早就承认了伯父的出众,甚至不自觉地引以为傲,可是,当妒忌燃烧起来,渐渐超过了这份引以为傲,再烧得旺些,超过了手足之情,最后,妒忌的厉焰连理智和良知都烧得干干净净,等他成功夺走他妒忌的一切,这火便渐渐熄灭。于是,他转过头来,捧着一把骨灰,告诉自己的儿子,你的伯父是个英雄,你要像他一样,坦坦荡荡,仗义行善,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真是可悲……
这归风山庄,又有谁不可悲呢?父亲,得了庄主尊荣,却永远不敢在儿子面前,理直气壮地说一句,儿子就要像他老子一样。叔父,想尽办法得到兄嫂,拆了一堵墙,却永远拔不掉心里的刺,爱恨交加,自我折磨。而我?哈哈哈,许铭扬啊许铭扬,你无忧无虑活了二十年,到今天才知道,这无忧无虑的二十年,是拿你最敬重的伯父、最亲爱的堂兄换来的!可怜你学什么扶弱锄强,你自己就是那最大的恶人……
“绣丫头——”
文锦绣听这熟悉的声音,转过头去,原是铁连生率领烈火骁骑军,已迅速包围整座山庄。
“铁叔,我……”
铁连生见文锦绣有些局促,自行查看了一番,见许仲泽、许季泽、夏紫已经断气,徒留许铭扬一人,颓坐在地,自言自语。主上曾特别叮嘱,尽量不波及夏紫,如果情况允许,最好四个人都留一命,绣丫头办事向来尽心尽力,准是在为此事自责。
“别多想了,此次任务着实艰巨,绣丫头你已经立了大功。”
文锦绣点点头,将事情原由一五一十告知铁连生。
“唉,真是可悲,我看这归风山庄,真真一个悲风山庄!你本留了他们一口气,只是天道循环,两个罪魁祸首,一个砸死在儿子身下,一个死在妻子手里,也是因果报应!”
说着看了一眼许铭扬,一身喜服依旧鲜艳,但那双清亮的眼,已如一潭死水。
“可怜这许少庄主,品性纯良,是个可塑之才,但此事过后,怕是也废了。”
“铁叔,现在如何处置?”
“你先给他们解毒。”
“可……”
“无妨,主上只是要他们,”铁连生说着,指着地上一干人,“清清醒醒,听完这份诏书,明明白白,将归风山庄物归原主。”
“是!”
又见红裙飘飞,文锦绣在空中旋转着,无数晶莹液滴自袖中飞出,犹如天女飞霖,洒下神圣的恩惠,所到之处,人人都得解救。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沧奕纪年四百二十八年,护国大将军许孟泽,于东海鳄鱼帮一役壮烈殉国,追谥‘武勇’。今,沧奕纪年四百四十四年,查实武勇大将军之死因,乃其二弟许仲泽、三弟许季泽密谋刺杀,罪已供述,人证俱在,是为结案。许仲泽、许季泽二人主谋,密谋弑兄,残害忠良,现缉拿归案,秋后问斩。其余亲眷、属下,凡直接参与者,同罪;不知情者,念其乃武勇大将军之一脉,着以流放东海,永不召回;许仲泽之子许铭扬,年纪尚轻,品性纯良,念其往日善行,特赦死罪,即刻发配西南充军,无诏不得回京。布告天下,咸使闻之,钦此!”
“为何不杀了我?为何不杀了我?”
许铭扬无神地看着铁连生,眼睛如同两潭死水,喃喃着。
“主上在陛下面前保你一命,你该知足。其他人,谁还有异议?”
只见这一大家子人,或惊讶,或悲痛,或心虚,或恐惧,世间百态,人相千种。
“我不服!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归风山庄的家事,还用不着你朝廷来插手!”
这一喊,便开了头,剩下的人,尤其那些同罪当诛的人,索性破罐破摔,跟着叫嚷起来:
“是啊!我归风山庄百年基业,上上下下千百号人,你们说杀就杀,说流放就流放?”
“是啊!归风山庄为姑苏城做了那么多,为江南做了那么多,如此功劳,你们怎不记着?”
“你们也得想想,这毕竟是武勇大将军的家,难道不顾及他在天之灵?”
……
“就是顾及武勇大将军在天之灵!”铁连生拔剑怒指,“你等鼠辈,当日为一己私利,谋杀自己的主子,谋杀忠臣良将,今日,怎么还有脸以他之名跪地求饶?我铁连生平生最恨这等蝇头鼠辈,你们不妨看看,你们自己,还配不配得上归风山庄这个名号!”
说完扔出数封帛书,帛书之上,清清楚楚,他们如何在甘昱若王宫安插密探,如何在军中安插眼线,又如何在黔州购置田地、招军买马,一五一十,毫无差漏。
这一下,几个人惊慌无状,终于哑口无言。
“你归风许家再大,也不过是个家,你们不该将这‘家’误当做‘国’,狼子野心,阳奉阴违,欲与正主争锋!十六年前弑兄夺位,十六年后还想弑君称王,如此心机与狠决,怎么不放在战场上,不放在敌寇身上?!”
“哈哈哈哈!你们说得对!你们说得对!”
只见那许铭扬摇摇晃晃站起身来,发丝凌乱,眼睛充血,大笑着,突然往门柱冲去。
这家伙想一死了之!
“不好!拦住他!”
铁连生喊着,连忙跃起直追。
文锦绣心头一紧,也急忙发出金丝欲往回拉。
奈何解了脱骨香的许铭扬,轻功远在他二人之上,眼看就要撞上门柱——
却忽感一阵疾风,自门口旋入。
说是疾风,其实比风更快,比风更有力,就那样——稳稳拦下求死的许铭扬。
“小云,你怎么来了?”
这身手,除了他陆行云还有谁?铁连生一下认出,走上前去。
陆行云脸上一如万年寒冰,没有回答的意思,径直朝倒地的妇人走去。
堂中几名老者,见到身着铠甲、大步向前的陆行云,以为自己老眼昏花,竟见到许孟泽的鬼魂,面面相觑之后,连忙跪倒在地:
“老奴……恭迎少庄主回庄!”
陆行云也不理,只大步向前。
他径直走到许季泽夫妇跟前,看着二人的遗体,眼神复杂,随即,他扔下一枚桃花玉佩,抱起夏紫的遗体,去也如风,只剩一语在堂中回响——
“祭风大典,报国一诺。许铭扬,你给我好好活着!”
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
那如风的年轻人是谁?
他为何带走了夏紫的遗体?
他又为何救下求死的许铭扬?
唯有一个人,再清楚不过——
许铭扬眼角滑下一滴泪,嘴角却泛起笑意。
“是他……他还活着……”
许铭扬笑了,却是那么苦涩,当年的兄长铭博,言笑晏晏,骑马射箭,好一个明朗少年,而今,成了身着铠甲的大将,脸上却再没了笑容。
是这样可悲的归风山庄,将他冻成了冰。
他带走夏紫的遗体,却永远扔下了归风的信物,许铭扬知道,他这一走,便不会再回来。
不是所有的爱恨都能释怀,也不是所有的悲哀都能消潜。
这归风山庄,这悲风山庄,不回也罢!
“归风山庄所有人听令!”
众人望着那身着喜服的人,衣发尽乱,额角还有血痕,但眼神却是从未有过的清明:
“我,许铭扬,归风山庄第十五代庄主,今日接旨!武勇大将军一案,我归风山庄甘愿领罪,从今往后,归风山庄废其名号,从武勇护国大将军之号,改名护国山庄,交由甘昱若整饬掌管。我许铭扬在此辞去庄主之任,从今往后,江南姑苏,再无归风,再无许家庄主。”
这一日,姑苏由晴转阴,天空飘起小雨。
百年归风一朝散,护国山庄,从此收归甘昱若军用。
时年沧奕纪年四百四十四年,四月,清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