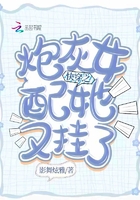这里是一间发明家办公地点的小房间,杨仲身穿病号服坐在椅子上耸拉双肩,十分无助地面向一台他不确定是不是录像机的机器,诉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穿越经历。“就是这样,当我重见光明那一刻,我从天花板掉落到一个女人的怀中。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被软禁。”话毕,他目光落向单脚戴的钢铁锁环,一脸不甘。
因为富含电子科技的锁环牢牢限制受用者的活动范围,胆敢跑出划定的活动范围以外就立刻释放高压电流并且发送定位。
而此时,有一位女人安静地倚靠在他背后的门框上,身穿齐膝盖的白大褂,发型是刚好齐肩膀的泡面头,金黑相间,一卷一卷的。“我必须告诉你,你一直面对智能家居的物理终端自说自话。”见杨仲对穿越难以置信地双手紧抓自己的头发,她开口提示道。
闻声,他故作淡然地松开双手,“阿达·琼斯,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没回头问道。
“从头到尾都在,前几天你活像个自闭儿童,难得今天敞开心扉说出很多话,我一开始不想打搅你,但现在我们需要谈谈。”
他抬起戴锁环的脚,面向她故问道,“你就让我戴着它跟你谈吗?”
“你说得对,如果没有相互信任,那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
…………
两人坐在单人沙发上,彼此之间隔着一台圆桌子,桌面放着家居终端和刚解开的锁环。“我先说明一点,”她开口解释道,“你人生地不熟,锁环限制出行是想让你慢慢适应生活,毕竟外面有很多东西是你从没见过。”
“没错,”他回道,“我是像个原始人,但适应生活就谈不上了,你们必须送我回去!”
“送你回去?这个问题待会再说。我听到你说起负质量粒子发生器,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他简短地回道,语气充满对于她的拖延战术的不屑,他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
“好吧,”她掏出一张准备好的照片,“那你见过这个人吗?”
这张照片不大,但谈不上小巧,裱有一个灰旧的木框,看起来年代感十足,应该是被珍藏起来的物件。而里面的中年男人只照进去半边身子,整体的脸部菱角分明,头上戴一顶高筒毡帽,目光如炬,嘴里斜叼木烟斗,脖领扎个蝴蝶结,上衣板正有型。
“你到底认没认出来,见过吗?”见他盯着照片不说话,她按耐不住问道。
他又思索了一会,不知在想什么。如果是在加深照片里的人保存在脑海里的印象,那么就说明他已经认出来了。“他是你什么人?”他试探性问道。
“是我的亲爷爷,可我没亲眼见过他,甚至没说上一句话。”
“什么?!”他大惊失色,因为她的爷爷正是那天晚上在豆浆店找事的路人,当时给他的第一感觉并非平常人,因为她爷爷说的话就像是掌握政权的大官,大意是要加强出入境管制,驱逐非法外来人员,因为这些人频繁参加非法活动扰乱治安。她爷爷给他的印象很深。“他是你爷爷的话,那我……”他忽然抓住重点,赶紧问道,“今年是第几年了?”
阿达·琼斯只觉奇怪,但还如实回道,“2077年。”
1984年到现在已有93年的时光偷偷溜走了,也就是说从小到大积累的应对人情世故的生活经验几乎作废,出门讨生活肯定处处碰壁,这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极为不公平的。
“93年……不对!”他情绪不稳地大力拍一下桌子,“你爸再往上数就是你爷爷了,怎么就过了93年?你在耍我!”
“冷静点,”阿达·琼斯抬起双掌,像是要把他的火气压一压。“听我说你就明白了……”
原来,她的爷爷,将一生的心血全放在自认为伟大的事业上——研究打开时空洞的机器,时过境迁,最终生命体征衰弱逐步走向尽头,她爷爷持笔签下将半成品及资料全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去完善,而这个人就是阿达·琼斯的父亲。她的父亲继承琼斯坚韧的品性,同时更为癫狂,接替实验小组的同时,他将精子冷冻,在事业未成寿命将尽那段时间里——阿达·琼斯赫然出世。
阿达·琼斯向他解释道,“精子冷冻是一项辅助生殖技术,在保证精子质量的前提下可以保存精子几十年之久,而我的母亲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所以…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时隔93年了吧。”
只见他一脸死寂,许久,才不善地开口徐徐道:“难怪你的姓氏也同为琼斯,我还纳闷什么情况,你们爷俩可真会捉弄人啊。”
“别这样说。其实我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她欣喜地继续说,“我们家族世代努力想完成的项目一直以来不被人看好,同行把它当成饭后闲谈,但你的出现狠狠打了他们一巴掌,虽然一代原型机毁掉了,可你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
“我不关心这些,我只是一个为填饱肚子奔走东西的普通人,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去,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
“你一定很低落,很伤心,我理解你,可机器已经坏了,你回不去了。”
“二代机呢?!你说一代原型机,就一定会有第二代的吧!你们到底要留我在这里做什么!”
“别激动,只想搞清楚你从哪里来的。”
“那现在你清楚了,也该送我回去了。”
阿达·琼斯见他情绪不太稳定,臀部俏俏离开座椅,方便因对突发状况,这才回道,“你需要知道真相,第二代机器不可能制造出来。”
“我不信!”
见他又是一拍桌子,激动得直接站直身子不知要做什么,阿达·琼斯赶紧向身后的空间躲避,“装配和调试的沉淀的价值,只有图纸没用的!再说了,很多关键零件像西瓜裂成几瓣一样,不可能回收。”她不屈地向他解释,试图阐明情况让他恢复一些理智,殊不知她在火上浇油。
绝望的杨仲怒火中烧,大吼一声欲要掀翻桌子,双手扣住疯狂使劲,没想到桌脚是嵌在地板上的,掀不动,紧接着他抄起家居终端看都不看就随便砸去。话语的倾吐也找不到对象,他太需要发泄了。
“铛!”落处传来钢铁撞击回响的声音,很清脆。他回头一看,只见门口闯进来一个蓝色机器人正拿枪对准自己,地上的家居终端往回滚了几圈,想必是砸到机器人身上了。
“这拓麻什么鬼东西啊。”他紧紧皱着眉头,对机器人上下打量。
“你需要冷静。”阿达·琼斯在角落处对他发出善意的提醒。
“什么?”他没听清别过头,就在这一瞬间机器人手持枪的枪口“咻”的一声射出一根细小的钢针,速度极快。他只感觉脖子被蚊虫叮咬了一下,用手摩挲到针身那一刻眼球接收到的画面随之倾斜,只听“扑腾”一声,他重重跌倒在地下。
周围发出的声音在无限扩大,阿达·琼斯随即赶到他的身边,她的脚步声像隆隆作响的闷雷。“只是麻醉剂,你会没事的。”她蹲下身对他温柔地解释道。
“你麻……”他对机器人咒骂一句,倔强的眼皮也慢慢落了下来。
“嗞—嗞—”机器人脚步生风,上前走来,驱动电机发出一阵运转的电流声。
“你不能带走他。”阿达·琼斯拦在它身前,“他是我的客人。”
机器人停住脚步,单镜头聚焦式的眼球上下滚动,扫描识别到阿达·琼斯的身份是公司职员后立刻就收起枪支,转过身昂头挺胸地离开了。
“冰冷的机器永远只能是机器,无法制造信息素,更没有镜像神经元,只会依靠中央处理器识别并执行指令。”她轻蔑地嘲讽一声,现在房间只剩两个人,看着杨仲,她又不免微微犯愁,“这个原始人,要如何安排才妥当呢?”
…………
时间渐晚,透过窗户可见高低各不同的摩天大楼以及墙上近百平米的超大广告屏,像一面光墙的广告一直循环播放钢铁假肢的精密细节,空中飞过三两只摩托大小飞行载具,这些事物,所有的奇景异象都是他前所未见的。
到处是彩光污染,人造灯夺走了本该漆黑的天色,这座几乎由广告牌组成的城市让人无所适从。
“我必须振作起来!”杨仲站在窗前思绪万千,既然无法回去,那也不能安于现状,一般人经历世界观重组的人生悲剧心态不免会崩塌,但他有绝对的信心白手起家,也清楚当下该做什么事。
他在这间高层房间醒过来已有半小时左右了,房间布设极度简陋,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单人床,厕所的镜子旁边放着垃圾桶,没有能看新闻的电视,没有任何娱乐措施。一开始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身处牢房,但很快,他就联想到更多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大抵是关于赚取安身所需保证的经济状况。他现在身无分文,而人员流通量大的城市,房价只会越来越死贵。
遥想1984那个晚上,他那几个伙伴负伤窘境,和阴险的二宫王允有不可化解的矛盾,就算他们死里逃生,日月推移93年,理应全都不在世上了吧。
他也有过一段十分开心的日子,虽然很短暂如昙花一现,但就是这样才更显难得珍贵。他自愿用强壮的后背替乔安娜挡子弹,可乔安娜没能逃出生活的戏弄,在下大雨的夜晚被发明家斯嘉麗接走,等待她的,将是一个填满液氮的冰棺材。
可以说人体冷冻就是葬礼的一个变种,虽然他万分思念乔安娜,但头脑还是很清醒,知道人体在自然死亡前冰冻起来今后重生是不可能的事。世界这么大,他是个没有同伴的原始人。生火、捕猎、藏身处建造全得靠自己。
“滴——”突然,房门传出一声电子开锁响声后向内打开,阿达·琼斯手拎一个购物袋赫然出现在门外。她不用敲门,想进就进。
“你身体素质比我想象的还好,我以为你还没醒呢。”她边走边说,语气就像和一个朋友在闲聊。
“我一直在等你,想跟你道个歉。”他勉强堆笑,遮挡锋芒,心底十分清楚她是需要巴结的对象。
“你发泄情绪的方式的确很不理智,如果乱砸东西能让你好受点,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将购物袋扔在床上,继续说道,“刚下班出门给你买了一套衣服,不知道你的尺码,试试合不合身吧。”
“太谢谢了。”他欣喜地拿着衣物走进厕所内换了起来。而阿达·琼斯望着他进门时的背影,眼神耐人寻味。
看向镜子里换上新衣服的自己,一个黑色修身皮夹克和深蓝牛仔裤,内衬深灰色T恤胸口画有一颗绿色的发芽草苗子。女人的心思是很细的,这颗苗子可能是指她对自己抱有很大期望,也可能没有任何象征性的意义。
他转动水龙头顺便洗一把脸,清冷的水能让头脑保持清醒。对于自己来讲,阿达·琼斯牢牢地掌握他性命攸关的未来生活,决定他每个清晨醒来,是待在干净的房间吃营养早餐,还是一副肮脏流浪狗的模样,狼狈地翻找垃圾桶的食物残渣。
没有现社会的生存经验,难以自力更生的他,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就是巴结她,展现自己剩余不多的价值,首先当然是要保持宾客礼貌,身位社交性的稍远距离,不让她有反感的机会。
“你换好了吗?”她站在原处伸长脖子,好奇地大声问道。
只听“咔嚓”一声,厕所门向外打开,杨仲微笑着从里面徐徐走出,“衣服我很喜欢,太合身了。”他抖擞外套一边说。
她对他上下打量后,很显然对衣服上身效果十分满意,但是却没有说话,气氛就此僵住。
“你…没有要说的吗?”他打破尴尬问道。难不成这个女人只是来给自己送衣服?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值得关心,他最在意的是自己该何去何从,最好她能帮自己谋份生。
“我习惯换位思考,但公司没有你能做的职务。”她终于开口说话,一针见血。
此话让他如被天雷击中,一部分是担忧自己,另一个原因是惊讶这女人有如此聪明的头脑。既然她能揣测心中所想,那么自己再藏着掖着也没意思了。“我可曾替你爷爷干过活,我和他之间是同事。”他厚脸皮解释说。
“我一点也不了解我的爷爷,甚至没见过我亲生父亲,你和我说这些做什么?”她歪着头不解地问道。
他一下子又抓住重点,决定扯一个弥天大谎,只要能和她搭上关系的话,就不会放任自己不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