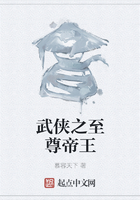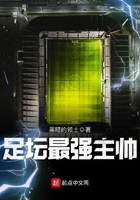济北王并没有想过,真到成亲那一日,他心里能这样平静。
冯翊公主帮他料理婚事,因笑道:“早知道最终还是要进我家门,先前又何必——”
“阿姐。”他平静地打断她。
冯翊失笑:“是是是,阿弟大喜日子,阿姐就该多与阿弟说上几句吉祥话,贺阿弟心想事成,与谢娘子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济北王微微一笑。他看不见,但是就这么一扫,冯翊竟觉得他往自己腹部看了一眼,不由大窘。她与慕容泰成亲半年有余了,还没有动静。求神拜佛,香火钱去了不少。她有时候疑心,是真自己有问题。
好在天子出征中州,慕容泰带兵去了。这让她多少松了口气。慕容泰虽然不是她心中所想的如意郎君,然而出现在她对穆昭绝望的时候,时机是对的。穆昭娶了皇帝那个年届四十,又黑又胖的乳母,如今很得皇帝重用,她只觉得可怜可笑。她不懂他们男人,要这样的富贵有什么用。
她这个堂弟却孜孜以求,只要谢云然。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这么大。
济北王“看”着窗外,已经很久了。天还没有黑下去。腊月的风。她上次成亲是在六月。六月的风灼热。如今冰凉。
他忽然又疑心起来:“阿姐。”
“嗯?”
“阿姐你说,云娘她怎么又肯松口了。”
他们都说,南平王世子与世子妃恩爱非常。当然昭诩失踪是有些时候了,然而就算昭诩是没了,守孝也要一年。云娘没有等满一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计较这个。他原本是希望她能忘掉他,越快越好。
冯翊漫不经心地道:“大概是……绝望了吧。”
“什么?”
“如果十四郎还在世,当初南平王叔遇害他不出现,玉郎出世他不出现,兰陵在中州闹天闹地,他还是不出现,”她原本想说“如果她改嫁他再不出来,她就彻底死心了”,话到嘴边,就变成,“要不就是没了,要不就是没心肝;他要是没了,云娘以后日子还要过,圣人记恨,不会容她好过,你瞧瞧这些日子上祭酒府上提亲的那些东西,有一个人样的吗?阿弟总算是真心待她。”
他这个瞎眼的堂弟,除了眼睛,也没别的不如人。
没成过亲的小娘子要得多,要家世清贵,才貌双全,又温柔体贴,言语生趣,谢云然当初不就这样么,然后呢——一旦大祸临头,就只剩了孑然一身。她如今该是想开了,想要安安稳稳过完下半辈子。
想到这里,冯翊倒对她生出几分怜惜来。她从前不喜她,是因她毁约嫁了十九郎,如今既然是自家人了——冯翊是个很懂得分清楚自家别家的人。
济北王沉默了。
忽又问道:“听说中州那边吃了败仗,还丢了相州?”
“是有,你姐夫前儿都捎信说要回来,气得很,个个都想着捞上一笔,防着别人和自己抢,先就把九郎和陆四排挤了出去,还有绍将军,要不是阿钊的妹子在宫里受宠,恐怕阿钊都会被他们赶下去,”冯翊不由地冷笑,嘉欣这件事是家丑,对外头不好说,当然他们姐弟是肆无忌惮了,“也不想想,六镇这么好打,怎么当初就劳动李司空、我阿爷、圣人,还有南平王叔轮番上阵?”
济北王听着好笑:元明修哪里做过主帅了——当时的主帅是宋王。不过人都秉着功归于上的习惯往皇帝脸上贴金。还有她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爹,也好意思和李司空、南平王相提并论。
“那姐夫如今怎么打算?”
冯翊最后会嫁给慕容泰,济北王心里也是意外的。当初宜阳王与他说慕容家上门提亲,他还以为冯翊不会点头。看来女人的心思,还真不是他能猜得到。后来冯翊带了慕容泰来见他。
他让他觉得危险。
那种粗犷的、凶蛮的气息,像是弯刀,或者野兽。和洛阳的精致大相径庭。
他与他说他的家乡,部落里的习俗与产出,越过边境来劫掠的柔然人,还有突厥人——“他们是给柔然人打铁的奴隶,住在金山以南,人不多,但是极其凶悍,断发文身,有着铁一样坚硬的肌肉。”
他从他的声音里听出天下之大。他困守洛阳,便以为洛阳就是天下,而洛阳之外——他从不知道有多大。
他甚至都没有办法想象,跟着宋王南下的兰陵,怎么会突然折转去了中州,又怎么得到数万人马,与洛阳拼个你死我活。他羡慕他们的生命力,那些可以不必被洛阳困住,不必被一个宅院困住的生命力。
“不知道,总要年后再做打算吧。”冯翊懒洋洋地说,她不关心这些,那是男人的事。
冯翊也是被困住的人,济北王淡淡地想,虽然她的眼睛是好的。但或者是,大多数女人都不得不被困在宅院里。
外头、外头有什么?狂风暴雨。
“圣人和兰陵……”济北王突兀地冒出一句,“阿姐希望谁赢?”
冯翊:……
“我说了又不算。”
济北王于是笑了,真的,她说了不算,谁说了都不算。谁赢不都是他元家的江山。谁赢了不要钱,不要兵?他有钱,慕容手里有兵,虽然不是太多,这乱世里,也足够让人忌惮了。尤其是在洛阳。
只要是在洛阳,他们就能好好地过下去,无论金銮殿上坐的是谁。
天渐渐就黑了。
谢云然之前提过不大办,也确实大办不起来,无论如何,济北王的眼睛总是不便。都为了他着想,也没有另置青庐,也没有请太多的亲友,尤其是谢家那头,就只让谢冉送了亲,然后就都打发了出去。
人都知道她是再嫁,不能太计较。底下嚼舌根有提起她初嫁,说她初嫁不顺,再嫁又嫁了个瞎子,连从前与她订过亲的崔十一郎都死得不明不白,这克夫的本事,与她那个搞事的小姑也算是不相上下了。
当然谢云然不在乎这些,她已经将玉郎托了母亲,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她想不到真相是这样的,是她连累了昭郎。她不明白济北王怎么会对她有这么深的执念,她并不觉得是因为她。或者是因为他的眼睛,或者是因为当初订亲再退亲,总之——都不会是因为她这个人。
这些话,她也不能与旁人说,连四月都不能泄露半句。
她赶在成亲前把四月许了人。四月起先不肯,哭成了个泪人。她与她说:“我再嫁,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也不能时时回来,玉郎身边没有人,我心里总放心不下,就只能托付你了。”她这才应了。
谢云然也知道这不是最好的,早知道会有这样的变故,就该在南平王府的时候给她找个好人。南平王手下的将官或者昭诩身边的羽林郎,当时没来得及,如今是不能够了。但是也好过——
她只能尽可能多地给她备了嫁妆,尽这一点最后的主婢之情。
七月和十二月跟她进了济北王府。
这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屋里点了灯,灯是给她备的,他用不上。婢子都退了出去,脚步声慢慢近来。他走得不快,即便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她听见自己的心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她其实再没有见过他——父亲说她小的时候见过的,她记不得了。父亲和母亲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肯再嫁,赶在这个时候。虽然三娘那头胜算不是太大,但是昭诩失踪尚未满一年,再等等也无妨。
父亲疑心她是因着那些来提亲的泼皮,安抚她不要多想,阿冉也这么说。母亲就一直哭,说:“这样不好。”
她从前拒绝过的,如今再嫁,她怕他待她不好。
她安慰母亲说:“不会的,他如今再上门提亲,是他还惦着我。”
父亲也觉得不好,他还是喜欢昭诩。
他们都不知道,昭郎就在这里。谢云然忍了忍,没有让眼泪流出来。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谢云然微抬了眸光,看到走进来的年轻男子,他长了元家人的眉眼,清隽如流云的气质,他眼睛里没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