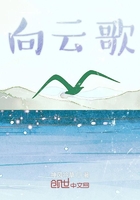刚刚刷微博,看到郎朗跟吉娜说,你出生那天,天气特别好,我记得特别清楚。
真浪漫,突然地我想起来,CX那天下雪了。2018年12月29日。
是CX在那三年中唯一下过的一场雪。于是在从基教A座去学院楼见AJ的路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希望可以带来好运气。
那段时间我站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深陷自我怀疑之中。白天不停的上新课做项目、复习结课的内容以应付一周一门为其两月的期末考,晚上得一丝空闲,却不愿睡觉企图逃避明天接踵而来的巨大压力。
我曾想大学不该单以成绩论优异,授课老师的人格和性格对学生的影响远比给分松紧高低来的重要,而学生应该去学习的东西也远不止课本上的那些,健全的人格和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也至关重要。
可最终,无论是保研还是出国,就只看那一个干巴巴的GPA。那我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又在哪里呢?
于是我约了AJ,想和这位年轻却学术成果斐然的副教授聊一聊。是我私下里第一次见他。
那大概是我爱他的开始。
回去后我特别开心,觉得人生找到了方向。我在日记本里夸AJ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才33岁左右,跟他聊完觉得人生还是比较有希望的。AJ成功的说服了我放弃去英国读研究生,转而去新加坡留学。
说来也好笑,我刚进副院长办公室时看AJ穿着一身上了年纪的黑色羽绒还在心里嫌弃地吐槽他的审美,觉得他还年轻怎么这样自我放弃。
结果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完全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溃不成军,想透过皮囊去爱他的灵魂而不自知。
后来我有机会把这个故事讲给AJ听,他生气的拿手边的抱枕砸我,一边砸一边说:“我那是专门买来和四五十岁中年男人打成一片的,怎么样,效果还不错吧”。
而后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梗,每次都要揶揄我:“你不是嫌我衣品差么”。
每年的12月末我好像都在生病,那时也是这几天感冒了,甚至更严重一点。还伴随着急性咽喉炎和胃炎,准确的说是食道的最后一截和胃连接的部分。
AJ是老胃病,据他说久病成医,而且是御医级别的。
那天结束见面后,在不得不去城市咖啡厅赴约的路上,AJ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戴着羽绒服的帽子还要再围一条围巾,连看着我的脸讲话都只能整个身子扭过来。
他看我带着口罩,笑问我:“你这是,为了好看还是保暖啊?”
“啊...?”我顿时语塞,“...我最近生病了,感冒又...胃炎。”
AJ好像来了兴趣,非要询问我具体症状,顺带给我开了副药:“吃点那个埃索美拉,一定要进口的啊,那个药效好。”
我原本也没什么在意,想不到他竟跟我小姨(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开给我的药一模一样,可见水平远超校医院的各位。
就这样乱扯着聊了一路,我眼看着AJ一边说:你走那么快干嘛,一边应付着电话那头的催促说:马上到...3分钟...已经到楼下了。
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一整个寒假我都念念不忘,逢人就夸我们副院长是个极有意思的人。
也许是他问我“你是XX附中的啊,那你怎么跑来了C大?”;
也许是电话里的邀约他不想去就直接当着我的面往沙发上一躺,演技极为逼真的对电话那头说:“诶哟...我...我昨天喝多了...现在还在床上...晚点吧”,挂掉后随即坐起来用眼神示意我接着说;
也有可能是他听完我高中都跑去谈恋爱了却说“应该的,恋爱也是人生的必修课。”;
或者是他像个小朋友一样跳到我面前,说他跟只大他三岁的曹老师也有代沟,又跳回去继续走路。
我偶尔会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的AJ,充满孩子气,像是我的同龄人。而非后来带着满身的疲惫,以至我想要他快乐,都不知该如何劝慰。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法想象,压在AJ肩上的到底是什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自己包裹在要和“老年人”打成一片而特意买的羽绒服里。
可我还记得。19年3月初的某天清晨,我站在宿舍大门口一扭头就望见AJ。
那么远的距离,AJ一边抬手朝我问好,一边意气风发得大步朝我这个方向走来,好像连风衣角都飞起来了。
我看呆了,脑袋当机到只朝他笑了一下,说了声“老师好。”也没等他就直愣愣地走了。
这个画面却没来由的在我脑海里驻扎到今天,也许是潜意识里我觉得那样的他,像是从我错过的、属于他风华正茂的好时光中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