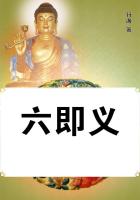危思跳下公共汽车时夕阳已经沉没,街上行人稀少,淡淡的暮色在街面上无声地弥漫。宝蓝色的天空犹如一个平静的湖泊悬在城市上空,稀疏的星星钻石一样点缀其上。上弦月似一叶随波逐流的小舟在几片薄云中穿行。
他朝庄姝过去的房间瞥了一眼,果绿色窗帘没有了,那间房子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拐进一条小街,匆匆往北郊而去。
走到小街尽头,穿过一片菜地,是一座不高的小山。山上没有树,全是峥嵘的石灰岩,泛着灰白色的光。山脚有好几幢平房被凤尾竹拥簇着。他用不着去查门牌号码,因为他一眼就看见,那块苹果绿的纱质窗帘挂在东端那间房子的窗户上,轻轻地飘起一角,似在向他招手。
他向绿窗帘走过去。房间里没亮灯,但窗户开着。整幢小屋静寂无声,像被遗弃的小庙。他扒着窗棂朝里观察,幽暗之中,他依稀地辨出了庄姝的那些简单的用具。
她显然外出未归。他在走廊上等着,背靠柱子,眺望月光下的城市。偶有几声汽车喇叭从城市腹地传来,随即被郊外的静寂所吞没。晒场边竹影斑驳,清凉的风从面颊上滑过,不禁使他想起她皮肤的滋润滑腻。
有一条灰白色的小路通向屋后的小山。何不到山上逛逛,边等她边找一点诗情画意?说不定,她就在山上散步呢。
他沿着那条小路慢慢地走到了山腰。到处是光秃秃的岩石,袒露着一种荒凉美。举目望去,月光从山顶的岩石上淙淙地淌下来,一直流到他身上。山尖参差不齐,几颗星星在石柱间明明灭灭。他忽然有了凌绝顶一览小城夜色的欲望,于是手脚并用,兴致勃勃地往上爬去。
月光似乎愈发的皎洁明媚了,岩石的皱褶都看得很清楚。他举起手抚摸空中悬挂着的月光之瀑,又叉开五指让月光从指缝里漏下去。他的身子被月光浮了起来,向山顶升起。那条弯曲的小路却好象爬累了,懒懒地沿着另一面山坡一头扎了下去。
山顶近在咫尺,他心有不甘,便撇开小路继续爬向山顶。当他越过一块卧狮形状的巨石时,发现山顶展现在跟前,而且,它决非他想象的那样狭窄尖突,它很宽敞,矗立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柱状岩石。确切地说,山顶是一片石林,它们犬牙交错,奇形怪状,全都一声不响。月光只能照亮岩石上部,似乎一落到下面便被阴影吞吃了。
他被这奇景震慑住了。他像走进了一座古堡,又如落进了一个迷宫。他有一些兴奋,又有一些恐惧。他背靠着岩石一动不动。忽然,前面石缝里有喁喁的人声。他支愣起耳朵,当再次听到确有人声传出时,蹑手蹑脚地向前摸过去。他好像意识到一个故事正在这岩石的布景里进行。他闪到一块岩石后。一串清脆的笑声从岩柱间蹦出来,听上去有点耳熟。他的心脏悚悚地缩紧了,背上出了一层冷汗。他摸索着,仄身穿过一道石缝,只见里面豁然开朗,敞开一个房间大小的空间。他向里面一瞥,居然看见了她!
她斜坐在一块岩石上,双手支撑在背后,后仰着身子。她望着夜空,月光泻在那张秀美的脸上。她的短发如一道黑色瀑布垂挂在脑后。她裸露的颈项和手臂闪着迷人的光泽。还是那件短袖的浅绿色裙子,只是已被月光镀得如白银一样。她的双脚立在阴影中,就如站在水中一般。她大睁着的双眼就像镶嵌在她脸上的黑珍珠,熠熠闪光。
在她对面几步远的地方,倚着岩石站着一个男人。男人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见神态,但危思觉出那男人正贪婪地欣赏她的脸。他的身体从上至下的发凉,变得跟岩石一样坚硬了。
那男人走出了阴影,向她伸出了一只手。那家伙的脸丑陋而狰狞!而她,竟然拉住了那人的手,使劲一扯站了起来。那男人还不松手,企图将她往怀里拉,她咯咯咯地笑着跳开了,轻盈地做了一个旋转的舞蹈动作——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的舞姿,然而却不是为他跳的——她的裙裾荷花般优美地绽开,如水的月光被她搅得荡漾不止。他被这种不期而遇的美深深地杀伤了。他呻吟着,直往下面缩。这时那个男人又一把抓住了她的玉臂,想把她往怀里揽。她扭转身子后退一步,好像试图反抗,而她的胯部却侧着向前拱,似乎去迎合。那男人向前一扑,她终于落进了那个恶毒的怀抱里了!那男人右手环住她那只有盈盈一握的纤腰,左手按住她的后脑壳往面前压。男人的嘴凑上去了,她左右扭动不让那家伙亲吻,可嘴里不断飞出不连贯的笑声。最终她让步了,和那个男人咬在了一起。
他躲在岩石后窥视着,心里一阵绞痛,视线酸楚无力,却始终粘在那两个扭曲的人体上。这时她踮起脚尖,好像尝试一种新的舞蹈动作。那男人向她压过来,她向后仰,像是要下腰。那家伙一只手搂着她,另一只手腾出来撩起了她的裙子,亮出两条演员特有的健壮、修长、白净的大腿。月色在那两条大腿上淋漓尽致地淌着。那是他无数次珍爱地抚摸过的大腿啊!她扭摆着,嘴里唔唔地呻唤,当那男人的手发动侵袭时,她的髋骨就扭动着划着弧线。她犹如在配合那个男人跳一种奇特的舞蹈。后来她一个踉跄失去平衡,搂着那个男人倒在阴影里,再也没有起来……
他双腿发软,身上忽冷忽热,得了疟疾般颤栗不止。他十分惧怕被那两个人发现,极其紧张地从岩缝里摸出来,跌跌撞撞地跑下了这荒凉的山岗。
他头重脚轻地经过那幢小平房时,再也没有去欣赏什么果绿色的窗帘。不过他发现了一辆来时没有发现的摩托车,它阴险地隐藏在墙边阴影里,使他立即想起那个他忌讳已久的名字。
他在夜色里抱头鼠窜。他窜上了街道,窜上了一辆正停在路边的厂里的卡车。
他站在踏板上,嘭嘭地拍打驾驶室的门:“师傅,回厂里么?”
司机说:“是呵,进来吧。”
他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关上门,战战兢兢地抱着双肩。
司机说:“你怎么牙齿敲梆呵,是不是病了?”
他不吱声。他急于要逃走,逃离这个可怕的月夜。卡车在月光里疾驶,怎么快他也嫌慢。司机似乎懂他的心思,不断地加大油门,车速愈来愈快,愈来愈快,所有的建筑物都向后倒了下去,星星拉成了一根根金丝……
从那个月夜逃出之后,危思长时间地昏昏沉沉,似醒非醒,对一切事物都持一种漠然而矜持的态度。他希望把一切都遗忘,所以当他和全班工友都围着桌子团团坐着,一时竟不知事出何因。
他愚钝地望着桌上的红葡萄酒和从食堂买来的味道雷同的菜肴,久久沉默,无有话说。
黄秉良举起酒杯,腥红的酒液在杯子里晃荡:“今天我们开个欢送会。我没有料到一下子有三个同志调离我们班,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我们还是高高兴兴为他们送行吧。来,大家干了这一杯!”
危思随着大家站了起来,把一杯酒倒进肚里,灼热郁闷的酒意顿时直冲头顶。不知谁把勺子碰到地上,叮当作响,沉闷的气氛就绽裂开了。
“彤彤,来,我先敬女士一杯,”黄秉良说,“我祝贺你荣调召阳,而且,不用倒班了。说实话,人都是肉做的,哪个愿意倒一辈子班?我们是没办法,班也要有人倒的,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只要我们尽了力,就问心无愧了。你的工作做得不错的,分析基本上准时、准确,我代表全班感谢你!”
“班长,你和班里的师傅到召阳来,一定到我那里去玩!”冯彤彤眼睛发红。
“一定、一定!”
众人七嘴八舌答应着,只有危思不作声。
“小谢,我也敬你一杯,”黄秉良又举杯向着谢建华,“祝你如愿以偿,调到行政科当干部。”
“班长,这杯酒我来敬,”疏水器推开黄秉良挤到谢建华面前,“小谢,这些年你太辛苦了,八小时内要帮危思抄报表,八小时外要给缪书记做家务,还要帮行政科科长带孙子,没有功劳有苦劳,当干部是应该的!我祝你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弄个一官半职,也不枉为我班出去的人,有本事!”
谢建华红了半边脸:“开什么玩笑,不过是个办事员,算什么干部喽。”
疏水器道:“不是开玩笑,老人家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嘛!”
黄秉良拉开疏水器:“少说几句,怎么说也是一个班的人,各有各的活法嘛。”
疏水器没有尽兴,怏怏地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