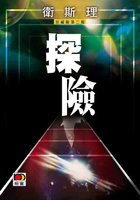他机械地往口里扒饭,只觉味同嚼蜡,脑壳里轰鸣不已,好像有一辆摩托车在疾驶。吃过饭,他在机器噪声中徘徊,看似在作巡回检查,实际上对那些仪表指针视而不见。想象中飙飞的摩托车令他心烦意乱。庄姝,那真是你?你那玉色的手臂真环绕在那个陌生男人的腰间?你是去幸城,你是让摩托驮你回到你的过去?那到底是怎样的过去?我不浅薄,我不想浅薄;我不狭隘,我决心不狭隘,我无意探究你的过去,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不求拥有你的过去,但求拥有你的现在和未来。这个骑摩托的男人是你过去的一部分吗?你并没有斩断同过去的一切联系是吗?有一点你要明白,你可以不爱我,可以拒绝我,但不可以羞辱我,我有我的人格与尊严,我可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工人,你美得令人心颤,人见人爱……我不允许别的人爱你!你身上已被我打上了爱的印记,你是属于我的……我要把你供奉起来,你是我的神,我的维纳斯,你主宰我的命运……你是那么好,你那么优雅美丽,那么热情似火……你使我的心灵和肉体享受至高无上的快乐,使我的灵魂出窍……我决不听信那些话,那是小心眼女人的小诡计……我太爱你,我不能失去你,只有你能重塑我的生命,只有你是我生命中的诗……
在他纷乱的思绪中时间悄悄溜走。檐下斜射而入的阳光撩拨着他的眼睛。只差半小时下班了。他拖过水管来冲洗地面,做交班准备。他捏瘪胶管口,让水呈扇面冲刷开去。一双趿拖鞋的脚从眼角余光里走过,一看,又是冯彤彤,端着脸盆往浴室方向去了。分析室通常比其他岗位早交班半小时。冯彤彤冲他笑了一下。他对这笑没有感觉,继续埋头冲他的。灰尘被水赶进了地沟,但地面到处湿漉漉的了。
冲完地,危思又抓起棉纱擦拭泵体。姚汉金在值班室填写交班记录,谢建华则站在门外东张西望看风景。谢建华是刚分配来的徒弟,明确要他带,但他从不叫他师傅,而是直呼其名,人也懒,一搞卫生就躲到一边。他也懒得叫谢建华,不是一天两天,叫得过来的?全靠自觉。叫他还不如自己多干一会。
搞完卫生,洗了手,就只等人来接班了。但突然间墙上铃声大作,紧急停车的红灯亮了。他立即朝姚汉金招手,大步奔到合成塔下,将P4大阀套上套筒,双手抓住猛扳。阀门实在太重,猛扳一次,只转动一点点。待姚汉金赶来帮忙,才大幅度旋转起来。与此同时,他指挥谢建华去打开减压阀。
一鼓作气将大阀关死,刚伸直腰吁口气,只听地沟里噗一声响,一股白烟腾空而起。他一惊,立即判断是减压不及时,管道内超压,高压液氨将法兰垫圈刺破了。他飞奔到控制屏前,按下了停车键。马达霎时停止了旋转,噪声骤然消失,车间里平静下来,只有排放阀发出尖利的呼啸。他狠狠瞪了谢建华一眼:“你怎么搞的?”戴上防毒面具,去完成余下的停车步骤。
地沟里不断冒出白色烟雾,那是气化的液氨。前后阀门都已关死,只有泄漏点所在一段管道中的液氨无法控制,只能等它泄光。白雾不断升腾,弥漫,空气变得火辣辣的了。浓度很高,防毒面具已失去效用。他忍着肺部阵阵刺痛,强憋着气,将最后一道阀门关死,才从烟雾中冲出来。他跑到厂房外,双手在腋部和裆部乱抓,氨气与水分发生反应,好似无数口针在那里扎。
他满面大汗地喘气,泵房里氨雾越来越浓,一阵风吹来,白雾南移,顿时将厂房一侧的简易浴室包围得严严实实了。他心里一紧:冯彤彤不是在里头洗澡吗?
他将防毒面具往地上一扔,用打湿的衣襟捂着鼻子冲进氨雾弥漫的值班室,从柜子里抓出一个氧气呼吸器,心急火燎地背上,戴好面罩,旋开氧气开关。泵房里一片白茫茫,能见度不到一米,他凭着记忆迅速穿过泵房,摸索着到了女浴室的门口。
他用脚猛踢浴室门,里面没有任何回应。他低头冲了进去。里面水汽加氨气,一片浑沌。他吐口痰擦了擦面罩镜片,还是看不太清。他向水龙头走过去。突然他被什么绊了个踉跄。蹲下身子,双手一摸,是一具裸露柔软的人体!他使劲睁睁眼,再凑近一些,冯彤彤丰满的躯体赤裸裸地呈现在面前。她双目紧闭,已窒息得不省人事。他顾不得多想,取下一件冯彤彤挂在墙上的换洗衣服盖在她身上,抱起她就往外闯。在浴室里转了两圈他才找到出去的门。冯彤彤又沉又滑,坠得她双臂仿佛即刻要断裂,他拼命支撑着,向明亮的地方趔趔趄趄地奔去……
终于,他抱着冯彤彤从那片该死的白雾里冲了出来。当看到许多人影围拢来时,他心里一轻松,和冯彤彤一起倒在了地上。
她提着小篮子去市场买菜。她的新生活已经开始。她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感到自己被淹没了。这就是她要的新生活吗?她不知道。她很迷惘。
她被人撞了一下,转了个身,不知往哪个方向去好。她站立不动,一时竟不清楚,来到这芸芸众生之中意欲何为。
这时她看见一个背影,背着个摄影包。她觉得她认得这个人。背影一仄,扭过身来,果然是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个人是个摄影家,曾经三番两次到幸城去给她拍剧照。
她欣喜地走近他,马老师,真的是你!
他也说,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她说,我调这儿的工人文化宫来了。
他点头说,我听说了,你就这么离开舞台,再也不能施展你的表演才华,太可惜了。
她顿了顿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这一跤跌得太惨了。
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不必这么想,其实也不算什么,我倒羡慕你,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平平淡淡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
她笑笑,谢谢你的安慰。
他说,我这是真心话,不是廉价的安慰。瞟瞟她手中的篮子,说,你成家了?
她摇头,没有。
他问,有男朋友了?
她想想说,正在考虑……
他说,是该考虑了,老一个人,不好。
她问,您是来出差吗?
他说,我是出来搞摄影创作的,想弄个青衣江风情展。搞我这一行,就这点好,比较自由,闲云野鹤一般,不受什么约束,想出来就出来。
她热情相邀,到我屋里坐坐吧。
他想想说,下次吧,我下午准备回召阳。你回幸城看看么?我开一辆三轮摩托来的,可以带你一程。这一路风光很好,顺便还可以给你拍点照片,请你当当我的模特。
她说,幸城我是不想再去的,不过我正想去你们召阳群众艺术馆学个新节目回来呢。
他说,那好啊,一起走吧。
她兴奋起来,点了点头,与他约好,下午一点在文化宫门口见面。
她回到单位,向主任告了假,收拾好简单的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她的心情焕然一新。她吃了点饼干当中饭,兴冲冲地出了门。他非常准时,骑着一辆带斗的草绿色摩托车停在门口。上车时,他抓住她一只手托了一下,并且在极短的接触时间里,亲切地轻轻捏了捏。她便不由自主地,也回握了他一下。感觉很微妙。她心里有莫名的温暖滑过。
摩托开动了,风流过她的脸,她的短发扬起像挥舞一面旗帜。
他大声说,开这么快不怕吧?
她大声回答,快才过瘾呢!
人影和树影一掠而过,公路像一条带子刷刷地抽向身后。她感到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将所熟悉的庸常生活统统甩掉了,她正进入一个崭新而不可知的境界。哦,这不正是迷惘的她所渴望的吗?
危思在食堂吃午饭,发现一些目光在身上缠绕,颇不自在。正想离开,宣传科的赵小鸣蹲在一张水磨石餐桌边,招着手:“危思,你过来。”
他有些不情愿地走过去:“什么事?”
“告诉你,你们车间给你写了份表扬稿,说你英勇救同志,越是危险越向前咧!”
“这有什么。”他说。
“不过,稿子在宣传科没有通过。”
“为什么?”
赵小鸣嚼着饭,嘴里鼓鼓囊囊的:“唔……胡科长说,你的救人行为还是不错的,但要广播出来,怕影响不好。”
“为什么?”
“关键在你救人的情节。你不是把冯彤彤光着身子抱出来的么?稿子上虽然没写,但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嘿嘿,科长说有点象黄色小说咧,广播这篇稿子怕引起不健康的意识,不播为好。”
“不播就不播。”他说。
“不过听说车间准备给你加十块钱奖金。”
“我又不是为得奖金才救人的。”他说。
“那你为了什么?”赵小鸣盯着他。
“就为救人,不为什么。”他说。
“你怎么不说点豪言壮语,把思想境界提高一点?”
“我实话实说。”
“呃,危诗人,那你跟我说实话,”赵小鸣笑嘻嘻地凑到他跟前,“你救她的时候,比如说用衣服盖住她的时候,有没有摸过她?”
他怔住了,嘴巴张开忘了闭上。刹那间,他又有了那种久违的壳感。愤懑的情绪在他的壳内膨胀着,沸腾着……他极想把那口未咽下去的饭吐到面前那张脸上,但他还是忍住了,低声骂一句:“流氓!”转身离开。
危思情绪恶劣,跑到邮电所给庄姝打电话,电话通了,却没人接,这才想起,中午休息还没上班。几天没她的消息了。他已打过多次电话,接电话的人很不友好,一听说找她,说声不在就把电话挂了。
回到宿舍,他闷头闷脑地睡了一觉。一醒来廖一平就邀他去医院看望冯彤彤。两人到商店买了一些水果奶粉之类,用网兜提着去了医院。一进门,就见一些穿白大褂的女护士走来走去,褂裙飘然,风姿绰约,他莫名地觉得她们与庄姝有某些类似的地方,都那么优雅大方,看上去很顺眼。
他跟着廖一平进了病房。冯彤彤正坐在床上看书,气色不错,脸蛋在雪白的被子和墙壁映衬下显得很红润。冯彤彤目光一碰见他,迅速地收回去了。
廖一平大声招呼着:“冯彤彤,好些了吗?”
冯彤彤冲廖一平笑:“好多了!”
“嘿嘿,你可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呵!”廖一平用水果刀削着苹果,“不倒班,就是福,我看你都养漂亮了呢!身体没有什么大影响吧?”
“没事,只是轻度肺水肿,被氨气刺激的,医生说我体质很好,休养一段就会好的。”
“那太好了,呶,给。”廖一平将削好的苹果直接塞进冯彤彤嘴里。
冯彤彤眉开颜笑,手接下苹果说:“你这样苏又茹要嫉妒的!”
危思感到受了冷落,就去打开窗户,自言自语:“空气好象不太流通。”
廖一平说:“冯彤彤,这一次要不是危思,你可能到阎王佬儿那里报到去了呢!”
冯彤彤却不看危思,默默点点头,红着脸扭过头去了。
“冯彤彤……”危思欲言又止。他很想说冯彤彤我不该救你,救了你连话都不跟我说了,但没说出来。廖一平拉了拉他的衣角,两人出了病房。
“她不好意思呢,你看见过她的光身子。”廖一平说。
“我根本就没看清她,这事怎么好像成了我的错了?”他说,心里很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