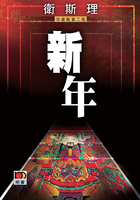他刚吃完午饭,手里还拿着饭盒。他盯着那辆已经启动的公共汽车。这是到她那里去的公共汽车。几天不见,他太想她了。她的脸,她的眼,她的唇,她的笑,她的声音,她的动作,都像蚂蝗一样叮在他的脑子里。离下午上小夜班只有不到四个小时,路上一去一回就要两个多小时。即使这样,也可以在她那儿呆上宝贵的一个多小时。中午她正好在家休息。去不去?当然去,此时不去,更待何时。见她的念头一经启动就停不下来,就像那辆公共汽车。他将饭盒塞给廖一平,请他带回宿舍。他向开动了的公共汽车飞奔,招手大喊,在车门即将关上的刹那,他跳了上去。
上了车才知道它开得太慢了。它像个老态龙钟的长者,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哼哼唧唧,吱吱嘎嘎,走不了多远又要停下来歇口气,一停下来又要半天才动身。上下车的人都慢条斯理,似乎有意磨蹭,以延长他见到她的时间。特别是那些大包小包进城做小买卖的人,拖拖拉拉上车比上天还慢,让他心焦。每到一个站,都要看一下他手腕上的那块东风表,计算余下的时间。急得自已受不了,就帮售票员吆喝,上车的快点,下车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总算到了站。他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横过马路,迫不及待地跑进文化宫,走到她的门前,迫不及待得举起手弓起指头……但是他没敲门,门半开着,他闪了进去。
她正站在窗前,对着镜子梳头发,见他进来,并不惊讶,说声:“你来了?”走到门口,朝走廊两端看看,轻轻关上门。她一回头,他就把她搂住了。一如既往地将面孔埋在她芳香的脖颈里,呼吸她的气息。
她任他搂着一动不动,过了半天,才低声说:“几天不见,电话也没一个。”
他歉意地说:“对不起,电话我是打了的,是在邮电所打的,可办公室的人说你不在。我岗位上是内部电话,外线打得进来,我打不出去……要不我会多打几次。”她动了动身子,叫他坐,但他舍不得松手,紧紧地搂着她不动弹。
在她的气息里沉醉够了,他才嘬起唇去吻她,但她把脸扭开了。他很敏感:“你怎么了?”
她忽闪一下黑黑的睫毛:“没什么。”
但他明显看出她有什么。她的眼神飘忽不定,眉头微蹙。他小心地询问:“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她摇了头:“我情绪不好。”
他抚着她的脸:“为什么?”
她说:“你别管我,不关你的事。”
他将她的短发拢向她的耳后,捧起她的两腮:“怎么不关我的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不开颜,我也不高兴。你说给我听听,什么事让你心烦,让我来分担一下你的烦恼。”
她从他的怀里出来,看看他,抿抿嘴巴。他这才发觉,她穿了条浅蓝色底缀细碎白花的的确良连衣裙,腰掐得恰到好处,身体的曲线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即使是烦心之时,她也亭亭玉立地站着丁字步,保持着高雅的气质与风度,使他联想到舞台上的她。她想想说:“我还是不说的好,免得你也跟我一样心情不佳。”
他把双手搁在她肩膀上,注视着她:“你不说,更让我心神不宁呢,我不替你担心,还有谁替你担心?”
她咬咬下唇:“好,我说,不过你答应我,一定要冷静,不要生气。”
他郑重地点头:“好,我答应你。”
她叹口气,望着窗外说:“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弄得人心里不舒服……合唱队准备添置十几套演出服,上午我到服装厂拿了一套样品来,在屋里试穿的时候,主任来了,说这服装不错嘛,扯扯衣摆,拉拉衣袖,又摸摸腰,接着就把手放到我胸脯上来了……”
他脑子里嗡地一声响,脸就胀红了:“他、他居然敢这样!后来呢?”
她说:“后来我板着脸把他的手甩开了,他就没再怎样了。”
“这个流氓,老子揍他!”他倏地攥起拳头,转身往门外走。
她一把拽住他:“你要干什么?!”
他怒气冲冲:“他居然敢侮辱你,老子找他算帐!”
她把他推开,背靠着门:“难道你为这点事要找他打架?那像什么话?”
他额门上青筋凸起:“我、我找总工会领导反映去!”
她生气了,坐到床上,背对着他:“你怎么这么不冷静?!为这事你告他,以后我还怎么在这里工作?我的脸往哪里搁?要告也轮不到你,这是我自己的事!”
他说:“他欺侮我心爱的人,我怎么能够冷静?难道就任凭他胡作非为吗?”他气恨难消,屋子里来回走了几趟,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沉默了一阵,她叹声气,过来抱住她,把下巴搁在他头顶:“危思,我理解你,他侮辱了我也伤害了你的自尊心,我谢谢你对我的看重。可是告状不是办法,而且,说不定他会倒打一耙。”
他忧心忡忡:“那怎么办?让你在这样一个品德恶劣的领导手下工作,我怎么放得下心?”
她摩挲着他的下巴道:“他是个聪明人,只要我行得稳,立得正,正气凛然,他不敢动手动脚了的,这种人把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其实我不该说给你听,这么一桩小事,我自己处理得了的,只是心里堵得很……现在,我心里轻松多了。你也别担心了,开心起来,好吗?”
他应了一声,反手将她搂过来,让她坐在自己腿上。隔着裙布他无比爱怜地抚着她鼓凸的胸乳,颤声说:“你是我的,你的每一处,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一口气息,都是我的,我要保护你,再也不让别人亵渎!你也要替我保护好自己,要珍惜自己!”她连连点头,解开了连衣裙的腰带和胸前的扣子,将胸罩往上一拨,两只饱满的乳房就跳了出来。她捧起左边那只,凑到他面前,它受了委屈,你快安慰安慰它吧。他两眼热辣,面颊在它上面擦了擦,轻轻地含住了那颗红樱桃似的乳头。他像婴儿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嘴里咂咂有声,手还抓着另一只,百般地搓揉。他脑子开始晕眩,意识也逐渐模糊,朦胧中听见她问:“想吗?”他抽空说:“想,想死我了……可惜我下午要上班,你也要上班了。”
她说:“还有半个小时,还来得及。”
他忽然变得力大无比,轻易时将她抱了起来,而且嘴也没有离开她的胸脯。他没觉出自己在动,而感到那张床自己浮了过来,塞在了他们身下。他被浓郁的芳香之气笼罩,身上的所有织物水一样滑了下去。他醉眼朦胧。她的脸红得象一朵燃烧的霞。他正要腾空而起的时候,她从枕头下摸出一个东西塞给他。他如在梦中,迷惑地低语:“什么?”她闭上眼睛:“套子,你戴上。”他手足无措,因为毫无经验:“哪来的套子?”她说:“前天在总工会办事,管计划生育的管姐托我带给办公室,我偷偷地留了几个。”她脸向着墙,不看他的羞怯与慌乱。他手忙脚乱,狼狈极了。他总算完成了这个环节,但介入这件事之后,他和她的亲密之间有了隔膜。这让他迷惘,不自在,感到美中不足。不过这迷惘非常淡薄,很快被肉体的欲望焚烧得一干二净。她盯着他,双目如炬,怂恿他朝着极乐的顶峰冲刺。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忽然,有人敲门:“庄老师在吗?”他惊骇得停了下来。她的手却在他背上果断地一按。他得到了指令,便不再顾忌,竭尽全力勇往直前,直到脑子里电光一闪,意识爆裂成无数的碎片……
后来他感到她吻了吻他的脸。她说:“你歇会儿再走吧,不要让别人看见。”她蹑手蹑脚,像只猫一样走了。他躺着,心如止水。后来他坐了起来,翻开枕头,拉开枕套后的拉链,从中摸出三个那样的套子来。他默默地看了看,把它们放回原处。他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他自己都弄不清。再后来他就到了回厂的公共汽车上,他摇摇欲睡的时候,发现对面一个满面皱纹的老太婆正盯着他,目光非常忧郁。
即使是在十八年之后,危思也闻得到工厂食堂那种大锅菜的熟悉味道。那种菜总是炒过了头的,总是放了不少酱油和味精的,总是像出自一个厨师之手,吃了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次,却又总是餐餐都要吃的。只是因为胃粘膜受了氨味刺激,工人们的胃口总是很好,所以对饭菜也并不怎么挑剔。
操作工连续上班八小时,需进餐也是不能离开岗位的,车间请了一位临时工,专门为当班工人送来那些味道一成不变的饭菜。
这日过了十二点,午饭才送来。危思正用勺子安慰自己的胃,冯彤彤走进值班室,将饭盒朝他面前一伸:“尝尝我们幸城特产,腊猪血豆腐!”
他就从她饭盒里夹了几片。
“多夹点多夹点,我还有呢!”她用筷子真接往他饭盒里拨。
“多谢多谢,够了够了!”他把她的手推开。
冯彤彤却一屁股挨着他坐下了。
他把屁股挪开一些:“冯彤彤,当心领导看见听奖金!”
冯彤彤毫不在乎:“串岗算什么,刚才我还偷偷跑到厂外商店里买东西去了呢!”
他说:“嚯,你真英雄。”
“哎,我还看见你那位了呢!”
“什么我那位?”
“装什么傻,就那天坐在你房里的漂亮小姐!”
“逗我干什么。”
“当我骗你呀?真的看见她了!她坐在一辆摩托上,还抱着那个男人的腰,刷地一声就从马路上飙过去了,好威风呢!”冯彤彤说。
“你一定看错人了。”他说。他想如果是她,到了厂门口,还有不来找他的道理?
“我怎么会看错人呢?他们是往西边去的,不是到幸城,就是到召阳市去了。”
“不可能。”他有些不安。
“告诉你吧,我认识她。她以前是我们幸城花古戏剧团的演员,演柯湘的,幸城人哪个不认识?进厂前,我经常看她的戏呢!那天在你屋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没告诉过你?”
“没有。”
“那她没告诉你的只怕还多呢。”冯彤彤神秘地笑笑。
“你还晓得她什么情况?”他问。
“某个方面的情况。”
他忽然觉得冯彤彤的面孔非常讨厌,那厚嘴唇油腻腻的,还有那自鸣得意样子,其用意一目了然。可他还是问:“能不能告诉我?”
“我不能说,你跟她好,我只能说好话对不?挑拨离间的罪名我可担当不起。再说你也不会相信我的。你认为我嫉妒她对不?我确实有点嫉妒……”
“彤彤,我跟她现在只是……”
“算了吧,你那样子一看就晓得丢了魂。我不会总是自作多情的。爹妈给了她一副好脸蛋,人见人爱。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还算不上英雄呢。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能真心爱你这个工人,你也能为我们工人争口气。”
冯彤彤起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