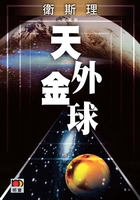他就像几年之后捏着中央戏剧学院的信进厂办公楼一样,捏着体检表进了隔壁量血压的房间。他感觉徐徐走了一盆冷水,深身起了鸡皮疙瘩。他把体检表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一边颤抖一边往自己的壳里缩。那位骨瘦如材的女医生的眼神与办公楼的白面书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饶有深意地瞄了瞄他,喝道:
“伸出胳膊,把袖子勒起来!”
他连忙遵命,胡乱地将袖子最大限度地往上勒。粗壮的胳膊裸露出来,肌肉紧张地蠕动。黑色的布带像一条冰冷的蛇,死死地缠住了他的左臂,紧接着那听诊器探头蛇头般贴着皮肤爬过来,钻进布带里,一口咬住他的手臂不动了,似乎在吮吸他的血。医生讥诮地冷笑,使劲地捏那个紫红色的空心橡皮球,布带里突然一阵阵地膨胀,胳膊被一步步勒紧,仿佛就要断裂!医生面无表情地盯着血压计。关键时刻到了,他紧紧地咬住下唇,屏住气息,希望自己身体里奔流的血液平息下来。可是他的心控制不住,它猝然狂跳起来,凶狠地撞击着他的壳!他的胸壁一阵阵地发疼,他的心跳一下,他就看见那可怕的水银柱向上窜一下;他的心越跳越高,那水银柱也越窜越高。他紧张恐慌到了极点,那颗疯狂不羁的心似乎即将撞破他的壳,跳将出来。他的目光因为惊悸而模糊了……
“好了好了,走吧……下一个!”
医生呼叫着推了他一下,他才发现臂上的布带已经没有了,体检表在手里闪着苍白的光。他机械地走到走廊里,目光怯怯地往表上觑去。“血压”一栏里,横摆着几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数字:70—150。就像摆着一具尸体,他不敢看第二眼。他第一个念头是,完了。据他所知,较为正常的收缩压,或者说招工的厂方代表所能接受,而医生也不会大惊小怪的收缩压,不能超过130。
他的心突然地就平静了,他僵在他的壳里,有一种毫无痛苦地死去的感觉。他的心在作弄了他之后,就麻木了。冷风从走廊里呼呼地穿过,拍打他毫无知觉的躯壳。不知过了多久,他的神经忽然醒了。不,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裁决。他本来是健康的,平时测量,血压并没有这么高,只是因为这是招工体检,它才高了。这不公平。仿佛从恶梦中苏醒,他气喘吁吁,余悸未尽。他在原地转了两圈,没有继续下一个项目的检查,懵懵懂懂地踅进了厕所。他并不要解手,当他看见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了钢笔,才醒悟自己有了什么样的企图。他一时惊呆了,深深地躲进自己的躯体里,蜷缩着一动不动……
后来,他的内心泛起一股疯狂的情感,这情感把他的身体烧着了。他两眼发烫,见左右没人,不顾一切地伸出颤抖的手,拧开笔帽,在手心写了几个毫无意义的阿拉伯数字。他嘴里喷吐着热气,头皮灼疼,似乎已经烤焦,散发出丝丝糊味。他耐心地等笔迹干了,把它与体检表上的笔迹相对照,发现墨水的颜色完全相同。他沉着地四下观察。除了他,厕所里没有任何人,安静得很。于是他低头开始研究那几个关系到他的前途和命运的数字。在极短的时间里,他拿出了行动方案。150毫米汞柱,这是个虚假的数字,除了他自己,没人会去纠正这种虚假。5字上头那一横很短,且不明显,改成一个3字,是比较方便的。他先在想象中改了一遍,觉得有了把握,便孤注一掷地将笔尖触到纸面上去……
做完之后,他将体检表对折了两下,若无若事地出了厕所。他沉着地进入下一步检查,把表送到医生手里。医生随时可能发现那个被涂改过的数字,他知道一旦败露,将有什么样的后果。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该发生的,那就让它发生吧。他奉命脱光了裤子,接受对生殖器的检查。当他将两条赤条条的腿从裤子里抽出来时,觉得是从自己的壳里蜕出来了。他站在那里,下身一丝不挂,一切秘密都暴露无遗。他听凭医生的手,那也是命运的手,任意摆布着。
然而,这一次命运宽大为怀,竟然默认了他的篡改。不知是医生责任感不强还是他们眼神不济,始终没有发现那个显而易见的秘密。他的笔尖两秒钟的移动,使得他摆脱了知青生涯,成了青衣江化肥厂的操作工。
但是,这只是一个特例。
他知道,绝大部分时候,人的命运都不在自己手里。
这是个闷热无比的夏天,林立的铁塔和巨大的球罐在灼热的阳光照射下泛着炫目的光,空气中流动着金属的干燥气息,马路上尘土飞扬,永不停息的机器轰鸣声隐隐约约地从厂区一直传到宿舍,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令人昏昏欲睡。
在这个夏天里,危思意志消沉,情绪低落。他很少看书,也懒得写什么诗,而与工友们打成了一片。下班之后,大都以打扑克来消磨时光。表面上看,他是合群了,但在内心深处,他是愈发的孤独。
平庸乏味的日子日复一日的延续着。
这天休息,危思与一堆工友打牌,对家是疏水器。疏水器本叫周卫星,因为有尿频的毛病,就有了疏水器的雅号。危思打牌总是有几分心不在焉,就出错了一张牌。疏水器马上就埋怨起来:“怎么不压上手的牌?眼睛配相的么?”
危思说:“我有我的考虑嘛。”
疏水器说:“考虑过屁,只怕考虑到哪个女人的奶子上去了!”
危思恼了:“嘴巴放干净点,打牌就打牌,干嘛侮辱人?”
“谁侮辱你了?跟你打牌没咸菜味,老子不跟你来了!”疏水器脖子一梗,两眼一瞪,把手中的牌摔在桌上。
危思胀红了脸,也将牌一摔:“不来就不来,这副鸟样子,还想吃人呀?”
疏水器额头青筋暴突:“老子就这副鸟样,老子的鸟样不比你那鸟样强?什么玩意?!”
危思立即敏感到疏水器在暗指他相貌丑陋,在讥讽他的单眼皮和散布着痤疮斑的脸。工友之间,是常以攻击别人的相貌来取乐的,往往一架吵过之后,就会和好如初。但危思还是深深地感到遭受了人格上的侮辱。他的心里立刻爬出一股小小的仇恨,血往头顶一冲,就冲疏水器扑了过去。
但是廖一平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了他:
“算了算了,我看是吃了枪药了。为共同对付敌人,国共两党都要合作,出错一张牌,你们就闹成这样子!不打就不打,不过这一盘算你们输,凳子还是要钻的!”
“就是,钻凳子钻凳子!”
众人一阵起哄,就转移了矛盾。没打成架,危思心里有些不快,他是很想发泄一下的。他心里憋的东西太多了。他怏怏地抓起一条小方凳,往头上一套。凳子实在太小,他竭力缩小身体,挣扎着将凳子往下褪。先从那个固定的小方格里钻出来的是头,然后是双肩、胳膊和腰,最后才是两条腿。整个过程,就像是蜕去一个壳。他又有了一次熟悉的蜕壳之感。危思刚从凳里拔出两条腿,胡松生的大块头挤进门来,眼睛一亮:
“嚯,危思也钻凳子呀?”
疏水器还耿耿于怀:“他呀,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下了班就种自留地,种昏了头就不晓得出牌了。”
危思瞥疏水器一眼,不吱声。
“噢,种什么自留地呀?”胡松生很感兴趣。
“写诗做小说呗,发表了得稿费赚外快,不是种自留地是干什么?”疏水器说。
“听听,小危呀,群众对你提出批评来了,我看你得虚心接受哇!”胡松生指点着危思笑道。
危思感到窒息,透不过气来,固执地沉默着。
“大家坐吧,坐吧,”胡松生招呼着,笑容可掬,“今天我是来跟大家告别的,明天我要到厂办公楼上班了,嗯,任政治部宣传科负责人。”
“哟,那得叫您胡科长了吧?”疏水器掏出一盒烟,先敬了胡松生一支,然后逐个散发,顺手扔了一支在危思怀里。
“嘿嘿,科长不科长,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车间里嗅惯了氨气,到了办公楼,还不晓得适不适应呢!”
“胡书记高升了,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小兵呀!”
“哪里哪里,领导你们这么久,都领导出感情来了,哪能忘?”胡松生转而对危思说,“小危,你搞创作,直接属宣传科管,以后多到宣传科走走,我可以给你出点主意。在创作上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嗯。”危思应一声,点燃烟吸了一口,吐出一口郁闷之气,“胡书记,你们坐,我要去排放一下。”
跟把吃饭称作投料一样,他和工人们都把拉屎撒尿称之为排放。这是操作工的职业用语。但他没有去厕所,而是回到自己房间,仰头倒在床上,望着蚊帐顶发呆。
等到胸口的细汗被灼热的身体吸干,烦躁的心也平静下来,他就摸起一本杂志来翻。这是一本本省的文学刊物,封二上登着一群文学创作竞赛获奖者的小照,每张小照下都有简介。危思随意地睃了一眼,发现其中一个年轻女子向他无声地微笑。他偏了偏头,改变了角度,但那女子的眼睛仍注视着他。在十几个男女中,只有她这样。危思心中就有一丝诧异,仔细看了一下她的简历:
柳莺,女,23岁,辰阳市工业局打字员,小说《邂逅》获本次竞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