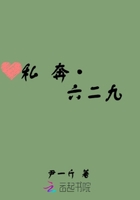话说听到报告说有记者点名采访杨康,世堂大为惊恐。单知道记者手中的笔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比旧时的刀笔吏有过之无不及。估计两个孽畜闯下了什么齐天大祸,才引来追腥逐臭的苍蝇。便一面派人增加岗哨,防止记者进来,一面令人拖出镇东杨康,兜头一盆凉水下去,浇醒二人。欲待问话,长官部派了车来接镇东杨康,并令驱散记者。
看着两人被带走,世堂忙忙回营帐,摊开纸笔给大哥回信,头绪万千,想说的事儿多如牛毛却不知从何捋起。康儿镇东被带去司令部,此事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还是等了事以后再说,一连串的问题搅得头脑发昏。
秀儿杨梅进来问了两次,都被摆手赶了出去,镇中等人哪敢过来请安。帐中无人相扰,静下心来突然想到为什么不问问记者因何采访杨康镇东,并对方才的举措深感愧疚。想找个人去请个记者来,连叫数声,无人应答。
忙冲出营帐,红日当空,子弟们在远处跟着教官在操练。滚滚尘土中大军还在撤退,问守把的岗哨,记者哪去了,答说早被驱离,已经无影无踪。
却说镇东杨康被送往司令部,两人也懒问因由,也知道问不出什么来。一上车就闭了眼睛,可怎么也睡不着,心中有事的假寐最是折磨,虽说杀的是鬼子,毕竟杀人了。
杨康想不通准备得好好的扁担为么抽不出来,念一声佛就抽出来了。镇东想的是小鬼子的功夫了得,自己早露败相,为甚么一个都不施以援手?看着快要落败,生死一线间,康儿才舞出扁担来。由此可知,什么兄弟情哥们儿谊都是假的,连书上说的什么桃园三结义也肯定是骗人的,不觉对康儿心生怨意。
司令部设在一座破庙里,一群服饰各异,南腔北调的军官早已侯在里面。两人进去,所有军官全体起立行礼,吓得两兄弟手足无措。面前桌上摆着杨康提回来的鬼子军刀,刀口残损到几成铁条,本想弃了,是孙大哥让顺回来的。落座后长官部副官请兄弟俩分别细说夺刀经过。
镇东杨康各各述说了一遍,讲完后让侯在外边。听到里面谈话声比较激动,杨康不解的是长官们怎么会这么武断,忙问镇东咋就认定这就是百人斩的凶手。镇东听刚才康儿的讲述,方知原委,遭遇荆柯刺秦的秦王也有拔不出剑来的时候,心下便释然,块垒顿消,反问道:“庙里的惨叫声难道你忘了么?”
军官们散去,镇东被叫进去。在几份《目击证明材料》上签了无数次字,按了无数个指印,并被告知是杨康毙杀了百人斩的刽子手,作为目击者自己只许这么说,接着被送往战时军官培训基地接受轮训。
轮到杨康,屋里只有一个军官和一个穿西装的胖子,面前除了那把军刀,多了个匕首半截扁担,还有一把王八盒子。进屋前有人悄声告诉杨康,那两个是国防部的高官,他们说什么你都只能答是。
胖子比杨康矮了差不多一个头,紧拉杨康双手,满面喜色,京味儿十足地说道:“我的大英雄,感谢您给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快请看看,这是你马上要出去宣传的材料。”
杨康先细看了那把战刀,还是佩服东哥,刀柄上日文刻写的“南京之役杀107人”字样,竟能电光火石般在一瞬间看清,回来路上知道刀上刻有日本字,但慌乱中也没有细看。书面材料上说击杀三个暴徒全是一己之功,深觉不妥,还有毙杀的那个鬼子明明是个马脸大长个,不似照片上这般短小,或许另有凶徒暴毙在自己手下,便说了不是的话来。
一句话激怒了胖子,胖子手捶桌面厉声叫道:“你说,被你敲掉脑壳的鬼子叫什么名字?啊,说不出来,是吧?告诉你,就算你杀了一条日本狗,它就是野田毅,就是向井敏明。这两个鬼子不亡,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无数冤魂。”
杨康被镇住了,想想也是,懦懦然道:“不全是我,那两个鬼子是我哥他们三个杀死的。”
胖子道:“不对啊,应该是他三人合力杀死了一个鬼子,然后看着你狙杀了百人斩暴徒野田毅和向井敏明。这是奇功一件,但英雄也只能有一个。”
是的,英雄只能有一个,英雄的事迹更应该广泛传播。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导引着汹汹民情。先是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勇士杨康斩杀在南京大屠杀中欠下血债的百人斩暴徒野田毅和向井敏明。
紧接着第二天的《中央日报》就用大量篇幅详细报道了具体内容,以特大号外方式报道。头版是杨康身着中央军军服的戎装照和狙杀过程,第二版和第三版是所俘获武器的实物图片及细部特写。第四版和第五版是参与襄理狙击的证明人,有川军上士孙绍晤和中士侯永明,滇军上尉连长杨镇东等三人的目击证明材料。余下版面是日寇屠刀下逃生者的血泪申诉。所有证据链指向明确宣示,犯我中华者,血债要用血来偿。
一时间,其它大小诸报争相转载,各地电台亦作重大喜讯连连重播。前方军队、后方机关、学校、社团组织等,邀请英雄现场演讲的函件雪片般飞来。
战场上刀枪杀敌,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同样称雄。对着人家拟好的讲稿宣读一遍,就能收获掌声、鲜花,还有美女的拥抱,这让杨康很是受用。
特别是《中央日报》,派来刚从美国留洋回来的美女记者杨阳,跟踪报道英雄的日常活动,在生活上更是对杨康关心到无微不至,几乎成了一介随员。每当出门演讲或接受报刊电台吃饭前都要在杨康脸上打点胭脂,口袋中给他备好折叠齐整的手帕。
看这杨阳,却是:肌肤如玉,目比杏仁点点黛,口赛樱桃一抹红,娴静如画上美人,行动又似风摆荷叶。一袭赭色西装也显巴黎范儿更显精明能干,前悬一具锃亮精致莱卡,臂挽半湾蛟皮磨砂小坤包。热点时评如玉盘落珠,忧民生计又似丁香苦结雨中愁。
世居杭城,积祖的皇商,到父亲这一辈成了买办,在上海广州开有商号。出洋数年,新近学成归国。原定探视父母后便游学欧洲,近因欧战越演越烈,孤女海外,也非双亲所愿。恰有世家提携,到《中央日报》做了记者。接领的首份任务,是连续报道宋氏三姐妹救助战争孤儿,让大众近距离感受到伟大女性的非凡魅力。这次受领的是追踪英雄的足迹,通过日常活动,挖掘英雄产生的沃土,微言大义,引导更多有血性的国人奋起抗争,成为民族的英雄。
在学校、在工厂、在后方机关的演讲,虽说照本宣科,鼓动劲儿远超预设。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军政长官都会派员陪侍宴请。可杨康是穷贱的命,架不住二两肉骨头,狗肉上不得席。每每未及开宴,杨康总抽个空,闪身后厨讨碗汤饭,站在角落处,片刻功夫吸溜得干净。人家厨子见身着中校军官服的军官进厨讨食,哪敢声张。
杨阳知道他不善交际,也发现了他的怪癖,为了不让英雄小我的另一面,被喜好猎奇的小报记者捕捉了去,只得紧紧跟随。但凡宴请,除开场敬个酒后就离了席,到街上僻静处找个小酒馆,两人一世界,猪头肉下小酒,杨康说肚肠才不至于弄饥荒。
说到无良的小报记者,那是些掘人祖坟挫骨扬灰,剥人衣物体无完肤,搏虚名寻蝇利,白衣服上给人撒个黑蛋,眼角窝里下个生蛆的角色。
这不,刚收到母亲邮来的几份小报和短笺,杨阳才知道自己居然成了野闻中的焦点人物,无意识的手挽杨康臂弯的街头小照,演绎为桃色新闻的铁证,母亲的便笺上就一句话:一切随心。杨康看到污人清白的报道,暗生退缩之意。
国防部官员给杨康大讲政治仗的意义时,提到野闻一节,就想促成好事。也来不及上告爹娘,杨康满口应承,打小意识中,娶个苏杭美女,此生便死而无憾。就这样,《中央日报》在杨康事迹报道后面有一个重要启示,杨康杨阳某月某日于某处喜结连理。当然是事后补登。
枕席间,阳子一脸疑惑地望着康儿,轻柔地说:“跟我讲讲你的家乡吧。我怎么老是梦见自己身披破毡,置身穷乡僻壤,周遭尽是困窘之人?往美里说,讲讲你的家吧。”
杨康问道:“诗意栖居吗?”
阳子点点头。杨康想了想,念道:“门前良田千顷,屋后青山连绵,四季风花雪月,爱你的人儿永远陪伴着你。”
阳子咯咯大笑,大叫狗屁的歪诗,抚摸着康儿肚皮,一指一戳说道:“草包肚里无墨水。”杨康道:“我们那地虽不是世外桃源,但至少没有无良的小报记者。”
但对杨康而言,紧箍咒也就从结婚这天起戴上了。出门时不论穿军装抑或着便服,都要一尘不染,浆洗笔挺。但凡上桌,不论参与宴请还是在家里,骨碟、菜碟、饭碗一律分开,汤匙和筷子功能不一样,不允许错用,更不许饭菜加汤的大杂烩。连走路说话待人接物,一一加以调教。白天有鲜花和掌声,晚上怀抱美女,让杨康激动得时常夜不能寐,想来天上人间不过如此。
一日午后,阳子说:“这么久哩,你也该给我未曾谋面的公婆道个喜,让他们知道你们杨家跑来了个不要聘礼的儿媳妇。”杨康点头称是,忙给父母和三叔修书报喜。
世堂是在移师鄂南途中收到这个信的。彼时,李宗黄李大人带出来的家乡子弟兵才有明确的番号,作为师直属预备队,李姓子弟为甲连,杂姓子弟为乙连,镇东为丙连,杨康为丁连。
镇东轮训归来,着少校衔任丙连连长,兼理丁连事务。慢慢地从只言片语中大家才套出事情的原委,明白镇东虚衔实职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大,都为镇东抱屈,镇东只是笑笑。就镇中反应强烈,一直埋怨大哥不带自己去,镇东不置可否,逼急了便骂镇中几句。大家询问康儿来信的内容,世堂只呵呵,说一切都好,信被当作点烟的信子用掉了。
世堂最关心的是关领薪饷时候,每每着人便捷处邮给金堂。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信中交待出征人员薪饷分为三份,一份给家属,一份充作公用,一份用来救助孤寡。自家六份,并秀梅杨梅康儿的份子都充在公中。开拔有费用,平日吃空饷,闲暇功夫让子弟们到野地里寻些草料,牲口省下来的草料钱,杂七夹八合计起来,足够日常用度,世堂对此很是满意。
更满意的是生活在一个团体里,后生们许多坏毛病被杨梅逐一矫正过来。单说漱口,山里人家你见哪个用牙膏牙刷来着?祖祖辈辈都是洗脸时鞠一捧清水在嘴巴里,伸个指头进去,上下左右揉搓一遍。一般人就一天搓一次,像杨家这样讲究人家,每每饭后都要刷一下口,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饭后不漱口那是要被长辈呵斥的。有杨梅的督促,大家漱口用牙刷,洗澡洗头用洋胰子。男兵勤刮须,女兵净梳头。风气一经开启,知道上等人家的生活是点滴细节累积起来的,上辈的做作是下辈的模样,先人家走一步就是头等人。于是人人争先个个恐后,精神由头倍儿增。
看见杨梅过来,有人打趣,用戏台上的戏文念白道:“梅爱卿,看朕的牙齿漱好了没有?”或者说:“梅爱卿,朕扭伤了脚脖子,给朕一点碘酒擦擦。”更有那嘴巴上捡便宜的就说:“梅爱卿哪,借你的洋胰子来朕洗个澡。”引得众人呼叫不已,军营中时时笑声一片。
溃兵们神情委顿,军服破损,衣容不整,纷纷后撤。滇军官兵身着簇新军装,水连珠钢枪和法式亚德里安头盔闪闪发亮,三人一排,头尾不可见,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枪炮声轰响的前方开去。
投入战斗是在后半夜接到的命令。
战事吃紧,不再看顾李大人脸面。听说甲乙二连先杨家军参与了战斗,已有伤亡,丙连和丁连接防吴官桥高地。说是高地,就几个房子大小的土包包,上面高高低低有些残破的战壕,四遭还有一些散兵坑。引路的导引军官介绍说,此阵地很是邪门,先是中央军,后是川军,坚守此阵地的官兵悉数阵亡,无有生还者。但此阵地事关集团军侧翼安全,坚守是死后退亦亡。让赶紧抢修工事,按常例,太阳升起鬼子就来进攻。
在有战斗经验的几个军官指挥下,不论官兵,每个人都分头行动开来。好在庄户人家不甚惜力,有的是劲儿,挖土掘坑,抬樑架顶,天亮前阵地抢修完毕。新修无数个土碉堡,还把散兵坑用壕沟串联起来,便于后撤和进击。预设机枪和迫击炮阵地,精确测量好有效打击诸元,单等小鬼子前来送死。世堂令把军旗和杨字大旗插在最高处,二旗中间高祭祖传宝刀。
太阳升起,鬼子没有进攻。
太阳老高了,战斗仍未打响。
烈日当空,阵地上依旧静悄悄,唯有军旗猎猎飘,宝刀闪闪亮,恰似唱的空城计。
司令部担心两个连队脱阵出逃,几次派督察队前来查看,但见所有人都躲藏在战壕的阴凉处,持枪待命,还说笑连连,不似其他连队,人人忧心个个担惊。
午后,仍然没有动静。世堂带人收集起战死将士的残损躯干,在阵地后方空地上起坟掩埋,三跪九叩,祭奠英灵。
太阳早落,天也黑尽,防备鬼子夜袭,派人前出阵地三百步秘设暗哨。这可是世堂自小熟读兵书战策,尽显平生绝学,还有听从大哥二哥的劝,为将者的统兵之道,世堂对此甚为得意。
在此阵地上其他连队没有扛过两天的。
五天了,日军单在别处扰袭,似乎忘记了这个方向。胡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久经战阵熟知攻防,从实战角度教导杨家子弟,利用工事的要点是:其一:枪出壕边头不见;讲的是日本兵枪法好,三八大盖射程远,头在外面容易被点杀。让大家要熟知手中枪的有效杀伤距离,估摸着敌人冲到有效射界内就猛打。其二是投弹莫用全身力。在战壕里你投不了多远,敌未至而先投弹,空落一声响,啥也没用。各人能投多远自己要心里清楚,一定要等敌人离近了再投弹。世堂知道,李大人的影子还是罩着子弟兵的。
第八天深夜,接到命令让快速后撤,大家掘损战壕,捣毁堡垒,迅速撤离。世堂威严,只要避开女客,在儿子们面前仍然和别人荤的素的一并来,八日八夜的临阵对敌,都是在说笑中渡过,祭奠英灵时的虔诚除外。
世堂接令到司令部襄赞军务,有两个特派员下来丙连丁连指导工作。
碰到一个老乡,姓寸,寸仕奇,寸师长热情地送了个紫砂壶给世堂,让世堂受宠若惊。但在司令部感到非常的不适,哪个军官遇到他都要行礼,连卢军长都给他敬礼。世堂识趣,尽量回避。
有军官把世堂请到地图前,告诉他杨家子弟们转战到哪个具体位置了。在和军官们的谈笑中,世堂才知道过五关斩六将那是扯淡,不走直线却兜个大圈圈,关公着实欠扁。身在司令部,心里却时时牵挂着子弟们。
特派员整肃军纪,军中少了说笑。
部队转进到徐州,看到伤员源源不断地往后方运送,枪炮声渐隆,空气中满是刺鼻的硝烟,许多人闻到了腐尸的恶臭。
在一个叫五圣堂的地方接防甲乙二连的防区,看到多是些生面孔,相互熟知的连长也换了人,这两个连已经被打残的传闻得到了证实。
简单交接后,镇东让人抢修工事,撤了左近业已毁损的民房用来加固防御。大家都得过胡教官真传,构筑起工事来得心应手。半宿功夫,简单的土防工事修复完毕。新增的几个地堡互为犄角,深沟高垒,地堡间还可以相互机动补充,迫击炮和掷弹兵也都隐入地下。
镇东带着几个连副排副四处巡视,几个惯经战阵的老兵对如此布防甚是满意。镇东让大家熟悉各自的射界,学世堂样,带人捡拾阵亡将士散落的遗骨,在战阵后面的空地上好生掩埋。
正在虔诚祭奠,人报鬼子来了。镇东赶紧进入阵地。
十来个鬼子兵三三两两,成战斗队形攻杀过来。杨梅隐身在新筑的短墙后,透过瞭望孔朝外观察。看到镇东过来,叫一声“哥”,嘻嘻笑说:“我眼尖,我让他们听我口令,谁打谁不打,多高多低,或左或右,这样总比大家都盲射的好。”
镇东看看也无言语,就站在背后看她如何指挥。只见杨梅令谁谁先放一枪,再作修正,听到口令的便噼里啪啦往外猛打,放完枪就躲回壕底。一个早上没有打死打伤半个鬼子,居然还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
午后,没有一丝风,太阳很毒。鬼子调来了一辆大坦克,四十几个日本兵成战斗队形跟在后面。坦克停在很远的地方,对着阵地后方一阵猛轰,镇东让迫击炮还了两炮,差老鼻子远去了。
正在和连副商讨破敌良策,邻近友军战防炮打来七八发炮弹,坦克成了一团火球。失去坦克掩护的日本兵在掷弹筒狠打了一通后冲了过来,这边依旧排枪还击,迫击炮和掷弹兵偶助一二。杨梅报说:“好。打死了两个,打伤了三个。鬼子兵把尸体拖回······”,突然就没了声响,身子重重摔朝后面。
“梅卿死了!”有人说。
“梅卿死了?”有人问。
不知道是哪个先来一声嚎,两百来号人齐齐跃出战壕冲向前去,手中枪炸响,喊杀声震天,迫击炮和掷弹筒也全部抬出战壕对着敌人一顿猛轰。
日军丢盔弃甲,顾不及死伤,纷纷溃逃。约摸冲出一箭之地,原本监军的特派员死抱镇东,让他下令速速撤回战壕。镇东喝令迅速撤退,大家伙这才不情愿地快速回撤。
才进到战壕,炮弹如雨点般砸过来,大地瞬间抖动起来,犹如簸箕筛黄豆。滚滚声响卷地而来,恰似重槌擂破鼓。每一声轰鸣都像夏雷在耳旁炸响,落石满空,热浪翻腾,硝烟四起,天地间一片混沌。处身巨震中,前后不分,上下无知,对面人莫辩。
足有一顿饭功夫,鬼子才停止了炮击。镇东忙命人抢修工事,计点人马,有几个被落石崩伤,余皆个个耳鼓被震损,人人干呕。谁也不说话,心头却如明镜,此时方知后怕,要是再缓一步,世上再无杨家军。都来看视梅卿,只见梅儿眉心血红一点点,眼睛轻轻闭,面相安详,左边的嘴角微微往上撇,似乎是在冷笑。
镇东命人把梅儿和伤员送往后方。一时间竟失了方寸,扑倒在地,把脸深埋在被炮弹犁开的泥土中,失声长嚎。梅儿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去交待?
卢军长把世堂请到作战室,屏退左右,先唠嗑了会家长里短,又问些气候饮食方面的话,突儿插了句:“梅儿首义,为国捐躯了。”世堂没有反应过来,卢军长又重复了一遍。世堂惊闻,如五雷轰顶,双手擂胸,大叫一声,血喷数升,昏死过去。有道是:天薄我以福,天厄我以遇。欲知世堂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