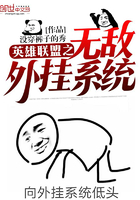走过狭窄逼仄的山路,赵尉松不禁感叹道:“此地与蜀道相比,凶险更甚!这条山路两边石壁夹住,中间只有这么窄的通道,当真有如剑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初汉高祖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后一统天下,最初便是经过这种小道走出去夺天下的!”
众人心知他话中的含义,只是一路逃亡,惨遭追杀,人丁稀落,人人脸上皆是黯淡神色,何谈一统天下?
唯独丁自祯听到赵尉松的话,大为赞许,道:“赵师傅所言不虚,明太祖创业之时,也不过几兵几卒,最终驱鞑虏,复我冠服,何其伟业!”
两人话里投机,相谈甚欢,一路高谈阔论,博古论今。
洪景潇压根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自幼出生时,前朝已经沦亡,生在惜命侯府,过着压抑但富足的生活,所以他从来没想过造反,更别提复国了。
他眼中只有紫若,两个人虽然一主一仆,前后隔开一段距离,但只要有机会,便四目相对,含情脉脉。
赵尉松看在眼里,心中不停叹息,国破家亡之际,怎么可以如此沉迷于儿女私情?
逐渐地话意阑珊,后半段山路上,这位头发突然白了许多的老剑客,沉默着不发一言,心中全是失落之感。
众人沿着狭窄的山路,前行了三四里地,豁然开朗,前面一片开阔的场地,建有几座高耸的瞭望台,数名背着箭袋,手持强弩的哨子站在台上,警觉地盯着入山口。
一名光头的土匪坐在台下,狞笑着走过来,冲着丁自祯道:“丁大爷,今天带几只麻雀?”
丁自祯拱手笑道:“白的十二只,黑的折了翅,还没飞到山下。”
光头土匪脸色一沉,道:“来这么些麻雀,万一被狗咬上,不怕雀窝被端了?”
丁自祯笑道:“顶上知道,不怕。这里有些鸟蛋。”
说着,从怀中掏出二两银子,扔了过去,道:“一点心意,兄弟们喝茶!”
光头土匪咧嘴一笑,道:“丁大爷,阔气!”吹了声口哨,身后一个小土匪牵来八匹腿部异常粗壮的矮马。
丁自祯道:“各位,请上马,此地到山顶还有四五里,山路崎岖,小心前行!”
除了洪景潇独乘一匹,其余每两人一匹,紫若跟着赵夫人共乘一匹。
光头土匪也骑上一匹马,道:“跟我走!”
马上,赵尉松奇怪地问道:“丁员外,这山上莫不是有其他上山之路?”
丁自祯道:“只有刚才那一条路,为何这样问?”
赵尉松诧异道:“那一条路狭窄异常,这些矮马是怎么运上山来的?”
丁自祯哈哈大笑道:“这些马就是小马驹的时候抱到山上,如今养大了而已。山路虽然狭窄,山上人另有办法,从后山低矮的一处峭壁,不到一百米,可以用手腕粗细的麻绳将重物运上山来,然后顺着山路送到山上。”
赵尉松点头称是,道:“原来如此,此山最高处多高?”
丁自祯答道:“这座山有三个峰,分别是金峰、银峰和玉峰,最高的金峰有一千多丈,银峰和玉峰只有八九百丈。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上山门,约有六百丈高,和玉峰落差无几,所以乘马前往。”
山上地势险要,长达十余里的大山脉,最宽处不过数百米,许多房屋半悬空而建,蔚为壮观。
山上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男女老少都有,买卖各种东西,仿佛一个集市,远不是众人心目中土匪窝子的可怕景象。
丁自祯缓步骑马,道:“这里聚集着大约两千多人,男丁一千五六,女子有些是抢来的良家女子,大多是他们上了山的家眷,都是些吃不上饭的老百姓,真正每日出去打家劫舍的倒只有几百个铁杆土匪。”
光头土匪哈哈笑道:“丁大爷,你这话,意思我不是好人呗?”
丁自祯笑道:“比上山前好多了。”那光头土匪乃是杀人越货无数的江洋大盗,被官府追杀急了,投奔神龙寨,没想到这里寨规极严,上了山已经数月没杀过人了。
光头土匪道:“那是!”
没多时,众人穿过了热闹非凡的集市,越过一片哨子把手的丛林,来到了玉峰。
玉峰之上,是一座巨石垒成的堡垒式宫殿,大门亦是能工巧匠用两块巨石垒成,为了避免巨石无法推开,将人封死在里面,旁边的石壁上还凿开一个供人爬出的狗洞,平时用木头塞住。
石门上两条鎏金神龙,威猛凶恶,栩栩如生。
众人下了马,站在门外等候。
赵尉松心道:“虎落平阳,堂堂大齐后裔,居然要在这里等一个土匪头子!”心里有几分不快。
洪景潇倒是浑不在意,他来到山上,只觉新奇,从未见过传闻中的土匪窝,居然是这个样子,与普通的街市县城并无二致,除了有许多堡垒、关卡和哨子。
他并不知道,山上不种粮食,打猎也不足谋生,所以每年都会组织数次大规模的抢劫,到时候土匪们几乎倾巢出动,附近几百里的县城集市为害极深。
紫若乖乖地站在洪景潇身旁,听他低声诉说着着一段日子艰险的经历,不时相视一笑,仿佛终于来到了安全之地,内心庆幸着从此以后可以长相厮守,再不分离了。
韦焕龙终于出现,一头蓬乱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大袍,胸口一面护心镜,金光夺目,若不是光头土匪恭敬地行礼,大家还以为这是看门的老头。
韦焕龙一脸笑容,心情似乎不错,大声道:“老丁,你可算赏脸一次,愿意来我这寒酸地方,今晚别走了,我已命令厨师弄一桌好酒好菜,看我不灌醉了你!”
韦焕龙一次带人下山打劫时,不幸被奸细出卖,遭到官兵埋伏,差点全军覆没,幸好丁自祯发现逃到自家后院的他,并救下了他。因为丁自祯发现这一伙土匪虽然抢劫,却不伤人命,比起横行霸道的官兵甚至都要良善,从此两人成了刎颈之交。
也是在那一次叛徒出卖之后,韦焕龙命人打造了一副防御的铠甲,前身要害全被这巨大的护心镜挡住,后背还有几块铁甲,从不离身,生怕有叛徒刺杀。
韦焕龙与丁自祯热情地打着招呼,完全无视山上的陌生来客。
丁自祯主动引荐道:“韦寨主,这便是我跟你说的洪家二公子景潇,这位是天下第一剑客赵尉松,其他几位均是当世高手,一会逐个向你介绍。要不,先去聚义厅坐着喝茶聊?”
韦焕龙一拍脑袋,笑道:“各位贵客莫怪,看我这脑子,还让大家在外面站着,里面请!”
聚义厅里一半是石壁里凿出的洞穴,一半是凿下的巨石垒成的屋子,四面墙壁均无窗户,因此十分昏暗,点着十来把大烛台,勉强有些光亮。
韦焕龙坐在主位,左上的位置本要让给丁自祯,丁自祯连忙退却,转身请洪景潇坐在首席客位。
洪景潇也不推辞,坦然地坐在左上位置,其他人依次落座。
韦焕龙转了一下眼睛,道:“不知洪公子是齐顺帝的几代孙啊?”
洪景潇一时答不上来,赵尉松脱口道:“我家公子乃大齐皇帝思宗之长子次孙,顺帝乃是伪朝蔑称,岂可当真!”
韦焕龙愕然,随即讥讽道:“既如此,为何坐在京城金銮殿上的不是贵公子?”
赵尉松勃然大怒,手拍石椅,汉白玉的椅背顿时裂出一条缝隙。
韦焕龙自恃他的剑早已在山口被卸下,手无寸铁,毫不在意。
洪景潇连忙笑着劝解:“寨主,大齐早已亡了,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啊!”
韦焕龙哈哈大笑道:“还是洪公子识时务啊!大齐亡了就是亡了,你把这椅子拍坏了,也改变不了事实。”
丁自祯紧锁眉头,他不懂自己这个兄弟之前答应好好地,今天为何如此无礼,言语屡次故意冒犯,充满了挑衅。
丁自祯道:“寨主,你过来下!”
两人起身来到后堂,丁自祯颇为生气,道:“你可知洪家公子乃是大齐皇帝唯一的血脉,若想复兴大齐,只有靠他了!”
韦焕龙笑道:“何必如此生气,我不过是和他们开开玩笑。”他有意激怒这几人,便是想要让他们先动手,到时候摔杯叫出手下,将几个人捆起来交给官府,这样出师有名,万一丁自祯责怪,可以推脱说是这几人先动手,不伤两人交情。
丁自祯怒道:“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上山之时,我便看到有个人面熟,原来是仙门府的跑腿,之前曾在府中见过,你是不是偷偷联络了官府?”
韦焕龙微微惊讶,半响无语。
丁自祯叹息一声,道:“大齐亡了之后,你看这天下,兵戈不休,生灵涂炭,当今皇帝大魏拓跋烈乃是鲜卑族血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但逼迫我等汉人改冠易服,削发束辫,更是屠戮汉人,死伤何止百万,赋税徭役,相比大齐重之十倍。如今,天下思变,人心可用,正是举着大齐后裔的旗号,重夺天下之际,你岂可中了官府的奸计,招安之后,必定暗地除掉你这枭首!”
韦焕龙挠着脑袋,道:“我就是一个粗人,若不是吃不饱,谁会干这土匪勾当!我那宝贝女儿如今正当妙龄,苦无好人家,全是因为我就是个土匪,现在你让我当造反的逆贼,我那女儿岂不是要成老姑娘了!”
丁自祯大笑道:“令千金我早已有妙计,就是不知你听不听我的建议?”
韦焕龙急忙问道:“只要能让我女儿嫁个好人家,一辈子吃喝不愁,荣华富贵,我什么都听你的!”他本来就是个莽撞人,之前暗结官府,沟通招安之事,本来就为了女儿婚事,不愿将她随便嫁给一个没有前途的土匪。
韦焕龙何尝不知道招安了的匪首没几个好下场,官府岂能容忍一个江洋大盗成为当地的富绅权贵,恨不得一下山就送去断头台。
这几日,他犹豫不决,此刻听到挚友的劝告,心中更加拿不定主意。他最关心的,就是宝贝女儿的婚事。
这个女儿是他的独女,与发妻所生,当初当兵回来,娶了一个妻子,两人如胶似漆,还生了个女儿,没想到几年后得了怪病,无钱医治,背着妻子去远近闻名的黄神医医馆求医,不料他张口就要三两黄金。
那可是三百两白银,哪里搞得到?韦焕龙绝望至极。
为了妻子活命,他决定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做了土匪,抢来几百两银子,黄神医果然医术超凡,妻子从奄奄一息中救了回来,只是从此落下不孕之疾。
两人感情极深,妻子劝他纳妾生子,延续香火,他始终不愿意,对独女宠爱有加,视为掌上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