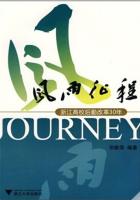之前我和林老在村头的河边写生,这会儿收了画具归往住处。刚走进村子,被几个孩童拦住了;孩子们吵着要林老讲故事听。
林老看了看时间,对我说:“时候尚早,回去也没事可干,我就给孩子们讲会儿故事,你若是想回,就先走吧。”
每到一处地方,林总是能和当地的孩子游戏得很近,他也很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林老有一个八岁大的外孙。可能看到这些孩子他想起了自己的孙儿吧!我时常看见他望着村里的孩子发呆,时不时脸上绽露笑颜。
我突然很想和孩子们一起听林老讲故事,于是说:“也是,时候尚早,闲着也是闲着,和这些可爱的孩子待会儿,心情都能变得愉悦些。”
孩子们很高兴,拉着林老在桥墩上坐下。我坐在林老身旁。
“孩子们,爷爷给你们讲一个《渔夫和鲤鱼》的故事好不好?”林老满脸慈祥的笑容。
“好——”孩子们异口同声。
林老开始讲故事:“有一天,渔夫和他的儿子……”
这是个童话故事,大至内容是讲:一只鲤鱼顺着湍急的流水奋力向上,想要去寻找一处乐园,不料却入了渔夫设置在流水出口处的渔网中。渔夫的儿子问网中的鲤鱼:“这条河流水草茂盛,为鱼之乐土,为何你要弃之而去?”鲤鱼说:“龙门,一生追求之天堂,向往之圣地,理因奋起而寻之。”渔夫大笑:“愚蠢——”
这个故事有很深远的寓意,我懵懵懂懂地能在脑子里整理出一层较浅的意思来。貌似这些孩子只听懂了故事,而完全没懂故事的中心思想——好像觉得不过瘾,吵闹着:“不好听不好听……”要求林老再给讲一个故事。我也觉得和这些八、九岁的孩童讲这样的故事不合时宜,他们单纯而稚嫩的思想哪里能懂这些。
日落西山去,鸟声空如洗。老农收锄犁,孤村炊烟起。
林老看了看时间,面带慈祥的笑容对孩子们和蔼地说:“时候不早了,你们该回家吃饭了,回去晚了,你们妈妈要打的。”
孩子们不情不愿地四下散去。我与林老都各自静静地坐着没动。我不动,是因为在思考刚刚那故事的寓意,想要整理得更深刻、透彻些;而他为何也没动,我就不明白了。我俩就这么安静着坐了许久。
突然,林老深深呼吸了一下,然后缓慢地起身,朝我笑了笑,说:“怎么?还没想明白呢?”
“什么?”我疑惑。
“信念、理想,执着、追寻,然后困境,再茫然。有理想是好事,不过,若是连自己在追寻什么都不清楚,结果就会和鲤鱼一样。”
他说的并不是什么大道理,我自然清楚。所谓当局者迷,事情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自然很难想清楚——这其间有太多因素,也并不是旁观者能够看得清楚看得通透的。若是将这些事情说得太直白,难免让人有觉尴尬。于是我笑着说:“故事是讲给孩子们听的,这些话您该对孩子们说才是。老师就是老师,开口便是教育,且三句不离其中,职业病犯了吧?”
他表情严肃起来,说:“在老师眼里,学生就算是七老八十了,也只是孩子。你是我的学生。”
我笑着说:“这故事是讲给孩子们听的,刚刚孩子们在的时候您又不把这些道理讲出来,现在孩子们散去了,您何故对我不依不饶的!”
“我就老实同你讲吧!这个故事我是讲给你听的。”
“我?”我继续装傻,“为何?为何要同我讲这个故事?”
他看了看时间,然后说:“好啦!时候也不早了,该回村子去了!我想,以你的智商,我为何要讲这个故事给你听,你定能想清楚。再送你一首诗:激流勇进累不休,不知网阵设上头;跃出龙门若是好,就怕徒劳阵中游。”说完,他便转身向村子走去,边走边叹息着摇头。
其实我早就明白了这一切,早在十年前踏上火车离开妻儿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只是身不由己,好似有某种无形的力量一步步将我逼迫至此。
听这里的居民说,这附近有个叫“雾林”的地方,他们说得神乎其神,我与林老都觉得好奇,想来看看。
一大早,天刚破晓,一个当地人领着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有些不可思议——已是晚秋时节,本该天干物燥,这里却是云雾缭绕?云雾绊锁之山色美景也有见过;只是那些景象,雾气都是绕在群山,依着山腰,虽美,却不觉神奇。而此间,云雾却是在山林中;更为神奇的是——若说是因早晨起雾,所以林中便有了雾气,也觉不奇;可是,天空中却没有一丝雾气——着实另人费解。
太阳在林子的边缘,青纱遮面,眨巴眉睫,举步娇柔。阳光射入林中,给林中雾气染上几分色彩;彩色的雾气在林中游走,清晰可见,好似有无数精灵在林子里舞蹈。水流唱着清脆的歌曲从林子里缓缓出来,载着各色各状的落叶。鸟在林中欢唱,每一声歌唱都迎合着轻柔的晨光。
用说的,都太肤浅!总之一句话:美不可言!
我与林老都万般感叹——叹这天设万物之神奇!见了此处景观,才知那画中仙境不过尔尔。
我已是看得目瞪口呆,完全找不来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其间之景色。当然了,画者是无需用语言来述说美景的,这不有画笔吗!
我迫不及待地布置好器材,准备着笔,想要绘一绘这神话中的仙境。今日有幸,见此美景,我的画作若能获此景色,也补了多日来我创作上的空虚无骨、乏味单调。
林老呆呆地望着林中景色,画架还背着没有解下来,完全不见他有作画的意思。
“老师是在构思吗?”我忍不住问。
他看了看我,笑了笑,然后长叹一声,说:“此间之景,文纸言表终觉浅,玲珑妙语不抒怀呀!这一次我想欣赏美景,不想作画。”
“为何?”我不解。
“幽幽山林,浓雾依锁、白露依衣、鸟声绘色;悠悠水流,潺潺水声。万物朦胧神秘,此间景色尽显天地契合。我想,无论是多么优秀的画家也无法将这浓雾弥漫之清晨山林完整地在纸张上表达出来,米勘朗基罗不能、达芬奇不能,你我就更不能了!”
“可是,见此美景,而不作画,岂不可惜,日后定会懊悔莫及。”我说。
“与其如寻章摘句般,绘形不绘意,画得意犹未尽,还不如静静的仔细地欣赏美景来得实在,痛快。”
“您真就见此美景而不为所动?我想,您的画笔应该也早已蠢蠢欲动了。”
“不不不,我的画笔从不作没把握的画,我想我画不了这美景。”
他如此这般,我也不知说什么好。若是因景色太美担心自己画不好而不画,那么,这世上也没有米勘朗基罗、达芬奇之类的名家了。或许林老心中另有想法,他的心思总是另人琢磨不透。
“好吧!不画了不画了!陪这您一起欣赏景色就是!”我心里总觉不快,话语间多少带有些忿忿之色。
“我不是想要扫了你作画的兴致,只是我真的没有心思作画。”
“为何会没有心思?”我问。
“近几日,我一直觉得心头闷堵而思门闭塞,灵感休绝,毫无作画的心情。”
“您是想家了吧?”
他叹了口气,然后拿出兜里的烟斗,塞了些烟草,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说:“或许吧!”
“我以前也是这样,往后便会习惯的。”我安慰他。
他沉思了许久后,叹息一声,看着我,说:“叙文呀!你的画作已经得到同行的认可,而你却还是这般执着追寻,这思想着实可贵。我知道,你一直觉得自己的画作还不够完美,你总觉自己还有待提高,可是,你这追寻何时才是个头呀?!我不是想说知足常乐,我是想说,每个人心里都有道坎——想要超越自我;可是这道坎在每一次越过之后又会再一次形成,反反复复,无穷无尽。”
他的话深深地说进了我的心底。十年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抛妻弃子,麻木而执着地追寻,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茫然与困惑,这值吗?
这时,山上的寺庙敲响了晨钟。钟声高亢而混匀,每一声都那么干脆,好似每一声都脱了俗尘的喧扰,都在三界之外。
不知为何,一听到这钟声,心头一下子平静下来,什么困惑,什么茫然,都去了九霄云外。
我突然心生感慨:“真想在这深山林中的世外仙境做一名僧人,每日晨钟暮鼓,无欲无求。只听佛门语,不闻世俗言!”
突然,林老大笑不止。我顿时茫然不知所措,便问:“老师何故发笑?”
林老停了笑声,淡淡地说:“红尘扼腕残杀,空门炖酒笑佛。烧香拜佛,诵经问禅,心休需几何?”
我没太懂他这话的意思,于是疑惑地望着他。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问:“难道你放得下你的妻儿父母?”
“我——”
“世俗断不尽,佛门酒肉浑啊!”他说完,又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