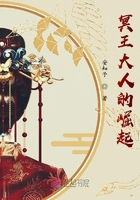那年在西藏安多买马兵站遇到的那只狼,算起来在我脑海里已经沉睡了近30年,它竟然没有死,近来突然活蹦乱跳地浮现在我眼前。还是我想象中的那副吐着长舌头的凶恶的样子,仍然怒瞪着一双射出绿光的眼睛……
西藏离我很远,那只狼却离我很近。安多买马那个冰冻的夜晚,我确实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错误源自一个梦幻似的念头。
提起安多买马这个地方,我对它的恐惧感至今不减。这很可能与它险要的地势有关。那是念青唐古拉山中的一条窄窄的峡谷,两边的崖壁高而陡峭,蓝天被挤成了一道细线,谷底有一条几乎终年封冻着的安静的小河。生活在这里的人很少见到阳光,据说每天的日照时间不足3个小时。兵站一溜排开的帐篷就坐落在谷底的崖角。我们这些来安多买马投宿的汽车兵都是在太阳衔山时到站,一走进谷底就有一种犹如掉入冰窖、与世隔绝的感觉。夜里睡在四面进风的房里,雪花落在被头上是绝对不会化掉的。屋外,峡谷里的风亮着疯了似的嗓门嘶叫着,兵们的鼾声被风卷得无踪无影。后半夜,当风停息下来时,整个峡谷像死了一般。高远的夜空悬挂着几颗晶亮的星星,一眨一眨地挤着小眼睛,使人感到这满山谷的寂静都是星星挤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夜晚,我在安多买马兵站遇到了一只狼。这很可能是我当时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对这个地方产生恐惧、战栗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晚12点钟,该我站岗。四野倶黑,只有深谷的尽头不知是磷光还是灯火显出微弱的亮色。我对一切视而不见,只是胆怯地守卫着我们连的几十辆汽车,夜很静,静得连小河冰面上落下一片枯叶的声音都能听得见。偶尔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飘飘悠悠的冷枪声,拉长了夜的空旷与寂凉。我的心随之一阵抖索。
当时,西藏少数叛乱分子掀起的恶浪刚刚被平息下去,社会秩序很不安宁,常常发生汉人和解放军战士被恶人暗杀的事情。我们的军用汽车即使在行进中也会遭到叛匪的冷枪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入伍才两年的新兵在夜里站岗时产生害怕情绪不足为奇。那一夜,我始终有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整个西藏的夜空下就我一个人,空空荡荡。我站在比夜色更深的黑暗处。
我穿着一件油渍溃的皮大衣,将头深深地埋进栽绒领内,双手紧抱着的木把冲锋枪从右肩膀处伸出半拉枪筒。我靠着汽车驾驶室门站着,巴不得让全身从门缝里缩进去。当然,藏在大衣领后面的眼是不能打盹的。
不知是午夜的什么时辰,我已经完全没有时间的概念了。忽然,我看见从黑绒似的夜幕中钻出两个绿莹莹蓝生生的小孔,直逼我而来。我没有任何的怀疑,立即就想到了:狼!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大人们说,到了夜里,狼的眼睛就是这个样子,说绿不绿,说蓝不蓝,阴森得怕人。从此,我便牢牢记住了狼眼,但从未见过,没想到当兵来到西藏遇上了这样的狼眼。
那两只绿蓝参半的眼睛继续朝我逼来。我的心和身子同时在收缩,想:完了!我很快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我没有想到,那狼走到离我大约100米处的地方时顿足了。只是两柱如火的绿蓝眼光仍然射向我,好像要把我戳死。
我浑身哆嗦着,冲锋枪已经下肩,把食指放在了扳机上。
狼一直再没有向前挪动,就那样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看不见狼身体的任何部分,它的一切都聚集在那双眼里。狼眼,就是狼。狼的凶残、可恶难道就是一双眼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那收紧了的心反而渐渐地松弛了下来。也怪,那一瞬间的我,一切杂念都离身而去,包括对这突然从天而降的狼眼的惧怕情绪。整个西藏的地面上仿佛就剩下我与这只狼了。不是我死就是它死,我有枪在手。
我诅咒那狼不得好死,让它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把我收拾掉,尽管我做好了与它拼搏的充分思想准备。
我不敢多看那狼一眼,但是我又不得不与它对峙着。我把枪握在了手里,随时用食指把一颗或几颗子弹送给狼。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不进攻我,我是不主动伤害它的。我在车场站岗,我的原则是自卫。
我和狼整整对峙了一夜。狼始终没有靠近找,我自然没有开枪。奇怪的是,在我站一小时后,该来接替我站岗的同志不知何故没有来换岗,这样,我就一直站到天亮……
随着夜幕的退去,那狼的绿蓝色眼睛也消失了。唐古拉山谷又一个宁静而清冷的早晨来临。
我下岗……
几十年过去了,我忘不了安多买马的那双狼眼。说不上是恨它,起码没有达到咬牙切齿的程度。狼毕竟没有伤害我,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否则,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就难说了。
事情的转折是由于一位友人的点拨,我豁然开朗。
那是不久前的事,我和一位高原老战友意外地在京相聚。海阔天空的漫聊中,我不由得提起了那年遇到狼眼的事,岁月把这故事沉淀得很沉重、很清晰,我讲得十分仔细,连那寂静的夜色、狼眼的颜色以及我当时的恐惧心情都追忆得惟妙惟肖。总之,我认为那夜恶狼没有暗算我是绝对的侥幸。不料,友人听了放声朗笑,问:
“狼眼,在安多买马兵站?”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
他又一次朗笑数声,说:“你错了!完全错了!那不是狼,是安多买马兵站的军犬。绝对不会错,是军犬!”
我犹如挨了一闷棍,事情为什么如此离谱?我把一个不是狼的动物当成了狼,几十年呀!仅仅就因为那双绿莹莹蓝生生的眼睛?原来天下并不是就恶狼有这种眼睛。友人继续着他的话:“那时候,那个兵站的军犬训练有素,这是青藏线上许多人都知道的。它常常在夜里出来伴哨兵站岗,给哨兵壮胆。有一次它硬是撂倒了一个窜进兵站行凶的叛匪,将那恶人的脸抓得血迹斑斑,把衣服撕得扑簌簌。”
比狼还恶的狗!只是它是个忠实的哨兵。
我不知说什么好,拉着友人的手不住地摇着,摇着,许久才说了一句话:
“我错就错在把西藏的猎犬当成了家乡的狼。”
事情就这么简单。
人在开悟、清醒以后,往往觉得世界很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