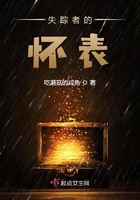刚刚还显得压抑不住心中怒火的泰勒,此时看起来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目光躲闪的转向了一边盯着,盯着自己赤脚站着的黑胡桃木地板上,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
鲁道夫见状装作嗓子不舒服一样轻咳了一声,然后拉开果汁罐子的拉环,放在嘴边发出刺耳的咕嘟声。
然后不紧不慢的将即将燃烧干净的烟蒂丢进了刚刚喝完的易拉罐中,随着滋啦一声烟头被残余果汁浇灭的声音响起。
这位大大咧咧的警局探长,此时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一样,随意的靠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着面前泰勒,反客为主的开口说道,“都已经现在这个时候了,我觉得你应该和你之前说的那样。
不要有任何隐瞒,当然我们也并不会为一些关于你和劳伦斯之间最隐私的问题去刨根问底,毕竟那些是狗仔最关心的地方。
好吧,告诉我们为什么那天晚上劳伦斯会给一个脱衣舞女郎打电话,甚至在自己的未婚妻即将在清晨回家的时候。
还要让那个女人来到自己的家中,我不认为他会自信到认为自己可以打扫干净所有的痕迹。
而且,虽然米兰达心里很清楚劳伦斯背后肯定不止她一个女人,但是有些事情不撕破脸皮,两个人依然可以波澜不惊的生活下去。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劳伦斯无论是谋杀或者自杀,你都不是那个凶手,甚至和凶手没有一丁点关系。
现在你更是充当着一个证人在帮助他,还在犹豫什么呢?
难道你真的想看到米兰达用那张遗嘱拿走两亿八千万英镑吗”?
或许是鲁道夫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泰勒咬了咬牙脸上泛起一抹不自然的潮红,直接将烟蒂丢在昂贵的地板上,咬牙说道。
“我无意间知道了米兰达会在第二天清晨回来,所以想要在她刚刚回来后,不给她留和劳伦斯接触的机会,所以我们决定去瑞士。
可是我贪心了,把事情想的有些简单,当时觉得自己很聪明,在下班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劳伦斯的办公室,给他递上了一杯手磨咖啡。
虽然几乎和以前每一天一样,劳伦斯伸了个懒腰,然后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让我坐上去,然后惬意的喝了一口那杯咖啡。
当我伸手挡住了他将要亲过来的嘴,半开玩笑的说道,我晚上想要去他的别墅过一晚上,怎么样?
当然,和我想象中一样,他没有半分犹豫就拒绝了我,他虽然说的很婉转,但是却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所以我悄悄的爬在他耳边告诉了一个可能会让他不高兴的消息,不过,比起可能会得到的结果,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泰勒说到这里,忽然紧紧停下来话声,整个人像是垮了一样,失魂落魄的走到壁炉前的摇椅跟前。
如同被抽去了浑身的力气直接躺在了上面,丝毫没有在意此时她正压在那张昂贵的爱马仕摊子上。
双眼茫然的看着天花板上那盏繁复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泰勒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胸口像是喘不过气来一样,开始剧烈的起伏着,不过伸手摆了摆,阻止了想要过来的几人。
“我爬在他耳边告诉他说,这杯咖啡里被我放了一点催情的药物,现在他有没有感觉浑身很热?想要一直和我待在一起。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就是想和劳伦斯一直待在一起,我已经跟了他七年了,默默的从一个懵懂无知刚刚走入社会的小女孩,到现在这个样子。
或许再过几年,免不了身材有些走样,皮肤也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光泽,那时候我呢?
甚至还不如他的两任前妻,我们说白了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可以把我像是垃圾一样丢出去。
我能怎么办,想要在伦敦这种地方保持着早已养成习惯的生活,我能有什么办法。
不过那些药物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作用,劳伦斯不耐烦的安慰了一下我。
哈哈哈,可能是打发了我,然后就回了家。
现在看来是我太急了,如果稍微等一下,那么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那天晚上我就会和劳伦斯住在一起。
我们两人一起等待着米兰达的到来,静静的看着那个该死的女人,看见面前这一幕嘴里发出尖利的叫声,恼羞成怒的将手中的包丢过来然后扬长而去。
而我呢?可以撕掉这两张机票,然后乘坐着那架舒服无数倍的湾流G650,和劳伦斯前往早已决定的瑞士。
在那里我会有一周时间让这个男人完完全全只属于我一个人,我要让他改变主意,让计划好的好的婚礼如期进行,而那个新娘则由米兰达换成我。
可是现在一切全完了,劳伦斯没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我真是做了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
随着泰勒微微开始耸动的肩膀,一阵压抑着的抽泣声从那张同样开始晃动的摇椅上传了出来。
壁炉中摇曳的火焰,偶尔发出一声木材燃烧后裂开的声响,像是在回应着脑海中被后悔充斥着的那个失去所有依靠的女人。
虽然看起来泰勒像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女人,想要通过自己的身体,永远的将劳伦斯这个像是长期饭票一样的男人,变成她的永远。
可是漫长的七年时间,足以让这个女人将那个并不能见过的爱情,当成自己的习惯,从而产生一种错觉,同样劳伦斯也像她一样,对待自己有着近乎习惯的感情。
所以,泰勒脑海中才会有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吧。
毕竟除了情妇的身份,她明面上更是劳伦斯的秘书,几乎大部分时间两人的距离异常的接近,都工作在那个奢华的办公室中。
正是因为这些劳伦斯错误传递给她的错觉让泰勒可以开玩笑一般将那些催情的药物倒在那杯手磨咖啡中,然后还故作无事的对自己的老板撒娇般如实道来。
可是这件事情虽然和她有着一定关系,但是绝不是决定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偶然。
虽然现在并不想打扰这个哭泣中的女人,可是他们的时间实在是很紧张,卡卡罗特嘴角抽了抽,还是开口问道,“抱歉,可能这么说不太合适,但我还是想要问一句。
为什么你会想到放那些催情的东西,嗯,我觉得你并不像是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