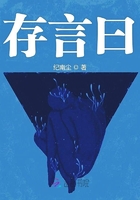黑马河,即黑马河乡,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县境西北部,海拔3200米左右,距县府驻地148千米,是青海湖环湖公路的起点。在湖边有一些藏民开的帐房宾馆,他和梁应情就是在那里相遇的。
“这么冷的鬼地方居然有这么漂亮的景色啊!”陈长安把手揣在口袋里,依然觉得空气冷得他呼吸都困难。
青海湖属大陆性高原半干旱气候,年平均气温3.2℃。而这里的昼夜温差变化,让人在一日之中便能感受到四季变化。此时已是日落时分,夕阳已有小半部分被湖光吞没,冷风也仿佛要为夜的到来而拉开了帷幕。
那个人就站在湖边上,金色的光芒把他的发丝映得发亮,即便是呵出去的水汽也如同向天飘散的丝绸,夺目而耀眼。只是,他微微低下了脑袋,落辉照不到的眼睛毫无波动,如同在工业发达的城市里夜幕之下的天空——透不出光芒。
“少爷,你也该添多一件衣服了,这里的晚上气温会低很多。”如同以往一样,背后那人总是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为自己披上一件外套,沉稳的声音虽然没有一丝波动,但陈长安知道这是那人的温柔。
“皮卡丘!你看看那人,明明穿得和我差不多厚,他都一点事没有,我又能有什么事!再说了,悄悄跑到别人背后,是会给人吓出心脏病的!”陈长安不满地撇着嘴说道。
“如果您能换一个方式叫我,我下一次会注意的。”何避丘把一杯黑红色的酒放到了陈长安的手中,“这是您要的自由古巴,弄来的方式十分不易,请您尽情享受。”
“哼,我知道了。”陈长安扭过头,拿着酒向自己的帐篷走去。
何避丘看向湖边站着的梁应情。此时的体感温度已经到了10°C以下,而这个人上身还是只穿着一件薄卫衣和一件风衣。他感觉,与其说是梁应情不畏严寒,更感觉他像是忘记了寒冷的感受一般,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即便是仿佛要把世间万物都染成金红色的晚霞——如同这片土地古老的民族让人想到的颜色,但他一身黑衣黑裤站在那里,连同鞋子和眼镜框都是黑的,仿佛周遭的一切都被他隔离了一般。
“梁先生,十分感谢您的帮助。”何避丘向那人说道。
“没什么。酒本来就是我朋友带来喝的,虽然他其实是个咖啡师,但也勉强会调酒。更何况你也付钱了,这只是个买卖罢了。”梁应情转过身面向何避丘,但他身后的光芒让阴影覆盖了他整个正面,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即便如此,还是要谢谢您。另外,现在的气温低了很多,请您注意防寒保暖。毕竟我们这些南方来的人,在这个高原地区感冒了可不是一件小事。”何避丘微微地鞠躬说道。
“嗯,谢谢。”
梁应情点头致意,走向帐篷宾馆,正好每一步都走在自己被拉长的影子上。
何避丘看向那个背影:虽说那人是个少年,无论是在外貌还是气质而言都是如此,但总觉得看着他,心里便有些不祥的预感。
回到帐篷里的陈长安心满意足地喝了口酒——这可是自己的成人认证啊!
何避丘大了他不到十岁,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何避丘便开始作为他的贴身侍从照顾他。虽说他们家也并不是什么混黑道的家族,但何避丘依旧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生怕他下一刻就会从眼前消失一般。
也正是如此,陈长安虽然没有对何避丘有什么不满,但总是时不时地给他出点难题。但何避丘也不是毫无条件地满足他,违法违规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比如给未成年喝酒。
“啧,虽然是第一次喝,不过这东西可真棒啊!”又感受了一下冰凉的酒水从舌尖流向喉咙直至深处的感觉,陈长安心情愉悦了不少。
是夜,湖边寒风起舞,如同恣意杀戮的野兽一般,在无人能见之处呼啸狂欢。
“老梁,明天要不要去看看……老梁?”一个男人走进了帐篷,却没看到这几天已经习惯性能看到的那个在角落里看书的身影。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信号差吗?”男人皱着眉头看着手机屏幕里满格的信号标志。
“调酒师先生,您有没有看到我家少爷?”何避丘拉开帐篷的帘子,喘着气问道。
“没有,你有看到梁应情吗?就是带你来找我的那个人。”
“最后一次见到是把酒给我家少爷的时候的事了,那时候天还没黑。”
“这样啊……”
男人看向帐篷宾馆外,皱起了眉头。“怎么外面这么嘈杂了?”
“好像有不少人发现同伴不见了。”
是的,原本在这个冷风肆虐的夜晚,湖边上的人很少。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似乎都走了出来,呼唤着同伴的姓名。
“喂,方教授吗?”男人似乎察觉了这夜空下的青海湖旁似乎出现了不该有的问题,拿起了电话,“是我,风过川,梁应情他失踪了!”
何避丘看着陆续拿起手机报警的人群,觉得自己的太阳穴上有根筋在跳动。
而这本不寂静的夜晚似乎更无法让人平静了。
“所以说,有没有人和我说说这是什么情况?”陈长安稍稍眯了一会儿,醒来整个世界似乎都是一片白色,没有边际。
“皮卡丘!”陈长安喊道,然而并没有人回应。
“何避丘!别闹了,这是个什么情况?”陈长安再次喊道,然而回应他的依然是令他咬紧牙齿的一片沉默。
正当他拿出手机看到信号格全空着的时候,一个仿佛本人十分喜悦的声音响了起来:“哎呀哎呀,没想到这边也有一个能醒得怎么快啊!虽然没有第一个那么快,但是也是一个可造之材啊!”
“谁!玩这种无聊的装神弄鬼,有本事出来啊!”陈长安攥紧了拳头。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先等一会儿,这边这个问题少年实在是不好处理。”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叫你出……”
真实的世界是疯狂的,在有规律的地方充斥着无规律,所谓的真实和虚假在很多时候没有意义。而世界本身也不是非黑即白,如同此时陈长安的眼前。那是突破白色的一抹黑色,就像在面巾纸上浸入的黑色墨水,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扭曲起来。
“爷姑且再问一句,你他娘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个声音从陈长安的身后响起,言语中透露出来的戾气就像是上世纪香港警匪片里的混混头子。
“哎呀,我都说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谁知道呢?”如同电脑卡顿以后突然出现的在屏幕里的页面一般,一个发色黑白参半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了陈长安面前的不远处。但目力不错的陈长安似乎怎么也看不清他的面容。
“呵,是吗,那看来你不是个东西啊,那爷就教你怎么做个东西吧。”那个声音低沉了下来,从陈长安的身后走向前。
“等一下,现在到底是……”
“哦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满是戏谑的声音在陈长安不远处依旧响起,但毫无真实感。
“闭嘴,老实待在这里。”低沉的声音来远处像变戏法一般,手里“长”出了一根长棍,随手挥了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是他唯一记得的眼神——如同霜降以后凝结在枝头的冰锥,居高临下,锐气逼人。
“等……”陈长安突然觉得脑子又开始混成一块,意识开始逐渐涣散。
“哎呀,看来他的自我还是没有你那么强烈呢,话说你真的确定要揍我吗……”
似乎有人猛地在自己面前动起手来,他似乎还听见了棍子带动的风声,但眼前的一切逐渐模糊,眼皮似乎又让陈长安不甘地沉重了起来。
“等等!”再度睁开双眼,眼前的天花板是他熟悉的房间的模样。
“做噩梦了吗?”熟悉的声音响起,陈长安才回想起昨晚才刚刚和梁应情见面。
“嗯,一个不太好的梦,为什么不早点来叫醒我,皮卡丘。”陈长安噘着嘴,不满道。
“因为少爷您说的是要我八点来叫醒你,我也才刚刚进来。”何避丘递过去了一条刚刚用热水洗好的毛巾,并在旁边放了一杯温度刚好的温开水。他深知不这么做会让面前那张好看的脸又变颜色。
“啧,算了算了,也不是什么恐怖的噩梦。”
“只不过似乎是我已经忘记了的东西。”这句话他没能讲出口,因为他可不想再让何避丘更加像监视一样地照顾他了。
陈长安梦里回忆的场景之后,在青海湖附近某处废弃的民居楼里,他被何避丘叫醒,醒来时他身上还披着一件黑色的风衣。
与此同时,这栋民居的其他房间里也发现了其他失踪的人,但是唯独没有发现那个在湖边站着的少年。而陈长安对自己昏迷前的事也已经几乎忘光了,脑子里对那个晚上的记忆十分混乱,只记得最后那个直刺人心的眼神——或许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而何避丘把他叫醒的样子也一样令他难忘:原本梳得整齐得体的头发有些许的凌乱,本该平静无波的眼睛满是血丝——如同纪录片里失去了王位的狮王一般——那是他唯一一次见到何避丘狼狈成如此模样。
当然,他也未曾忘记那件风衣也被何避丘拿走了。
在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正当陈长安在练习着舞蹈的时候,何避丘把电话递给了陈长安:
“陈长安先生吗,您好,我叫梁应情。何避丘先生说,您能帮我一个忙。”
第一次到那条街的时候,他从没想过在一座繁华的城市里还有这么一条街:一排排过去高低不一的房子,看起来虽不老旧但却有些陈年的韵味;各色各样房子的一楼基本都是店铺,各色各样的店铺有各色各样的招牌,招牌下各色各样的人们却似有默契地交谈——仿佛这里自成一方小天地一般。
“这就是,叁贰壹书店啊。”看着木质的招牌下,店面整体是比较现代的复古感,这和陈长安想象中的略有不同。“还以为会是那种已经开了很久很久的书店呢。”每次前往陌生的地方,何避丘都会提前调查出一些资料,而他也自然懂得一点。
“少爷,以前这里就是一片村子,后来因为一些变故,村子就迁移了,而这里也就逐步发展成了一条老式的商业街。”何避丘在他身后说道。
推开店门,陈长安注意到的不是那一排排的书架,而是眼前的那一抹白雪。
“哇!”陈长安吓了一跳,立马往何避丘的身后躲了过去。
而“白雪”只是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朝书架的后方叫了一声。
一个有些微胖的年轻人走了出来,脸上还有些整理书架而留下的灰尘。相比于湖边那时见到的模样,年轻人似乎成熟了些许。
“你好,陈先生,何先生,欢迎光临。”
“你好,梁老板。”
原本梁应情只是希望何避丘能帮忙找个地方能照顾敖清的,没想到陈长安本人自己来了。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梁应情也对敖清有所认知了:
这狗东西完全就是披着狗皮的人!
还在西藏的时候他就知道敖清不是一般的狗。虽说他也没有见过其他的藏獒,但是能嘴里叼着木棍当剑使的狗肯定和其他藏獒不一样!更重要的事,这家伙的脑子简直就是人脑,说什么都听得懂:不管是叫它吃东西,还是夸它,或者是骂它,它都听得懂!
梁应情很想拿本婴幼儿启蒙书来教它读书认字,但是现在他真的没有时间了:他也要去读大学了。虽然每个寒暑假他一定会回来,但是他父母也是上班族,还是要找个能照顾它的地方。
“因为路敌说一定要替他好好照顾敖清。”梁应情心里不由地回想起那个仿佛能和藏地的雪山草原融成一体的身影。
“梁先生,请问刚刚那只狗就是敖清吗?”何避丘看着有点走神的梁应情问道。
“啊,对。它现在应该去拿行李了。”梁应情回过神来,看向何避丘。
两人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眼神之间的交互还是被陈长安看到了。
“拿行李?它会自己拿行李吗?”陈长安的眼睛似乎能蹦出小星星。
“嗯,敖清很聪明,你只需要把它当做一个披着狗皮的人就行了。”梁应情微笑道,平静而随意。
“啊,这样啊。”
陈长安微微皱了皱眉——那是一种自记忆而来的违和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通常来说,一个人的表情分很多种,但对陈长安而言,他认为最基本的就分为大致两类:无意的和有意的。
无意的表情除了表现人的心情和态度,同时也能反映出这个人的心性。有意的表情虽然可以尽可能地作态到神似无意的,但神似终究只是神似,眼神和气质以及一些微动作是掩盖不住的。而人的眼睛虽然在有意的情况下无法完全捕捉至这些细节,但通过反复观察来锻炼之后,可以利用眼睛无意下捕捉到的这些细微之处来感受到这个人真实的情绪。
倘若说那个记忆中模糊不清的少年与现在在他面前的这个少年是同一人,那么这对为了歌舞而早已习惯相信自己的眼睛的陈长安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前者的性格像是拉满的弓上那尖锐的箭,仿佛下一刻便要刺透心脏;而后者则普通到没有任何特点,就像是森林里的一棵树,草原上的一株草。
“真有意思。”陈长安忍不住说道。
“对吧,敖清虽然看着比较凶,但性格还不错,应该是不会让你们太为难的。”梁应情看着那只大白狗叼着一个小拖车从书架后出来,拖车上是一张精致的小床和装着宠物证等东西的小包。
“嗯,既然我帮了你一个忙,那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呢?”陈长安微眯眼,看向梁应情。
梁应情回头看到了他的眼神,眼底有一丝波动,但却毫不犹豫地说道:“当然可以。”
何避丘愣了愣,看了看那一狗一人,从敖清的嘴里接过小拖车。
陈长安也把何避丘的神态看在眼里,但什么也没说。
“少爷,少爷,少爷!”何避丘忍不住捏了捏陈长安的脸,手感倒也一如既往的不错。
“皮卡丘!你是想死吗?”陈长安猛地咽下嘴里的三明治,差点没忍住跳到餐桌上。
“我不想死。但是你吃这个三明治已经快十分钟了。”何避丘认真看了看手表,说道。
“嘶!”顾不上刚才何避丘对自己的“冒犯”(反正在这个房间周围也没有人),陈长安猛地加快了自己的吃速。
角落里熟练地倒着温开水的何避丘微微笑了笑,但眼底也多了几分阴沉,他也差不多猜到自家少爷在想什么。
在黑马河的那个时候,他用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找到陈长安的时候险些让他疯掉。当他得知警察找到陈长安时,他恨不得向手下忠实为他拼命的人怒吼。所以,他也自然不会忘记,那件披在陈长安身上的黑色风衣是谁的。
“有恩报恩,永远不要忘记这句话。”这是何避丘的父亲临终前对他说的话。他的父亲是一个保镖教练,和陈长安的父亲相识多年。在他家穷困不堪的时候,陈长安的父亲接纳了他们父子二人,让他的父亲当陈家的管家,而他的母亲早已死在了精神病院。但日积月累的各种疾病终是在打倒了他那印象中高大的父亲。那时候,他才刚上小学一年级。
没有人生来坚强,也没有人生而自立。
陈长安的父母都是工作狂,而且他们夫妇二人同时经营着多个行业的事业。虽然他们对待何避丘谈不上无微不至,但也可以说是待如亲子了。只是每次家长会的时候,他们二人都无法在场,而是让他们这个行业或那个行业的秘书来现场录音,并向老师咨询他的学习状况。他的同学都以为是他的父母工作太忙而无法到来,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早已没……
“何避丘,你说我要是女装去看阿琳,她会不会更开心?”陈长安的声音打断了何避丘的回忆。
“我想代琳小姐肯定会很开心,但这样的话您也会被看过您演出的人发现你去了一家宠物医院,并且和那里的一个护士小姐十分熟悉。”
“啧,要不干脆告诉他们我是男的算了。”
“不,你要是这么做,搞不好会有偏好这一口的人更为狂热。”
“嘶!那还是算了吧……”
何避丘微微摇了摇头——陈长安总是能有意无意地打断他负面情绪的增长,就像许多年前那样。
何避丘初三那年,他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虽然他也算是班里成绩出色的学生,却也依然不可避免地喜欢上一个女生。当然了,只不过他是不会主动去和那个女生交谈的——不仅是因为他心里清楚早恋是不允许的,更重要的是那个女生有了一个喜欢的男生,而那个男生正好坐在她的后排。
“能看着她好好的,这样就够了。”他对自己如是说。
那是个怎么样的女生呢?他也快记不清了。他只知道一点,那个女生虽然有些内向,但是她很爱笑,笑起来就如同夏日午后微风下的花儿,轻柔而温暖。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直到那件事以后就不再是这样了。
“话说你明明都已经有女朋友了为什么还和那个小哑巴有联系啊?”那个男生的跟班问道。
“嘘,她还不知道呢。白痴,有人白送给你东西你会不要吗?正好省了我一笔钱去送给我女朋友。”那个男生嘿嘿地笑道。
剧情老套得让人难以吐槽,如同肥皂剧里固定的套路。似乎下一个桥段就应该是何避丘“重拳出击”。
“人渣。”但何避丘只是在心里这么骂道。
他用左手写了张纸条,放学后趁着教室没人放在了那个女生的抽屉,告诉了她这件事。他本以为故事就到此结束了,但却没想到自己第二天一早到教室也发现自己的抽屉里有一张纸条:
“谢谢你,我知道了。”
何避丘纸条是用讲台上老师留下的草稿纸,写字的笔用的是班里人手一只的填涂答题卡用的铅笔——何避丘实在想不明白,在这个没有摄像头的教室里,她是怎么知道这是他写的。
除非她“亲眼”看到……
“走了走了,梁应情那家伙居然都到了,本来应该是我先到的!”陈长安急急忙忙地走出房间,头也不回地说道。
“那是因为少爷您换衣服用的时间太久了。”何避丘跟了上去。
“你管我!赶紧下去开车!”
“是是。”何避丘微微笑道。“这个表里如一的家伙。”他心里这么说道。
在看到那张纸条之后,他便不再管这件事。但不到一个月之后,他便听说学校有个女同学得了怪病住院了。何避丘本没有太在意这件事,但是当那个男生和其他男生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不由地看向那么女生。而她呢?依旧是微笑地看向他。
只不过,他不再觉得那个笑容那么温暖舒适了。事情似乎也算是到此为止了。
中考很快就来了,然后又很快就结束了。毕业那天,他回到家里,打开书包,发现多了一个信封,里面放着一只摁压式的水性笔笔,一封信,一朵花,以及一小袋粉末。
信上的字有些是用铅笔写的,一笔一划分明,但却不怎么美观。
“笔里藏着一双眼睛,藏着一颗心,藏着过往,藏着将来。
ps:不要去闻或者尝一下那袋粉末噢”
何避丘拆开那只钢笔,这才发现这个笔帽确实长了过头一点:这分明就是个微型的充电式摄像机!
那朵花呢?虽然被压扁了,但处理的方式很好,依旧看得出它本身的艳丽。但何避丘这时却没有什么欣赏的心情:因为这是一朵夹竹桃。
“夹竹桃整棵植物包括其树液都带有毒性,其他的部分也会有不良影响。夹竹桃的毒性在枯干后依然存在,焚烧夹竹桃所发生之烟雾亦有高度的毒性。些许或10-20块叶子就能对成人造成不良影响,单一叶子就可以令婴孩丧命。对于动物而言,致死量低至每公斤体重0.5毫克。大部分的动物对于夹竹桃都有不良或死亡的反应。”
他依然记得他们的生物老师在课上如此提到过,但这也是初二的事了,老师也没有再细说下去。而生物这门课也并不是他们的中考内容,何避丘之所以记得也只是因为他每次上学的路上,都能看到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上有长着种花这样的树。
而那一小袋粉末,他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
一时间,他觉得脑子有些乱。突然而来的信息如同海上巨大的漩涡,让他的脑袋有些昏沉。毕业典礼后自己一个上午收拾行李收拾宿舍就已经让他疲惫不堪,此时的他只想躺在床上睡一觉,什么都不去想。
“皮卡丘哥哥,皮卡丘哥哥!”稚嫩的童声勉强将他唤醒,他依然觉得脑袋有些刺痛。
“这个香香甜甜的东西还有吗?”
“嗯?什么香香甜甜的东西?”勉强睁开眼睛的一瞬间,何避丘只觉得自己的脑袋瞬间清醒了,仿佛洪钟在耳边敲响——陈长安肉肉的小手正拿着那个被他随手放在书桌上的小袋子!
他此时已经近乎无法思考了,但身体依旧是本能地动了起来:打电话,抱起还没反应过来的陈长安冲出门去!
深夜,陈长安的父母终于来到了医院。本将他们二人早已视为自己“工作繁忙的亲生父母”的何避丘却没有敢去和他们见面。
恐惧,不安,内疚,迷茫……混乱的情绪如同波涛骇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击着何避丘。医院的外附楼梯散播了夏天凄寒的月光,冷得何避丘的身体忍不住发抖。
洗胃,输液,服药……想起陈长安那好看的面庞上的泪痕,何避丘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和他说“对不起”,他真的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现实远比戏剧来得更加的突然与猛烈。一件又一件事接连不断的到来,其中的痛苦就如同一刀又一刀的凌迟。
医院外依旧有过往的车辆,不时也有救护车出勤,但这并不影响院区该有的寂静。走廊感应式的灯忽亮忽暗,只不过更多的时候仅有值班区的灯亮着,就像是黑夜从天空渗透到了病房里。
“哒,哒,哒,哒……”何避丘敏锐的听觉告诉了他:有人正在靠近。
五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稚嫩的童音试图让何避丘惊吓,但何避丘还是忍不住“噗嗤”一声地笑了出来。
“吓到了吗?吓到了吗?”撩开挡着脸的假发,陈长安眼里蹦着小星星一般地问道。
“嗯嗯,吓到了。小少爷,你这是哪来的假发。”
“这个是睡着在病房门口那个大桌子上的护士姐姐旁边发现的!”陈长安得意的笑道。
“等会儿护士姐姐要是醒了发现自己东西丢了怎么办?跟我还回去,不然一会儿她醒了就算你要道歉她也得打你的小屁屁!”
陈长安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屁股,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何避丘哥哥,对不起!”
“嗯?”
“之前爸爸妈妈来得时候在我的病房里吵了一架。爸爸说妈妈没有教好我,没让我学会不乱吃东西;妈妈说爸爸不该把会议安排在今天,不然他们就能早点回来了。他们吵的时候我已经醒了,只不过我不敢说话,就继续装睡。”
陈长安把脑袋低了低几分,继续说道:“如果我没有乱动哥哥的东西,不去乱吃东西,就不用让哥哥带我来医院看病了,也不用让哥哥晚上还要待在这里了……”
听着陈长安说的话,何避丘只觉得眼睛有些滚烫。
“对了,爸爸妈妈还从护士姐姐那里要来了纸和笔,写了封信放在我床头,说是留给你的!”陈长安摘下假发,从里面拿出了那封信。
借着走廊里的灯光,何避丘看到自己的手又有些发抖。他接过那封信,打开:
“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问过一个算命很灵的神婆,她说过长安这个孩子这辈子注定要有三次灾祸,都是因为他自己造成的。事情的经过你也告诉了我们的秘书了,没能参加你的毕业典礼还要再让你送长安来医院真是辛苦你了。我们夫妻二人忙于工作也不会带孩子,而你自幼便独立也没让我们怎么操心,现在还要你帮忙照顾长安。不要为这件事而难过,相信长安这个孩子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怪你的,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热流再度涌上何避丘的眼眶,温暖地从眼睛滑向脸庞。,
“皮卡丘哥哥,你怎么了?”感觉到何避丘的情绪有些波动,陈长安问道。
“没,没怎么。只是有些困了,打了个哈欠想睡觉。”
“那你要不要去我的病床上躺会儿?”
“不用了,我就随便找个地方坐着就可以睡得很好了。倒是你,大半夜不睡觉还想跑出来吓我!”何避丘捏了捏陈长安那柔嫩的脸蛋,手感好的令他有些不想收手。
“五现赛就灰取碎校(我现在就回去睡觉)”
“好,我们还得把护士姐姐的假发还回去。不过你长头发的样子还挺好看的,说不定穿起裙子来也挺好看。”
“真的嘛?要是我穿裙子,皮卡丘哥哥会给我买可乐喝吗?”
“如果你不叫我皮卡丘我就会买给你喝。”
……
“让我猜一下,早上赖床,吃早餐发呆,换衣服磨蹭,所以来迟了,对吧?”梁应情把咖啡一饮而尽,向陈长安问道。
“还有路上堵车好吗?”陈长安好看的脸有些微红。
“嗯,十点多,你和我说路上堵车,你怎么不说路上碰到钢铁侠和变形金刚跟哥斯拉和假面骑士打起来了?”
“你管我!”
真是个表里如一的家伙,何避丘看着陈长安心里这么说道。
再看向梁应情:这个和陈长安年级相仿的年轻人时不时会让人觉得他有着多面而突出的性格,总是让自己无法猜透这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即使他长着一张丢进人群里便找不到的脸。
后者的目光微微在自己的身上停顿了一下,便又若无其事地和陈长安走进了这家宠物医院。
“兄弟,进去吧,我替你在这里看着车。”戚理祥看着何避丘说道。
“不了,有梁先生跟着就够了。”
有恩必报,这是他父亲和他说过的。他知道黑马河那件事,梁应情必定替他保护过自家少爷,即使他时候只查出这件事涉及到了一些他无法得知的军事机密。所以在那之后他也和梁应情联系过,表示对方要是有什么困难,他也愿意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如果在自己未能注意到的地方,陈长安又遇到了危险,那也只能寄希望于那个时候正好在他身边的人。
“嗯,那倒也是。那小子要是有耐心和毅力去参军,应该是个不错的苗子。”戚理祥靠着自己的车,伸了个懒腰说道。
阳光正明媚,把宠物医院照的看起来温暖而有生机。
何避丘相信自己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个月光下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