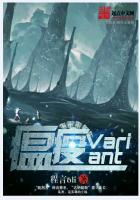春节以后,我派明烨连做了两单西药,每次都以2000万圆做本金,按照3倍加2成的价格出库,第一单就收回货款6400万圆。留下4400万圆不投入,只投入2000万圆做本金,又收回货款6400万圆。4400万圆加上6400万圆,共收回货款一亿零八百万圆。亿圆身家已经是名至实归。
晚上回家后,把存折给诗雅看了,对她说“咱俩已经是亿圆身家了”。诗雅自然是高兴了一下,她把我的存折放入了保险柜,然后说“欣实,我想过了,粮食生意比西药买卖要安全一些,咱俩的本钱上亿了,还是做个合法生意心里踏实”。我一听她挺聪明的,就说“粮食生意还不到时候,要等两年以后,现在我们每次只投2000万圆本金,既没有人身危险,也不会倾家荡产,再干两年吧”。她听了就说“只要你不去上海办业务,我就听从你的”。我说“西药生意的路子已经铺平,当然不用我亲自去办理业务,这几单生意也是明烨帮我干的,我是在汇款环节遥控着他而已”。她说“那就这样办吧”。
又过了两天,阿兰、阿婷、阿园、阿柳陆续返回。因为师生返校还要等半个月,烤亭生意也无法开张,就让她们去烤亭和舞场打扫卫生,把上学期烤亭的垃圾装桶后运出校园倒掉,那些啃剩下的骨头、碎屑,平时堆城了一个大堆,那个年代没有专职送垃圾的环卫工。整整干了三天,把舞场和烤亭周围全部打扫干净。我到供货商那里约定:3月1日准时供货。供货商在寒假时期生意不好,听说下个月来生意了,就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保证在晚上七点前送到”!他又问“曹先生,除了魷鱼、河蚌、禾花雀,还要不要些羊肉串儿”?我一听就说“当然要,批发给我多少钱”?他说“1角钱1串儿”。我说“烤熟了卖多少钱”?他说“1块钱4串儿,夜市上都是这个价”。我一听翻了番儿,就说“那就先来100串儿试试,要是好卖的话就加大进货量”。
回家后,让女佣们把各个房间的卫生打扫干净、把花园也修剪一下,然说宣布:“剩下的十几天,做饭的活儿,大家一起干,烤亭暂时不能开业。我和你们玩扑克,还是粘纸条儿”。大家听后一起笑了。
那天上午,正在和五个女佣打牌,门铃响了,阿春去开门,辛楣和鸿渐走进来,见我脸上粘着纸条儿。鸿渐就笑着说“你们挺会找乐子的,这牌是怎么玩儿的”?我把规则说了一遍,辛楣和鸿渐觉得挺新颖,就说“老曹,我和辛楣也想试试”。我说“行啊,辛楣、鸿渐和我一伙儿,阿春、阿柳、阿婷一伙儿,咱们比赛如何?輸的一方粘纸条儿”。然后就打了起,起初辛楣和鸿渐不熟,就多粘了几次纸条儿,后来就打得难解难分,诗雅也出来看热闹。这下子变得不可收拾了,一直打到中午,我叫没上场的阿兰和阿泉去做饭。我们六个继续接着打,一直打到饭菜上桌。留辛楣和鸿渐吃饭,看桌上还是老一套:四荤四素八道菜,我说“再弄个烤魷鱼和朝鲜辣白菜”。凑了十个菜,两个主人、五个女佣,加辛楣和鸿渐,九个人就吃了起来。拿一瓶剑南春,给鸿渐倒一盅后,剩下都是我和辛楣的。我这才问“找我有事儿”?鸿渐说“原来是找你出去喝酒,现在就改成了打牌加喝酒”。我说“怎么样?这种玩儿法可以吧”?鸿渐说“倒是比不上桥牌正规,但是可以在民间进行比赛”。我说“咱们三个人配合得还不算好,要比赛也得是配合默契的人组成”。辛楣问:“这种打法叫什么?总得有个名目嘛,各系组织三个人,与其它系可以比赛嘛”。我想了想说“这种玩儿法叫脸粘纸条”。大家哄地一声大笑了起来。
正说着门铃又响了,阿春开门后,高松年进来了,他笑着走来说“我是闻着香味儿找来的”。他看了看四荤四素八道菜,再加朝鲜辣白菜和烤魷鱼,就说“给我来一个油炸禾花雀”。坐下之后,我叫阿春再拿一瓶剑南春。谈起刚才的纸牌游戏,高松年问“这种玩法好玩儿吗”?辛楣说“高校长下午有课吗”?高校年摇摇头,辛楣说“吃完饭,高校长,鸿渐和我一伙儿,阿春、阿柳、阿婷一伙儿,可以在这里玩玩儿试试”。
后来,高松年打了一下午,还觉得不过瘾。就对辛楣说“你组织12个系,每系抽出3个人,各系先进行初赛,再进行复赛,决出冠亚军,校长室只有我和程玉朵两人,你做为训导长,应该算校长室的人,也参加比赛。练牌的时间,不能影响上课,不能让学生看见,到宿舍里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