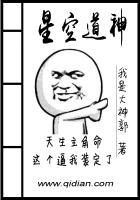陈鹤僵直的右手困在半空,许久不再发话,隔了半晌,他才从背后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丁尔拉:
“不了……刚路过你大学,门口那家鸡蛋仔居然还在,想着……你很爱吃,顺路买了送过来……我……”
“谢谢。”丁尔拉打断他的话,接过牛皮纸袋,热乎乎沉甸甸,“居然还没被我吃倒,生命力挺顽强……要进来坐坐吗?”
“不打扰你们了,我……走了。”陈鹤压低帽檐,“明天尤雾婚礼,你应该会去吧……”
“当然,我是她的伴娘,唔,千年伴娘……”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章知难笑着接过话,顺势紧紧将丁尔拉挽入怀中,丁尔拉莞尔,不再戒备,靠在他身畔。
“啊……恭喜。”陈鹤有些愕然,随即迅速接话,又挤出笑容,“恭喜,尔拉。”
“那明天见。”章知难伸出手与陈鹤告别,不由分说,关上房门。
丁尔拉与章知难站在门口,许久听电梯“叮当”一响,章知难接过她手中那包鸡蛋仔,“挺香。”
“想吃就吃。”丁尔拉有气无力,才发现自己仍挂在章知难身上,忙抽出手臂,悻悻然道,“刚才谢谢配合。”
“不亏,做你男朋友我很乐意。”
丁尔拉蜷进沙发,不再吭声,章知难系好衬衫扣子,穿上外套:
“我回家了,想必跟踪者对你无害,我也不用担心,给你的姐妹打个电话报平安,早些休息,有事随时给我电话,陪聊陪吃陪喝,免费。我的电话写在纸上,给你放这儿。”
丁尔拉盯着门口章知难消失的背影,再看看手中这包鸡蛋仔,神使鬼差拿出来咬了一口,还是记忆中的味道,简直让眼眶温热,而味道是最好的记忆引线,让丁尔拉回到少年时光,树如墨荷,光影斑驳,她与陈鹤走在长长的甬道上,还是彼此热恋无暇的时光。
没有人告诉她爱情究竟何时开始,正如没有人告诉她在那之后如何残酷结束。彼时他们都是无知又坚定的少年,熟识彼此,青梅竹马,一同小学,一同中学,丁尔拉上学的路需要走过一条极其阴暗的甬道,两壁高墙,了无人踪,陈鹤总是绕路过来陪她一起走,不论上学放学,一坚持便是近十年。
刚过除夕,那个原本属于所有人新年的第一个凌晨,在那之后,丁尔拉没再见过自己的爸爸,问妈妈也是三缄其口,家中没有任何关于爸爸的照片、物品、信件,全凭幼年些许可怜的记忆勾勒爸爸的形象,记忆中似乎是微胖不高的男人,留着平头,穿着青灰色的夹克衫,最后离家的凌晨她并没有熟睡,眼见他轻轻离开家门,不再回头。她不敢起来叫他,隐约觉得他并不想妈妈和自己知道,只好趴在窗口,在妈妈均匀悠长的呼吸中远远目送他消失在薄暮之中,心中被幼年毫无察知的疼痛击中,如刀割一般钝痛不已,只能任由眼泪滂沱。
在那之后,她已记不清家中波澜四起究竟为何种面目,一开始妈妈的惊慌失措,到后来的唉声叹气,再到后来她无故而起的暴怒与痛苦。丁尔拉不愿再多回忆,只记得众人指点耳语背后,陈鹤是唯一邀请她去家里做客的同学,他给她放爸爸昂贵的黑胶唱片,给她吃爸爸从新加坡带来的巧克力,给她看爸爸出差带回来的英文绘本书,邀请她来吃爸爸从北京带回来的烤鸭……好像她生命里父亲所不该缺席的所有喜怒哀乐,他都借由自己父亲之手完整地给了她,她打心底里感谢他,喜欢他,欣赏他,爱他。
“如果有一个人能让我如父亲一样疼她、爱她、护她,除你之外别无他人。”
在双双拿到同一个城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第二天,陈鹤站在甬道的尽头对丁尔拉表白,炎炎酷暑的正午,阳光灼烈,暑气逼人,丁尔拉来不及舔净手中已经融化得一塌糊涂的雪糕,就已被陈鹤的亲吻融化。
大学是两人最快乐的时光,丁尔拉和陈鹤的大学都在同一个大学城,隔着两条街,学校门口的鸡蛋仔摊从最开始的两人流动小摊,发展到独立的街边小铺,再发展到同时售卖港式奶茶、芋圆等港式甜品的综合小铺,鸡蛋仔的口味也从单一的原味拓展到巧克力味儿的、草莓味儿的、奶酪爆浆的……丁尔拉是常客,嘴馋得不行,但凡和陈鹤赌气了,选修课不过关被批了,大姨妈来了……鸡蛋仔便能化解一切纷争,一切愁苦,简直是丁尔拉的救命稻草,以至于大学毕业之后,老板娘也依然给俩人至尊VIP的待遇。
毕业后,两人双双借由优秀毕业生的头衔顺利找到工作,陈鹤的家人也早早在他们念大学的城市里买好婚房,一切顺利,人人艳羡,几乎让丁尔拉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女人,双方家人都已见过面,谈婚论嫁尤为自然,定好来年国庆两个孩子领证……除了自己的父亲不能亲身领略她的幸福,丁尔拉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几乎死而无憾。
究竟是什么时候一切都变了样子……哦,是的,是那件事,那件丁尔拉不敢再回忆,也不能再回忆的事……噩梦般的记忆犹如跗骨之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突兀地跳出来,撕扯她的心脏,撕碎她的魂魄……她记得《牧羊少年奇遇记》中,撒冷之王曾对牧羊少年说: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而丁尔拉无法迅即而行,也看不懂上帝给她的预示。上帝只是让陈鹤离开了她,夺走了她此生一见倾心的男人,然后让她不再相信上帝。
是陈鹤亲口对她说的再见,她早已预料但不曾想过来得那样早,但对此结果她毫无怨言,除了颔首接受,她完全没有想过反抗或者争取,因为她深知毫无意义。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她放弃了他。
丁尔拉头痛欲裂,她放下手中已经凉透的鸡蛋仔,扔进垃圾桶。奇怪,回忆如此汹涌惨痛,却毫无泪意,除了心中残存的一些痛楚,她居然能置身度外将所有情绪抽丝剥茧,一一理顺整齐。丁尔拉耸耸肩,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记忆是一池春水,无人随意轻扰,便不会产生任何涟漪。
不知为何,沉重的睡意顿时袭来,丁尔拉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卧室,一头栽进床铺,周围尽然充斥着湿润厚重的寂静,邻居抬动桌椅的声音隐约传来,窸窸窣窣和窗外的雨丝融为同一种声响。大脑一片空白,丁尔拉和每一个独自睡去的夜晚一样,将身体深深陷进深蓝色床单,深蓝色被褥,意识犹如探入陌生海域的水母,水路相继关上通往意识的出口,很快,她便浸身于深蓝色的沉睡中。
时间沉入世界尽头,凌晨五点,似乎下起大雨,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窗户,清醒倏然而至,与其说是生物钟自动唤醒,不如说丁尔拉本身即是一个钟表更为妥帖,时间到点,身体里的拨片轰然开启,急遽颤动,将五脏六腑搅动开来,简直如条件反射一般。
丁尔拉猛然起身,拉开窗帘,奇怪,没有大雨,却是阳光灿烂,她脱掉衣服,用热水仔仔细细清洗干净身体每一个角落,肌肉的形态与线条优美流畅,结实有力。她需要神清气爽的开启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大日子,是她十二年的闺中好友尤雾的婚礼。
丁尔拉简单收拾好物品,准备出门,却发现门外挂着一个手提袋,她诧异地打开袋子,愕然发现自己昨晚给章知难止血的围巾已被清洗干净,整齐折叠置于其中,还附带了一条章知难手写的字条:
“知你清俭由人,这是你唯一或最爱的围巾,今日气温冰点,遂连夜洗净烘干。另,谢谢为我止血包扎。
住在你楼上的男朋友:章。
即日。”
丁尔拉忍不住笑出声来,将围巾坦然绕在脖子上,好闻的不知名的清香钻入鼻腔,沁人心脾,丁尔拉陶醉地埋在柔软围巾中,不知不觉已经下到一楼,推开门,气温并不如她想象中寒冷,淡淡的红日斜倚在天边,温和得好似回家后刚熬好的一碗赤豆汤,世界一片金色温暖,云朵细碎可爱,仿佛美人鱼的鳞片一般贴满天空。
唔,是个结婚的好日子。丁尔拉这么想着,愉快地向酒店方向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