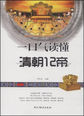这一定是徐阶在考察我的应对能力,我思忖片刻,道:“目前最关键的是,凡事都要顺从圣上、迎合圣上,让圣上感到失去严阁老,他并没有损失什么。至于高中玄所谓拨乱反正,学生以为,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须臾,又补充说,“还有,要和科道商榷,让彼等莫再参揭严氏父子,在圣上面前也不提及严氏父子的话题,就仿佛那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徐阶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才露出了笑容,说:“叔大非高新郑可比也!”旋即,又恢复了凝重,嘱咐说,“近期少与人交通,不到不得已,也不要直接来见我。”
或许,不明内情的人会觉得严嵩的倒台,远远没有人们所盼望的那样带来喜庆气氛;稍微知道些内情的人,则隐隐感到,近日的京城官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这天,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我刚要走出朝房,国子监教授耿定向急匆匆闯了进来,一边抹着额上的汗珠,一边焦急地说:“太岳兄,这事怪啊!何先生不是不守诺言的人呀?”
“楚侗!”我以责备的口气说,“何事如此张皇?”
“事先预订好的,今日午后由何先生讲学,可是自清早就不见了他和夫人的影子,四下找了整整一天,就是找不见人影。”耿定向不解地说。
何心隐突然销声匿迹了?凭直觉,我感到何心隐已经离开了北京,而这其中,必有隐情。打发走耿定向,我径直赶往徐阶的直庐。我知道,徐阶最近一直在直庐过夜,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
前两天,圣上突然下了一道御旨:“今严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邹应龙俱斩!”看到这道御旨的人,无不被惊得目瞪口呆。谁也不会想到,圣上竟然说出了这样杀气腾腾蛮不讲理的狠话!邹应龙乃是弹劾严世蕃,促成严嵩父子倒台的功臣,已晋升为通政司参议,任命诏书刚刚颁下,墨迹未干,转眼间,在圣上眼里,邹应龙竟成了该杀的罪人!看到这道御旨的邹应龙,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也未敢前去通政司履任。
走进直庐,徐阶正伏案疾书,我轻轻唤了一声:“师相——”
徐阶抬起头,看着我,责备说:“叔大,嘱咐过你的嘛!”
“师相,”我焦急地说,“何心隐失踪了!想必是听到什么风声,悄然出京了。学生觉得可能要出事,所以……”
徐阶没有回应,从表情上看,徐阶似乎并没有像我听到这个讯息那样感到惊讶。
我不便再说下去,走不是,留不是,左右为难,索性就又问:“师相,圣上何以颁发‘同邹应龙俱斩’这等令人匪夷所思的御旨呢?”
“以叔大之见呢?”徐阶问。
“这或许表明了圣上的心虚!”我说出了几天来苦思冥想的结论,“群臣诟病严嵩的所有罪孽,不是禀承圣上的旨意,至少也是得到过他的首肯的,倘若任由臣僚揭发严嵩父子,势必触及皇威,至少会引发对圣上德行有亏的联想。”
徐阶凄然一笑:“叔大果然有非凡的洞察力,此非一般人所能测见。然则,拔擢邹应龙的诏书毕竟刚刚颁下,如此前后失顾,必然另有隐情。”
“隐情?”我的神经绷紧了,“会是甚样隐情?”
徐阶叹了口气,说:“当然时下已不再是隐情了。本来不想告诉你,蓝道行入狱矣!”说着,他轻轻拍了拍几案上的纸笺,“老夫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写几句话,留待将来。你快走,这几天万万不可再来,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
“师相!“我顿时紧张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好,既然已经来了,不妨让你略知其事,”徐阶说,“今日一早,圣上突然召我入对,问我蓝道行伪造上天乩语,该如何处置?”
“啊——”我禁不住叫了一声,几个月都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怎么会突然事发了呢?
徐阶沉吟道:“我当时也是大吃一惊。但事到临头,是来不得半点惊慌的。我知道,这一定是圣上在试探我,所以,我平静答道,能替神说话的人,并不是神本身。圣上对我的回答似乎还算满意,口谕锦衣卫立即逮问。揭发蓝道行之阴事,显然不是彼辈之目的,目的是要追查幕后主使者。只要蓝道行供出背后有人指使,这个人,只能是我徐某,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我刚要说话,徐阶制止说:“叔大不必再说,对你来说,一切都没有发生,一切都毫无所知。静观其变。”
蓝道行扶乩之事,怎么在这个时候突然被揭发了呢?出了徐府,我脑海里一直在思考这个关节,百思不得其解。看来,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严嵩一方在采取行动了。一瞬间,我把当时全部的经过又仔仔细细过了一遍,我并没有和蓝道行直接交通过,他不会供出我来。但蓝道行显然是和何心隐合谋,受何心隐指使而行事的,而我正是何心隐选来作为内应的。这些,徐阶能够替我承担得了吗?
难道,第一次涉足官场的是非之中,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前程乃至身家性命断送了吗?我感到有些后怕。
事到如今,后悔是没有用的。既然已经陷进去,就索性一搏!看这局势,似乎正在发生逆转,眼看徐阶就要转入了守势。按徐阶的主张,是要我以静制动。但总不能无所作为、坐以待毙吧?万万不行!想到这里,我转身又回到了徐阶的直庐。
“叔大,怎么又回来了?”徐阶吃惊地问。
“师相,学生以为,该派人到江西去,掌握严氏动向。”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既然严氏父子在反扑,则不能不掌握严氏行迹。一来知己知彼,便于因应,以免措手不及;二来若严氏及其党徒兴风作浪,有不法情事,可适时报于圣上。”
“叔大言之有理,”徐阶满意地点着头,“不过以何名目呢?又派何人前往呢?”
我已经想好了,于是很是自信地说:“学生以为,圣上笃信道玄,蓝道行下狱,圣上身边再也没有高深道士可用,就以访仙御史的名义,派往江西,名义上为圣上寻访道仙和符笈秘术,实则监视严氏行迹。”
“访仙御史?”徐阶似乎犹豫不决,我猜想他是怕出此名目,会被舆论所诟病。
“师相,当此紧要关头,不可犹豫啊!”我劝说道,“只要圣上高兴的事,就得不计毁誉去做,况此举虽有揣摩迎合之名,实则乃是为挽狂澜于即倒,拔除大奸,拨乱反正,请师相断然采行。”
“可是,能当此任者,恐不易物色。”徐阶接受了我的建言,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御史李幼滋可当此任。”李幼滋是在不久前转任都察院监察御史的。以我对他的了解,是可以托付的。但说出了李幼滋的名字,我又觉得还是不踏实。仅凭一个李幼滋,势单力薄,人地两疏,要完成肩负的使命,恐勉为其难。我突然想到殷正茂正好辉县知县任满,当下就在京师候补,何不派他去袁州任推官。推官虽然品位不高,但正是负责治安、司法,可以巡视所辖各县,对掌握分宜县严府的动向,就相当便利了。殷正茂是进士及第后直接分发到地方任知县的,所以虽然是我的同年,但与徐阶却毫无渊源,想来不会引起关注。以徐阶在朝中的威望,推荐一个知府衙门的佐贰官,在吏部那里,不会遇到什么障碍的。关键是殷正茂是否会接受。毕竟,推官只是知府在司法方面的助手,殷正茂很可能会感到委屈。但我有信心说服他接受,以殷正茂的性格,他最愿意做具有挑战性的事,而到袁州去,他所肩负的使命,本身就是一个严峻挑战。
“如此甚好。”徐阶满意地说。从他的神态、眼神可以看出,徐阶不仅对我的一番部署,更是对我所表现出的从容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