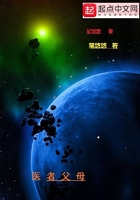那是一个空气里飘着柠檬甜涩的清晨。
可我的心情却只有苦涩没有甜,2019年的尾巴,马上就要迎来我33岁的生日。手机里传来的滴滴声全是花呗的还款信息和合租室友的催缴单子。我的银行卡窘迫得像只不能下蛋的母鸡,在被主人扔进锅里之前做着最后的挣扎和求饶。
报社的效益越来越差,工资单薄的如同人到中年的头发,风一过便落一把。纸媒的没落已成必然,我不能抱着一根笔杆子死磕到底,一个月前便提了离职,而今天也是我为晚报做的最后一个采访任务。采访的地点不是我选的,应对方要求选在四环上一家新营业的西餐店里。
外面的雪越来越大,我早早穿了黄色的棉鞋,提起我厚厚的棉服,不,是战甲,去地铁里抢占一席之地。无声的雪花也遮掩不住城市的喧闹。一路拥挤一程嘈杂,终于是到了。我坐在餐厅里不断刷着各种求职信息,四个月了,我投出去的简历大半都石沉大海,偶有询问,也都不见下文。魔都啊魔都,多少名校出身的人才,前仆后继;多少青春朝气的人才,一茬又一茬。与我这学历平平,相貌平平,才能平平的中年人来说,放眼望去,只有八个大字:来路已死,去路尚无。
我把所有的招聘网站看了又看,不断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村上春树33岁开始写作,耶稣33岁钉上十字架……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我还能拼,我还能拼。“嘟”的一声,花呗的催款消息此起彼伏,所有的心理建设全部崩盘,我沮丧地看着周围来往的人,串串眼泪浸湿了采访大纲。阳光刺眼透过餐厅的薄纱,采访大纲下面是我前一天刚取的车票,我正站在迷茫的十字路口,不知是倔强向前还是打包回家,我是懦弱的也是动摇的,缴械投降是我一贯的处事原则,所以人到中年才这般狼狈和潦倒。眼睛哭红红,鼻头酸涩涩,嘴巴苦丢丢,我仿佛成了静止符,孤独地定格在偌大的魔都里,无人同行也无人指路。
“你好,是木记者吗?”淼鑫花卉的钻石王老五陈傲礼貌地向我伸手示意。他就是我今天的采访对象,年轻有为的陈先生和自己的哥哥陈诚在魔都开拓了自己的事业版图,我望着这个20多岁年纪轻轻的执行董事,快速地整理好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作为记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也是我多年职场修炼的本领。“木记者,这次是想让贵报社根据我们企业的成长史作一篇品牌报道。今天下雪不好走,辛苦你了。”我连忙摇头说是自己应该做的,简单寒暄后,我的采访大纲还没翻开,隔壁桌几个家长带来的孩子却捣蛋起来,把桌子涂上厚厚的奶油蛋糕,又将椅子上的把手黏上果酱,一时间,孩子的叫喊声和家长的责骂声交在一起,屋子里面乱成一团。
我的采访声音根本架不住这满屋的嘈杂,忍不住提高嗓门抱怨:“只有小孩子才会这么吵,大人就安静多了。陈董,要不要换个地方。”
他摸了摸袖口的金色纽扣,若有所思地沉沉一笑:“木记者,你相信吗?我见过比小孩子还闹腾的大人。”“什么?我听不清。”孩子们越发活跃了。被家长追的满屋子乱跑。“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听听我的故事,听听我故事里那个比孩子还要闹腾的人。”我看见陈先生张嘴说着什么,因为听不清,就顺着他的微笑点了点头。几个服务员走了过来,配合着家长把熊孩子们归拢到一边,店里又恢复了安静。陈先生端起咖啡沉思很久,然后就着杯子里升起的腾腾白气。向我敞开了他记忆的大门。我抬了一下手,看见手表上的时针刚好指向9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