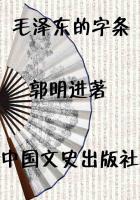普拉提走进办公室刚坐下,有人敲门,未等他说话门已开了,进来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普拉提出于礼貌和她问了好,并请她坐下,但他一时还想不起这位年轻女子是谁。
年轻女子娇里娇气地说:
“普拉提大哥,我上个月给您的诗歌集,您看完了吗?”普拉提这才想起她是谁了,他轻轻地拍了拍脑门,连声说:
“抱歉。你不说,我还真没有认出来。”
“哎呀,普拉提大哥,您的忘性很大吗,这么几天就不认识我了?我长的就那么没有特点吗?”年轻女子又娇里娇气地说。
“我最近实在太忙,没有来得及看呢。等忙过这几天,我一定抓紧时间看。”说完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些材料翻看,不再理会她。
年轻女子趁他不注意,从包里拿出小镜子照了一下,用手整了整有些凌乱的头发,用舌头舔舔嘴唇,之后又解开大衣的扣子,有意露出被鲜红色毛衣紧紧裹着的高耸的乳房,她有意挺直腰端坐着,眼睛一眨一眨的,涂了厚厚一层睫毛膏的睫毛忽闪忽闪的,极具诱惑力。她问道:
“普拉提大哥,那我什么时候再来?”
“过三四天吧。不,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您的手机号是?”年轻女子赶紧从包里取一个名片双手递给他。普拉提接名片的同时,得以近距离看到她的脸,他暗想:“怪不得她写的东西深度不够,原来她的功夫都下在自己的脸上了。”
总算送走了这位难以对付的小姐。普拉提拿出几篇稿子开始从第一篇看起,可是看了一会儿,他就看不下去了。他想起父亲交代的事儿。他必须去医院一趟,母亲的事儿不管输赢都得有个结果。他将稿子收起来,拿起皮包出了办公室的门。
他走到达瓦医院的大门口时,时间已是11点10分了。就是说,离下班时间还有五十分钟了。他小跑着到了院长办公室门前,门虚掩着,他没有直接往里闯,先是敲了敲门,那声音极小,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母亲一个健康的大活人死在这个医院里,作为死者亲属,他来这里讲理,要求解决问题,本应是理直气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来到这里时,他都有些胆怯。尤其见到医院的领导时,心里总是慌得不得了。此刻,他虽然敲响了院长的门,但又有些怕见到院长。
他敲过门后,里面并没有反应。他又敲了几下,仍然没有人答应。他推开门一看,里面并没有人。门没有锁,证明人没有走远。他在沙发上坐下,等着院长回来。
大约等了半个小时,院长兴致勃勃地回来了,一推门,见到坐在沙发上的普拉提,院长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普拉提赶紧从沙发上起来迎着他,并向他伸出手去想握个手,可是院长大人却假装没有注意普拉提伸手的动作,边往自己的办公桌走,边对普拉提说:
“你坐,你坐。”他坐在办公桌后的转椅上,打着官腔说:“你们老说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你们的母亲讨个说法。可是,咱们是法制国家,干什么都要依法,要讲证据,不可感情用事。”说着他用胖胖的短手捋了捋稀少的头发。之后,又从衣服里掏出小梳子一遍一遍地梳起头发来。他此刻的样子与以往谦恭有礼的表现成了鲜明对比。看到他的这个变化,普拉提的心凉了半截,他预感到事情不妙。他正在想着应该如何和这位突然之间变得傲慢的院长理论时,院长又说话了:
“尽管你们一直都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与我们交涉,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了一回事儿。因为,让患者满意是我们始终的追求,我们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调查组已经写出调查报告,报到院党组了。调查结果表明,我们的医护人员在给你母亲做手术时,没有违反规定和医学行为。你母亲的死亡是一起意外事故。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说这个事儿了,我们也忙。”说完院长看看手表,把桌子上的一个笔记本锁进抽屉里,拎起皮包站起来。看来他是要下班了。普拉提不甘心就这么走,他站起身说:“院长,我能不能看一下那个调查报告?”
“不行,这是我们的内部文件,不能让外人看,可是报告的内容我不是已经对你说了吗?你还是走吧,不要再来了。”普拉提从小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从大学出来后就进了出版社工作,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他所接触的人也都是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他长这么大,还没有跟什么人大声地争吵过。尽管他觉得应该和这个院长大声地争一争,可是,他依旧没能鼓起这个勇气。
“院长,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完了,我母亲不能就这么死了,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也是有母亲的人……”普拉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种没有任何力度又毫无条理的话。院长径直走出了办公室的门,普拉提也只好出来,看着院长锁了门。他站在院长旁边没有动,等着院长对自己的话作出反应。可是,院长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普拉提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他的脑子里变得一片空白,一刹那间,他甚至忘了自己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鼻子一阵发酸,委屈的泪水涌满眼眶。他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好像这么做可以将泪水也一起咽下去。他沿着过道慢慢地走着,想着刚才院长说的每一句话,很显然,再找这位院长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怎么办?难道就此罢手?母亲含冤而死,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为她讨个公道都做不到,我们就那么无能吗?”普拉提想到这些感到痛苦万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医院的行政大楼,迎面走过来两个护士小姐,手里端着饭,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事,他只听到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行了,你也不要可怜她了,她可能命该如此。”另一个并不同意,她尖声尖气地说:“什么命呀,我才不相信什么命呢。这个帕提曼也是的,医生说了那个病人是心脏病死的,她一个小小的护士懂什么呀,敢对医生的结论说三道四的,她得到这个下场也是自己活该。”另一个护士说:“听说那个死者的亲属一直都在找院里理论……”两个护士说着话绕过行政楼前的花园进了外科楼,后面的话普拉提没有听到。但是,从她们的对话中可以听出,她们是在讲一个医疗事故。这个事儿怎么像是在说母亲的事儿啊?莫非是真的?普拉提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他飞速地跑进外科大楼,可是那两个护士小姐已不见踪影。他沮丧地走出外科楼。但是,那两个护士小姐的对话给了他启发。他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道:“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手术那天在场的人员。原来我们只顾和那个主刀的医生吵,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决定我母亲的生死,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实情似的。他的那些助手呢?噢,对了,动手术不是还有麻醉师吗?我们真笨!”他又一次朝自己的脑袋上重重地打了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