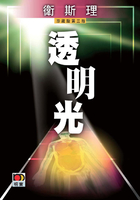教堂后面较小的帐篷是指挥官的,我说,帐篷,我对你说,较大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狙击手的。我们大约有八人。一半人上岗的时候,另一半人就在营地睡觉。然而,你永远都不知道上尉究竟是在他的帐篷里还是在战壕里。你以为他最不可能出现的时候,就会被他一脚踹在靴子上,我说,靴子,我对你说,你还没回过神来他就已经站在你后面,也许他已经在你后面站了很久,离你很近,看着你每个动作,以及你在枪林弹雨中的表现。他寻找着恐惧的征兆,对每一名狙击手来说都是最要不得的,但过分勇敢却更糟。
“一名狙击手,”他说,“必须要耐心,镇定,清楚地知道实际上他自己也是有肉体的,即使也许没有人看得见它。离敌人很远,不代表离死亡很远。每一具肉体都携带着自己的死亡,”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肉体,就连神也有,这样他才了解死亡;如果他没有肉体,他就不会了解死亡,如果没有死亡那就没什么仗好打了。所以,让我说得再清楚点:人就是一根普通的黄瓜,知道自己是要死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负起责任,像人一样睿智地活到死去。”这是每天早上热头鹰在我们去战壕之前都要对我们说的话。他从来不会忘记提起黄瓜,我说,黄瓜,我对你说,每次他说到黄瓜我都会想起高中时他咬校长耳朵这件事。
他总是在日出之前剃须,面前摊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卡在梨树枝之间,关于德克雷申佐哲学的一些历史,我想。我认为他那些高深的想法就是从这里学来,并据为己有,而我总是因此苦苦思索却从未真正理解。昨天我终于问他为什么说神有肉体,因为我们都清楚神是没有肉体的,但他只是挥了挥手把我赶走,然后爬到钟楼上去了,去看河对岸发生了什么。他下来的时候,就拉着我的胳膊带着我一起走进了战壕。
“神是如何创造出人的,我所谓的将军,”他说,“如果他不知道人长什么样。提醒你,在一开始,只有他,所以他只可能知道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模样。”他说得没错,然后就去没几天前普里克·约翰逊分到的岗位,就是那个他擅自离开去“光毛小公鸡”的岗位。当然,此刻的热头鹰已经剃干净自己的胡须,手里拿着枪走了过去,如果他反抗就杀了他。我们在墙边排好队,左看右看,但我们的眼睛最终总会回到他身上。只有普里克·约翰逊,就是那个很多年前,当我们仍出神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进来告诉我们爱玛·包法利的故事已经结束了的人,一个人站在旁边,靠近祭坛。热头鹰上尉突然停下了,好像喉咙里卡了一根头发一样吐了口唾沫,并且在我们面前踱步,只是盯着他,盯着约翰逊。偶尔他也会被草丛中躺着的十字架绊一跤,我说,搞得他不得不抓住最近的东西,免得摔倒,他诅咒着所有那些决定在他的路上享受永生的逝者。他因为他们挡了他的路还云淡风轻不帮他一把而愤怒不已。从头到尾他的枪都指着约翰逊,他跳上了一座大理石坟墓,也就比草高一点点,提了提他的裤子,膝盖上下动了两下好让裤子不要粘在汗湿的腿上,他在等着一颗流浪的弹壳在西瓜地里爆炸,只有坟地后面的田里才种满了早熟的西瓜,我说,爆炸,我对你说,把西瓜子炸得四处横飞。“如果他还是一个人,现在应该已经自尽了。”他说。“出于爱国之心。”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枪指着普里克·约翰逊,此人正蹦蹦跳跳好像急着上厕所的样子,为了不让裤子掉落用两根手指抓着皮带圈。“我给了他那把‘精密’,该死的,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步枪,由芬兰制造商拉普阿制造,美国海军陆战队研发。这是唯一一把。”他说。“军团唯一的一把。”他对我们说。“它射出的银色子弹紧贴着枪管,一点声音也没。它可以消灭远在一千三百米之外穿着四级防弹背心的敌人,看在上帝的分上!一枚子弹,该死的,与我们一千个人等价。这个人,如果他还是人的话——站住,你这根该死的黄瓜——被分配到我们的主要目标,要杀掉极其重要的人。三天前我命令他紧盯着对面,消灭他们的首领,那个缺了一条手臂的人,该死的,那个长着大胡子,胡子上给眼睛留了两个洞的人。你能相信吗,该死的,这个普里克站在这儿,把狙击步枪朝壕沟里一放——站住,你这根该死的黄瓜——那把无价的狙击步枪,该死的,为了一品脱啤酒去了‘光毛小公鸡’!”
“葡萄酒。”仍然醉醺醺的普里克·约翰逊咕哝着,刺激得热头鹰从坟墓上跳起来,近距离瞄准他。这位战士在蓟丛中吧嗒吧嗒跳得越发快了,蹦蹦跳跳好像在跳吉格舞一般,而上尉抡着枪追在他后面,像是在挥舞指挥棒。
我差点笑出声来,朵兰缇娜,差点咯咯地笑。
“他,在‘光毛小公鸡’的时候,我们的敌人们已经捅上了我们的‘光毛屁股’!”鹰咆哮道。“三个大胡子都已经到了桥中央;他们让一头驴子拉着一车甘草走在前面。我的副手,回声·响嘴,”他说,“响嘴,”他对我们说,“及时用火箭筒射那驴车,驴车像军火库般一直炸到高空。甚至还有几门彩色的火箭炮,名副其实的烟火。从远处看还挺漂亮的,该死。但是,那爆炸本应该发生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岗哨中,在我们的队伍中。如果真让他们得逞,我们已经变成一堆肉糜,等着给人讲故事了。然而,感谢我的副手回声·响嘴,虽然他不在我也要表彰他,那驴车唯一剩下的就是驴蹄了。我为那些驴子难过,但我可不为你难过,你这该死的蠢黄瓜!”热头鹰大叫,握着枪,他攻击普里克·约翰逊,又开始在草丛中走了起来,用闲着的那只手劈开空气,屁股在十字架之间扭动,好像滑雪一样。往回转身的时候,他被一颗隐蔽的、顶上有褪色红星的石头绊了一跤,失去了平衡,在他倒入草地的过程中,他的枪突然走火射出一枚子弹。与此同时普里克·约翰逊也往后倒入草丛中,两条腿乱蹬,像是肚皮朝上的龟,我说,龟,我对你说。手抓着草,他一路爬到了教堂的墙边,突然他两腿一伸,软了下来不动了。等热头鹰两脚着地,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仍处于震惊之中,没手没嘴,就像坟地中半身像的半成品。几秒之后,普里克慢慢站起身;他靠在祭坛上,眨眨眼,像刚刚睡醒,他捏捏鼻子,哼了哼,终于发现自己还活着。上尉发出脱臼般的咔咔声,又像哭又像笑,同时给枪里的子弹退膛。在南方某处,我说,从桥沿着溪流往南,我说,左岸的某处,在高程点106,机关枪也咔咔作响,中间有几次间歇,好像是要解决问题,你能听到狙击手发出砰一声闷响。当鹰把那些弹壳扔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空弹,头都是坏的,没有火药。他这么干已经是第二次了,可还是没有人能确定他枪里装着什么样的弹药。他开始在我们面前上膛,这次用的是真子弹,接着他气愤地给普里克·约翰逊配备了一把新的狙击步枪。“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这该死的蠢黄瓜。”他吠叫着,并且亲自护送他到钟塔塔尖。不幸的是,他一上岗,两眼之间就嵌入了一枚子弹。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在无名英雄纪念碑旁挖了个墓,因为这是唯一一个不会被草遮住的坟墓,如果将来有人想要找到他给他收尸比较方便。我怀疑是否会有人来找他;好几年来约翰逊家没有一个人从辛普森沙漠回来过;他们都隐姓埋名住在赤道以南,印度洋之外,靠近麦克唐奈山脉山脚下的爱丽丝泉;他是唯一一个因为爱国而留在祖国的人;他只喝国产葡萄酒,唱民歌,那些悲剧英雄史诗编成的歌曲。他是个爱国志士,朵兰缇娜。就连他的葬礼都充满了爱国主义:
“汝等爱国志士约翰逊!我们都有肉体;因此神也拥有肉体。死亡是神圣的,该死。我想说的是,坟地,就像妓院,当然,适合每一个人。妓院向所有人敞开,就像坟地也向所有人敞开。昨晚你碰巧出现在‘光毛小公鸡’,现在你又碰巧出现在这里。生命与死亡是一体的,就是同样的玩意儿。你只需要知道怎么玩就行。你,真正的爱国志士约翰逊,不为生死而羞耻,但是,很明显,你也不为死亡感到羞耻。你这根该死的爱国黄瓜;你,普里克,约翰逊[1],不为任何事而感到羞耻,这就让你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愿你安息,即使我知道这个地球根本不平安。”于是热头鹰结束了他的演讲,降下了我们之前碰巧在草丛里发现的国旗,扔了几块土到敞开的坟墓里。小号手奥托·叽叽迅速地吹出一段充满爱国主义的调调,接着我们在十字架上用潮湿的火药写道:“国家志士约翰逊。”每个人都只知道他叫约翰逊,虽然实际上他的真姓是碎蛋人。
当晚,朵兰缇娜,你们的人展开了进攻;你们试着攻下那座桥,占领坟地,好在之后从那里进军田地。我推测你们的计划应该是向前推进,建立一条与大胡子出没的北线平行的分界线。第一波猛攻是由那些最勇敢的人发起的,随后都被歼灭,但是紧随其后的就是那些不那么勇敢,但也欲火焚身想要白白送死的人。我确定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直接上天堂,你知道,那有河,有酒,有美丽少女。在普里克·约翰逊死后,热头鹰把我分到钟楼顶上,从那里,我可以看见他们如浪涛般扑来,像黑蚁,跳上那些死去、受伤、倒地的同胞们,我说,蚂蚁,我对你说,然后继续向前冲。你看不到他们队伍的尽头,真的。好像某个疯狂的神祇坐在山后某处,持续不断地用泥土把他们制造出来:芝麻—泥土—开门—人,冲出去再死一次,他似乎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究竟有多少他们这样的人,我说,那么多,我对你说,像是复印机里搅和出来的。透过我的瞄准镜,透过我的夜视镜,我看见最小的那些也是最有恒心的;那些穿着黑色衬衫的大胡子,胡子中有两个为眼睛预留的洞。他们的眉毛上方绑着刻着黑字的头巾;这些字母像一串蚂蚱一样排在一起。他们会爬下河,我说,河,用牙齿咬住飞来的子弹。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还挺高兴去死,因为我们的前线自卫队一看到他们出现在河岸上就会立马把他们收割,我说,河岸,到达水库之前,很明显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那里。但是,他们刚开始蹒跚,新的头颅又在他们旁边冒出来,好像是从他们的胸口兀自长出来的,芝麻—泥土—开门—人,冲出去再死一次!在黎明之前,我们的Mi-24绞肉机必须出动;那景象可怖,名副其实的屠杀。我从钟塔上往下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留着大胡子的男孩把自己抛到我们的绞肉机下,用自己的AK-47向它射击,就是为了等下一台绞肉机将他们炸成碎片,像碎西瓜一样喷洒在空气里。红色的月光四处散落;血红的空气四处喷洒,朵兰缇娜。一个光点会突然在周围的空间闪烁,于是左岸的夜空就会被点亮,像是新年的烟火。谁知道昨晚死了多少人,朵兰缇娜。就连那些飞来藏身在钟楼里的鸟儿都散发着血腥味;燕子挤在钟塔屋檐下的鸟巢中,翅膀在滴血。
到了黎明,连一枚子弹都没有从我的狙击步枪射出,从这把黑箭之中。然而,在太阳跳上教堂的那一分钟内,就在那里,你身后,在堡垒的东墙旁,我发现一个穿着和你一样的卡其衬衫的男孩。他的狙击步枪仍然架着,朝向钟塔,而他在仔细地梳着头发。我发现那就是他们射杀普里克·约翰逊的狙击点;我把眼睛压到激光瞄准镜上,在他的额头上作了记号;他一只手拿着黑色的贝雷帽,另一只手梳着头。在扣下扳机之前,我看见他左边的口袋上绣着某种黑鸟状的徽章;所以我就向它的双翅之间射击。男孩还没来得及放下握着梳子的手;他死前无须道别,无须恐惧,因为不知者无畏。想象一下,朵兰缇娜,我到这儿之后第一次,第一次,我发誓,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感到一阵释怀;第一次,复仇赠与我喜悦。实际上,我曾有过相同的感觉,当时,四年之后,我终于发现我的短篇登上学生报纸,就是那个第一次去见男孩父母时在火车车厢里被坦克火炮筒撞死的女人的故事。我胃里某种芬芳的东西融化了,我说,我胃里,我对你说,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其中用它的翅膀爱抚我。这种成功是否可能是复仇的一种呢,朵兰缇娜?一种深埋的复仇,朵兰缇娜,我心中的河?那这种披着成功外衣的复仇又是指向谁的呢?我不知道答案,当然。之后,我只能透过瞄准镜看着,我说,瞄准镜,我对你说,看你是否能打败一整支军队,无论是谁,有多少人在帮你;看你是否能攻占左岸供给半座城市的那些水库。新的雇佣兵不断从山上蜂拥而下,一群一群,胡子挤胡子,我说,胡子挤胡子,我对你说,偷偷摸摸想要过河,好冲破那些围墙,占领那些水库。他们在北方前线已经成功了;十万居民已经断水一百天,现在仍在继续,朵兰缇娜。这是热头鹰说的,也只有他知道这些了。我想要说的是,当第一波进攻者被收割,将要落入水库周围的防卫壕沟,新一波人就会跪倒,在他们身后的影子里弯腰。他们一结束祷告,就会起身猛冲迎向那些向他们飞来的神圣子弹;有的人甚至在倒下之前能用胸口接住好几颗子弹。当黑暗快要降临,我们的苏霍伊战斗机必须介入,我说,我们的苏-25,我对你说,人称“蛙足”,和美国的A-10相似,“雷电”。那些能逃过战斗机低空扫射的,不知怎的竟能退到村子里去,假装被当局骚扰的村民。“他们知道自己雇来的妓女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哪等着,”鹰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像蚂蚁一样把死人拖在身后,拖到那里,给他们穿上百姓的衣服。”我也能看见那些死人慢慢爬上堡垒上方的山坡,只为隔天能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隔天晚上,我在桥旁的位置,就是那个普里克·约翰逊留下他的狙击步枪,去“光毛小公鸡”酒吧的位置。主战壕就是从教堂开始,到这里结束,朵兰缇娜。其他分支连接了整片河岸,从水库到教堂,再从教堂到山谷的最高点,那是我现在的位置。天黑之前下了几次雨;一阵倾盆大雨之后就停了,只为了紧随其后两度卷土重来,从天上倾注而下之后才彻底停了。大约在午夜时分,战斗停止,整个夜晚一片死寂,十分应景。月亮就像黄色的碎瓷片挂在河上。我们三人在壕沟里,静默地坐着。上尉禁止任何谈话或动作,因为月亮正毫无遮拦地照在我们这一边,更不用提那死寂,让每一丝声音都在堡垒的墙壁间回荡。为了不让我们无聊地玩手指,热头鹰想出一个好玩的游戏:我们把一片片锡箔纸绑在灌木丛里,让它们沿着河岸闪烁微光。你们有些稍稍经验不足的战士毫无疑问会以为自己发现了我们的位置,因为它们在风中摇曳,月亮一照到它们便会反光。他们一定以为这是刀枪的反光,总而言之,彻底将他们戏耍一通,你们那些做记号的人则会对着那些诱饵开枪,暴露自己的狙击点。没几分钟,我们就消灭了三个。接着我们又沉寂下来,朵兰缇娜,因为我们不知道热头鹰去哪了;他可能远在天边,我们对对方说,但他也可能近在咫尺,甚至在我们背后,我们脑海的后方是这么想的。他在壕沟里潜行,犹如影子,你永远不能确定你看见的是影子还是他的真身。
大约午夜时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说,记得,我对你说,天空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给自己披上了雨披,但却饥肠辘辘,我肠子咆哮的声音,远在河对岸清真寺的他们一定也能听得一清二楚。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装面包的包,找到了午餐时剩下的一条。虽然它已经有点湿乎乎,我说,湿乎乎,我对你说,我窝在雨披里吃了起来。等我咬了几口之后,壕沟转角后方,离我不远的地方,另外一枚弹壳落了下来。我把面包收回包里,蹲在防御土墙后面,在那个凹槽里,我将自己隐蔽起来,等着另一道光从河对面,从你的那一边,从你的战壕里,射向我这边。我等着,但是那光并没有来,在破晓时分,朵兰缇娜,我看见我的旁边,那个代替普里克·约翰逊的男孩靠在战壕的土壁上,好像在酣睡。那血液汇成一条小溪流了过来;我打开包,我说,我的包,我对你说,却发现我刚还在吃的面包现在已经彻底成了红色,像海绵一样渗着鲜血。我用手把它拿起来,血开始滴落,我说,血,我对你说;就在那一刻,我只感觉天旋地转,肠胃也翻江倒海,我发誓就连我的灵魂都开始散发那男孩的气味。我用后脑勺叩击战壕湿漉漉的土壁,我说,战壕,我对你说,狠狠咬着自己的手,好防止自己叫起来,被热头鹰听见。我哭着哭着就吐了,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接着又哭,哭完了又继续翻江倒海地吐,整个过程中面包不断滴着血,我感到内脏剧烈翻腾着,都涌到我的喉咙口了,将我体内的一切都撕烂煮沸。我一直握着这血淋淋的面包,好像在握着男孩的心脏,他仿佛看着我,难以置信:难以置信我竟然吃了这块面包,或者难以置信他已经死了,朵兰缇娜?我不知道。
那天热头鹰把我拉出那个岗位,又把我带回钟塔。战壕将整片河岸切割成迷宫,没人知道等这一切结束之后这迷宫还有什么用。我们穿过战壕的时候,上尉对我说了些关于勇士和懦夫的话;但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那段关于小鱼和大鱼的。实际上,他是这么说的,大鱼总是形单影只,而小鱼总是成群结队;大鱼的生命是伟大的;而小鱼的生命是渺小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我说,他安排我回上面去,空中,在那里我就是一个人,与一切分离,当然也包括只有在地上才能流淌的血液。“壕沟里总是有血在流,因为壕沟是小鱼游泳的地方。”他说。“诱饵。”他对我说。我断断续续地听着,转头看向另一边,朵兰缇娜,突然间,那壕沟在我眼中真的成了一条血河,而我却像死人变成的鱼一样在里面游泳。“杀,然后立刻忘记。”就是热头鹰在和我一起爬上钟楼时对我说的话,他朝清真寺撇撇头。我在空隙间架好狙击步枪,眼睛压在瞄准镜上,我说,瞄准镜,我对你说,看见尖塔里有人影在动。我想说什么,但是上尉在后面朝着我的靴子就是一脚。
“你知道死亡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他问我。
“什么?”我回答,紧跟着那道影子,它又在尖塔里转了弯。
“没有人告诉你你已经死了!”是他的反驳,接着他又踹了一脚我的脚后跟就下楼去了,像老鼠般吱吱尖叫。
这倒是真的,朵兰缇娜,的确如此;死亡与我们如影随形,可我们却不认识彼此,一辈子都说不上一句话。
注释
[1]两个词皆有“阴茎”之意。——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