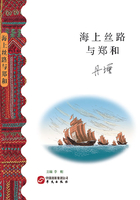戈列格里斯隔天一大早便出门,那天天色阴暗,雾气蒙蒙。他昨晚上床后,竟反常地很快就入睡,沉入波涛汹涌的梦境中,令人费解的船、衣服和监狱在梦中一排排涌来。虽然难以理喻,倒也不太难受,更算不上噩梦,因为那些如狂想曲般无序变换的插曲总被一个无声、却又十分真实的声音压制下去。那声音属于一个女人。他心急如焚地寻找这女人的名字,仿佛那事关乎己命。在他醒来的一瞬间,他想起了这个名字:昆赛桑,女医生如神话般美丽的名字,刻在诊所大门口的黄铜板上:玛丽安娜·昆赛桑·埃萨。他轻声读着这名字,一段遗忘的梦境浮现在脑海:一名快速变换身份的女人取下他的眼镜,重重按着他的鼻梁,现在他还能感觉得到那重量。
醒来时已是午夜一点,不可能再入睡,于是他翻阅普拉多的书,在一个段落停下来。
夜中稍纵即逝的脸
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与人相遇正如深夜里呼啸交驰而过的列车。我们望向在朦胧黯淡的车窗后的人,仓促一瞥。还来不及看清,对方已从视线中消失。那是男人还是女人?从对面车窗灯影里稍纵即逝的影像,就像从虚无中浮现的幻影,没有目的与意义,直接闯入无人的深夜。他们认识吗?是否在交谈,欢笑,或在哭泣?你会说:这正好比陌生人在风雨中擦肩而过。但很多人长期面对面而坐,我们同吃、同住、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何来稍纵即逝?稳定关系、信赖感,乃至亲密的了解都在蒙骗我们的错觉:难道我们不是为了安慰自己而发明假象,用以掩盖并祛除那稍纵即逝,只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一刻里捉得住它?他人的每一次注视、眼神每一次交会,不正像交驰而过的列车上旅人的视线,如鬼魅般短暂交接,在让一切战栗的疾速与强大气流中麻木?我们看陌生人的眼神不正如夜晚交驰的列车,迅速地从别人脸上挪开?留下的不过是臆测、浮想,以及凭空想象的特征?难道事实上相遇的不是人,而是投射出己身意念的影子?
戈列格里斯心想,身为一个从内心激荡深处呐喊出孤独的男人的妹妹,会有何等感受?这个在反思中将不留情面的结论公之于世的人,文字却丝毫没有绝望或冲动。当他的助手、递给他针筒、替他帮病人包扎伤口的人会怎么想呢?他写出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及陌生时有没有想过:这对蓝屋诊所的气氛有何意义?他是否把一切藏在心底?蓝屋是否是他唯一能吐露心声之地?他是否走过一间间的房间,手里拿本书,想着要听哪首曲子?哪种乐声适合他孤独的思考?是否明澈坚硬宛如玻璃?他在寻找与内心同调的乐声,抑或要宛如香脂的曲调和旋律,不至于让人迷醉恍惚,却让人内心祥和?
近破晓时,戈列格里斯怀着满腹疑问又浅浅滑入梦乡。睡梦中,他站在一道虚幻的蓝色窄门前,他想按铃,却又不确定该跟出来开门的老妇说什么。醒来后,他换上新装,戴着新眼镜去餐厅吃早餐。女服务生发现他崭新的外表时吃了一惊,一抹微笑随即扫过她的脸。现在他踏着雾色灰浓的周日清晨,去寻找老科蒂尼奥描述的蓝屋。
他在察看上城几条窄巷时,忽然发现在第一晚跟踪过的男人,刚好走到窗边抽烟。那栋房子在日光下看来比夜里更狭窄破落。房间内部虽在阴影中,戈列格里斯还是瞥见沙发上的织毯、摆设彩绘瓷像的玻璃柜,以及耶稣受难十字架。他停下来,望着抽烟男子。
“一座蓝色房子?”他问。
那男人将手罩在耳上,戈列格里斯又问了一次。回答滔滔不绝,他一句都听不懂,老人夹着烟的手同时上下舞动。老人说话时,一名身形佝偻、老态龙钟的妇人走到他身边。
“蓝屋诊所?”戈列格里斯问。
“是!”妇人声音嘶嘶响着,又说了一遍,“是!”
她挥舞着骨瘦如柴的手臂与皱巴巴的手指,激动地比画了半天。戈列格里斯好一会儿才明白,她在招呼他进去。他迟疑地走进屋子,房里的霉味与烧焦的油味朝他扑来。要进入老人正在等待的房间,像是得冲过一堵气味令人作呕的厚墙壁。这时,老人唇间叼上了一根新香烟。他一瘸一瘸地领着戈列格里斯来到客厅,嘴里含糊不清自语着,手飘忽地一摆,示意他在铺着织毯的沙发上坐下。
接下来半小时,戈列格里斯吃力地在两位老人令人费解的葡萄牙文及变化多端的手势间辨明头绪。老人试着向他说明,四十年前普拉多为这社区居民看诊的情形。言语间流露出对医生的敬重,尊敬一位远比自己杰出的人。但语调中还有另一种情绪,戈列格里斯渐渐才看出,那谨慎的情绪来自多年来不愿承认的指责,却又无法完全从记忆中清除。大家开始回避他,伤透了他的心。他想起科蒂尼奥告诉他,普拉多曾经救过有“里斯本屠夫”之称的鲁伊·路易斯·门德斯的命。
老人拉起一只裤脚,将一块伤疤指给戈列格里斯看。“这是他治疗的。”他用尼古丁熏黄的手指指着伤疤。老妇用皱巴巴的手揉着太阳穴,然后做出一个飞了的动作:普拉多治好她的头痛。她还指出自己手指上的一小块疤痕,从前那里大概有块疣吧。
戈列格里斯后来常自问,到底是什么让他最终下定决心去按蓝屋的门铃?这时便会不禁想起两位老人的手势,想到那名先受人尊敬,尔后遭唾弃,最后重新获得人们景仰的医生在两老的身上留下的痕迹,医生的手仿佛在他们的身上复活。
戈列格里斯详细打听去普拉多诊所的路后,便向两位老人告辞。他们头挨着头,在窗口目送他。戈列格里斯觉得他们的眼神中似乎含有妒意,一种矛盾的嫉妒:他可以去做他们已无能为力的事,去认识全新的普拉多,由此开拓一条通往自己过往人生的道路。
透过认知和理解他人,真的是看清自己的最好途径吗?尽管他人的人生与自己不同,拥有迥然不同的思考逻辑?对他人的好奇心,跟自己对人生流逝的感叹又有何关?
戈列格里斯站在一间小酒吧的吧台旁喝咖啡,他是第二次站在这里了。一小时前,他刚好来到路易士·路克斯·索里亚诺街,往前走了几步后,便看到普拉多的蓝屋诊所。那是一幢三层楼的屋子,蓝色瓷砖墙确实曾让房子泛着蓝色,但最突出的还是涂上闪亮深蓝色的高大拱窗。油漆虽已老旧,色彩斑驳,有些潮湿的部位长出黑色苔藓。连窗台下锻铁窗框上的蓝漆都开始剥落,只有大门上的蓝漆完美无缺,仿佛在说:看看这里吧,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门铃上没有挂名牌。戈列格里斯看着黄铜门环时,心中狂跳不已。我未来的一切似乎都维系在这道门后。他想着,然后朝几栋房子外的小酒吧走去,内心在与要他放弃的威胁感抗争。他看看时间:就在六天前,他正好在这时刻从教室里的挂钩上取下湿漉漉的大衣,头也不回地脱离原本安稳有条理的生活。他摸进外套口袋,碰到伯恩寓所的钥匙。一股强烈的欲望涌来,仿佛突然爆发的饥饿感:他想要读一段希腊文或希伯来文,要美丽的外来文字出现在眼前。四十年过去了,这些文字对他依然具有东方神奇的优雅魅力。他想证实,在经历过不知所措的六天后,他并未丧失理解那些文字的能力。
科蒂尼奥送的希腊葡萄牙文双语《新约圣经》放在旅馆内,但旅馆离这里太远。他想要读,想在这距离蓝屋不远的地方,在威胁着要吞没他的蓝屋大门尚未启开前,在此地此刻就要读。他赶紧结了账,去找一家有他想看书籍的书店。不巧今天是星期天,他只找到一家大门紧闭的教会书店,玻璃橱窗里摆着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的书。他的额头紧靠在雾气朦胧的玻璃上,再次感受自己想去机场,登上下一班飞返苏黎世班机的蠢动。他意识到自己战胜那咄咄逼人的期望后如释重负,他仿佛经历了一场猛爆性高烧又退了烧,耐心地等待热潮退去,然后缓缓走回蓝屋附近的酒吧。
他从新外套的口袋里取出普拉多的书,看着葡萄牙医生果断无畏的面孔,一名因恪守职责而遭致无情对待的医生,一名反抗运动者,试图用生命去换抵无罪之罪。他还是一个文字炼金师,最大的热情乃是让缄默的人生打破沉默。
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倘若在此期间蓝屋换了主人,那该怎么办?他匆忙将咖啡钱放在吧台上,然后冲向蓝屋。他在蓝色大门前深深吸了两口气,然后让气缓缓从肺部排出。他按下门铃。
门铃叮当响了起来,宛如来自遥远的中世纪,声音在整栋房子里回荡。没有动静。没有灯光,没有脚步声。戈列格里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又按了一下。依然无声无息。他转身,疲倦地倚在门上,想着自己在伯恩的寓所。他感到释然,一切终于过去了。他慢慢将普拉多的书放进大衣口袋,抚摸了一下大门上冰凉的门锁,慢慢抽开身子,打算远离此地。
就在这时,他听到里面传来脚步声,有人从楼梯上走下来。透过门窗,他看到屋里出现了一道光亮,脚步声接近大门。
“是谁?”门后传来一个女人深沉沙哑的问话。
戈列格里斯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他默默等待。几秒钟后,钥匙在孔眼内旋转,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