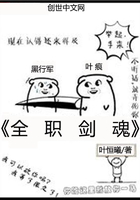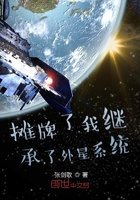或许在暴风城绝大多数人眼里,“已宰的羔羊”这间酒吧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地方。但对我这个外地到此,寻亲无门的落魄汉来说,那真是我唯一可以落脚的地方了。来到暴风城半年,回想起刚来这里时,我真是倒尽了霉。老家的房子塌了,带来的那点旅费花的精光,要投奔的远房表哥海宁也已经死了,还被街头的流氓给差点打死。如果不是酒保维尔逊老哥救了我,也许当时就已经死了吧。
维尔逊是个好人,虽然我对他了解不多。当他得知我是海宁的远房表弟后,对我诸多关照。不仅安排我去他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已宰的羔羊”打打零工帮帮忙,每天烧烧水,擦擦桌子,帮着打扫打扫。同时还给我找了个住处。那是一间破旧的空屋,原本是放杂物的,从没人住过。在酒吧后门附近,紧挨着后巷。有扇隐蔽的窗户,有月亮的晚上,可以把后巷看得清清楚楚。
像我这样的乡下小子,无父无母,无牵无挂。能有一个安身落脚的住处其实我很知足了。只是这间房子的隔音实在不好。而后巷应该是这个华美的暴风城里最阴暗的地方之一了。而时不时窜来的风,又会把后巷里的声音,隔着老远传进房间。我这人睡觉总是不安稳,可能是没安全感吧,有一点声音就会惊醒,而往往夜越深,后巷越是一点都不安静。每每如此,我就会爬起来听听外面的声音,实在好奇时就会凑到窗户边上去看个究竟。虽然多数时候只能看见小偷、夜游神、偶尔游荡至此的醉汉、又或是些不知哪跑来的妓女,难道这里还有客人招徕?当然还有些我最害怕,从来都不敢直视,即使给他们送酒或餐食去时都只是低头凑过去的术士们。他们每每在阴沉的夜色中说着一些我听不懂,也不想听懂的事。随着风钻进耳朵。
我有时在想,我是不是也或多或少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听到了一些不该听的话呢?然而我却一直都活的好好的,或许是我这个破屋实在太不引人注意,又或者是我这样的乡下来的穷小子实在是太微不足道,连被杀人灭口的必要都没有。然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那严实的嘴巴。我从不在人前说闲话。人后也不,因为我觉得像我这般的穷光蛋或是小人物想活的更好,学会闭嘴是很聪明的事。
不过很多时候,你不惹麻烦,麻烦却会来惹你。它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在你不想见到它的时候前来拜访你的生活。
暴风城最近处在全城戒严中,因为短短几天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凶杀案件。那个杀手下手绝对干脆利落,几乎每个被杀的贵族都是被一击毙命,按常识说,干这些勾当的,都该是那些传说中的神龙见守不见尾的盗贼,但这个杀手的身份职业如果真如传言所说,那么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据说那些死者,都是死在强力的冲击之下,看不见伤口,身体却又实实在在受到了重击,这样杀人可不是盗贼们的风格。只有高阶的神圣法术才能办得到。据最后被杀的那家里的管家说,凶手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人,但是身手却很矫健。关于这些,虽然暴风城高层要求消息完全封锁,可风言风语还是越禁越多。大家私下里没少谈论,绝大多数人认为下手的极有可能是个圣骑士,而且能从府邸中杀了人还全身而退,甚至不留痕迹。显然身经百战,本领非凡。
如果坊间传言是真的,那么我虽然可以理解官方封锁消息做的理由。但是一如既往的把责任推给了迪菲亚兄弟会就不算太高明了。有点脑子的,甚至我这个乡下小子也能想到,如果那些蟊贼真有本事请来这样厉害的圣骑士替他们搞暗杀,那么他们也不至于“什么事”都需要负责了。
“已宰的羔羊”因为是三教九流常常出没的地方,上头自然查的特别严。全副武装的卫兵们面无表情的站在门口,店里时常游荡着一些看上去有些陌生,但仔细看又颇有些熟悉的面孔,也许当中充斥着相当数量的密探又或是赏金猎人。为了那高达3000金币的悬赏。如此情况下,生意怎么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段时间里,后巷倒是安静了很多。没有了东游西荡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我总算能睡的好些了。
不过比较让人头疼的是,上头显然对“已宰的羔羊”非常怀疑。连我这个小小的跑堂,都被传唤了好几次,问些有的没的的问题。何况维尔逊那个消息最为灵通的老油条。这段时间,他被传讯的次数简直多得数不清。甚至昨天早上刚开业,就被卫兵带去问话。天黑了才回来。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可就是没人信,难道我就该知道谁是杀手?”维尔逊像是故意说给门口的卫兵听似的大声冲着老酒鬼杰拉德说道。
“哈哈,没错,每天站在这里跟木桩似的,难道那个杀手会像一只瞎了眼的兔子似的撞上来吗?”杰拉德说完哈哈大笑,酒吧里的熟人也跟着起哄。
我虽然不敢开腔,但也觉得杰拉德的话颇有道理。而且,随着一些关于这一系列的事的传闻越来越多。官方的态度和民间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我不懂什么政治,自然听不明白那些关于这一系列暗杀是否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看法。然而我坚信那些被杀的贵族绝对不是之前上头所说的那么无辜和清白。我比较相信开着一家侦探社消息灵通的凯特说的,其实那几个死了的贵族根本就是一群国家的蛀虫。他们中有贪赃枉法者、有强抢民女者、有专横跋扈者、总是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但随着这几个家伙的死。随之浮出水面的一桩大事,更是让人惊叹。
虽然具体的事情和贪污金额不明,但是这几个家伙显然都和之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克扣石匠工会工资的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政府已经公开惩处了好几个涉案的贵族。但其实谁都心里有数,连我这个穷乡僻壤没见过市面的小子都知道,那不过是一种无关痛痒的安抚。给我们这些平民看的一场戏而已。
不知道和之前那些“小鱼”比,这几个挂了的家伙比不比的上运河里的那只“大鳄”。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消息传开,街知巷闻,短短几天里,那个杀手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从一个人人闻之色变的凶手,变成了一个英雄。紧接着引起了政府更激烈的反应,还有全城的大戒严和大搜捕。比之前的更厉害。
结果依旧是一无所获。虽然好几次都说抓到了有重大嫌疑的人,最后又是不了了之。几次下来,大家也就觉得兴趣索然,懒得去关注更多。官方除了大加渲染的杀手的凶残以及“兄弟会”的穷凶极恶外。也显得无所作为。
只是这个杀手的形象在我们平民的心目中变得更加鲜活了。有人猜测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无法容忍日见堕落的联盟政府,所以铤而走险,为民除害。有人猜测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贵族,因为知道种种内幕,所以毅然出手,惩奸除恶。也有人说见过他,说这话的是一个流浪汉,自然没人相信。
《暴风城观察报》的主编保罗,同时也是酒吧的常客,作为一个参加过两次战争的退伍老骑士,他一向敢做敢言,常站在民众的立场撰写文章。并不畏惧上头的压力。虽然为此报纸多次被勒令停刊,但他不卑不亢,还是固执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家都对他非常的敬佩。常常有人说他一把年纪,依旧没有丢下手中的剑。
他喜欢在酒吧里大声的谈论起他的想法,神采飞扬时,让他显得意气风发,有些发白的须发飘荡着,看上去年轻了很多。
其实,我不是很懂他那些关于信仰和圣光的讨论。因为在这个年代里,圣光显得那么微弱,那么无力。我们曾经在它所给予的力量和支撑,辉煌而骄傲的生活过。我回忆起自己儿时所度过的幸福时光,也常常面带微笑,但随着那比洪水更凶猛,比雷电更残酷,比烈火更疯狂的亡灵天灾把一切撕碎,我已经失去了支持信仰的基础。圣光在哪里?圣光是什么?如果我们是无罪的,我们是无辜的。那么什么是公正的力量?谁又能给那夺去我们幸福和生命的罪恶以惩罚?
今天,保罗又在酒吧里一边喝酒,一边拿着准备第二天放到报纸上的稿子念道:“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一切的杀戮是一个圣骑士所为,那么我仅代表自己,一个老圣骑士,对这种行为表示最严厉的谴责。拥有力量并不代表拥有了审判别人的权利,力量更不是用来夺取别人生命的工具。圣骑士永远不能忘记他所必须遵行的操守和美德。然而我同时也是一个平民,一个祈望政府廉洁,人民团结,社会安定的平民。当罪恶不受到应得的惩罚,当正义得不到应得的伸张。那么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一种“公正”?难道这不是我们该为之思考的事吗……”他每当说到激动时,总会想演讲般的挥舞他的手臂。旁若无人。
我听着他的话,若有所思。
晚上,维尔逊请我帮忙和他家里人打个招呼,通知他的妻儿自己晚上不回去了。
去办妥了这件事,明明已经很晚了,我却不知为什么睡不着。就在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时,安静了很久的后巷忽然传来了人声。随着风传入耳中。
“你现在就要走吗?”这个声音我很熟悉,是维尔逊。
“嗯。”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传入耳中。难以分辨性别和年龄。
“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卫兵换防的时候,你应该可以顺利的离开。”维尔逊尽管压低声音,但我还是听的挺清楚。
“你真的没有考虑过告发我吗?”那个声音说道。
“我其实也有想过啊,好几次我几乎就快给打动了。要知道,现在的赏金可是涨到了5000金币哦。” 维尔逊说道。
“我知道这件事,想不到我还那么值钱呢。伯父他把我藏在地下室里,尽管他很生气,骂了我好多次。但是他到底还是没有去告发我。而且还不时的把最新的消息告诉我。”那个声音显得有些伤感,很低沉,很缓慢。
“保罗就是那种人,当初你会做圣骑士不也是因为他嘛。其实他今天在酒吧里说了很多话,一般他说的话,都会第二天登在报纸上,他作为一个圣骑士不认同你的做法,然而作为你的伯父,以及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或许他又有点认同你的想法吧。”维尔逊说道。
“我其实已经没资格被称为一个圣骑士了,关于对错,我也不愿再去考虑。多余的话我也不想再说了,很快卫兵要回来了。我会去瘟疫之地,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死在诺森德。今后,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那个人说道。
“关于海宁的事,我希望你别再放在心上了,他死了,而你还活着。好好保重吧。可能的话,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心上人。” 维尔逊说道。
这时,月亮突然出来了,还有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吹开了窗户,一阵声响,我被吓了一跳,赶快从椅子上轻轻下来。但还是忍不住好奇,于是又站了上去,而窗外,维尔逊已经不知哪里去了。而仿佛拉开幕布的舞台上,月光把后巷照的非常清晰,那个人影也清晰了,是一个满头金发的姑娘。长发反射着月光,在身后甩下一条长长的倒影。我似乎见过这个背影。她似乎很像那个偶尔来店里喝酒的美丽姑娘。总是恬静的微笑着。即使有人出言调戏,也是一言不发。
难道是她?
她是谁?
正在迟疑,月亮被云遮住了,我揉着眼睛去辨认,去观察,却什么也无法再看见。我知道我再也无法看见她了。
第二天,一切还是那样。悬赏单依旧被贴在大街小巷,仿佛就永远会这样被张贴着。维尔逊还是那个样子,保罗也依旧时常来喝酒。喝到激动就发表演讲似的大声喧哗。我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屋子里那窗户封上,连同一切我看见的,听见的,全部都忘记掉。如果可能,我希望最近能去表哥海宁的墓上送上一束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这样做,但我觉得我似乎也只能做这个。
难道还要我去思考关于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吗?
那太麻烦了,我还想活得久一点。
有些时候,信念这东西真的很麻烦,天天挂在嘴边上也想必很累,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如果有能力的话,就去做吧。
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又算是真正的公正,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