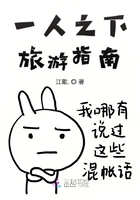无论在大海中遗失了什么(一个你或一个我),
我们找回的总是自己。
——E.E.卡明斯[1]
艾希:龙虾为什么会变红?
艾迪:我不知道。
艾希:因为大海撒尿了。
我最讨厌父亲的一点是,他讨厌我。
他有很多理由讨厌我。
不过我们都对那些讳莫如深。
父亲的眼眸是冰冷的浅蓝色,上一秒可以充满厌恶,下一秒却会哀伤地让人同情。我无法忍受怜悯他的感觉。每当我看着他,喉咙里就感觉好像有蛆虫在扭动。要克服这种令人作呕的瘙痒,唯一的办法是屏住呼吸,拼命将其往下咽,直到快要昏厥。最好的办法是不看他的脸或眼睛,更好的办法是压根不要看他。
幸运的是他几乎不怎么在家。他要么在外面跑步,让镇上的女人们对着他雕塑般的明星下巴发花痴,要么就待在因弗内斯他上班的银行里,或者在苏格兰到处出差放贷款。不要误解,他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相反,他总是发牢骚,抱怨他的客户们只关心自己拥有多少汽车和电视机,却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可怕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无动于衷。“黑岛的雨季没那么可怕,”他总是说,“想想那些年年都要发大水的偏远小村庄,那里的人能怎么办?”或者,“有些国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被蚊子叮了而死掉。”蚊子多的季节,我如果抱怨被叮了,他就会喋喋不休地念叨这句话。(蚊子爱吸我的血。)
我妈妈对他说:“等你发现怎么治疟疾,一定要通知我们。不过现在你儿子就要考试了,他需要抓紧时间看书。还有,你女儿的校服又嫌小了。”我真希望她不要用我的体重问题来引起他的注意。她为什么不提煤气欠费或者我房间返潮需要处理?
在父亲的床头柜里放着一本被墨水笔涂满的地图册。蓝色的点是他去过的地方,红色的点则是他的梦想目的地。地图上的澳大利亚被涂了一个大大的红点,涂得太用力了,红墨水印到了下一页的地图上——太平洋的中间。其实他二十岁的时候差一点就去了澳大利亚,那时他在游轮上当吉他歌手。我们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讲睡前故事,讲他旅途中的故事,他的声音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轻柔。雅加达港口的故事是他最喜欢讲的:那天,天气闷热、雷声滚滚,他乘的船正要离开港口,下一站就是澳大利亚。恰巧那时他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我的大哥——迪伦出生了。他说:“我太惊喜了,差点从船上掉下去,不过后来是我自己跳下船游回岸上的。”
妈妈说那不是真的,又说他其实想留在船上。我常常想,如果他当时留在船上,又或者他真的是高兴地滚下船去的,现在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对父母在我出生之前的生活片段大概知道一些,大部分是外婆去世前(还有她和妈妈闹翻之前)告诉我的。我的父母在迪伦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搬到了在麦凯伦大道的家。这是福特罗斯最便宜的房子,可能在整个黑岛也是。它便宜是因为房子的墙壁已经快塌了,而且屋后紧连着一片墓地。当时我父亲想回船上再多工作几个月,那样他们就能攒够钱搬到城里去,但妈妈无论如何都不肯放他走。她觉得他一定会一去不复返。
可他的确去努力挣钱了,去因弗内斯的各个酒吧里当驻唱歌手。但房子一直没钱修,账单也一直没有付清过。
一天,他们收到催缴欠款的最后通牒,当时妈妈正怀着孕,激动地押着父亲去了最近的银行,逼他填了银行职员的求职申请表。(这是他说的。)最后终于有一天,父亲挣够了钱,全家准备搬回城里去了。那天我们已经打包好行李,每人都分到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箱,里面装满各自的衣服和玩具。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我弟弟失踪了。
“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在我们本该搬走的那天,妈妈透过卧室窗户,望着外面的那些墓碑喃喃自语,“现在我的儿子也在那里。”
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事实。他不是真的埋在那里,我们只是在那里立了一块刻着他名字的墓碑。
我们再没打开过那个属于他的纸箱。妈妈用胶带把箱子封得严严实实,确保什么都掉不出来。我有时会想起阁楼上他的旧玩具:一只叫戈登的灰色毛绒海豚,那是他在海豹馆里耍了一通赖皮后我父亲才给他买的;一架木琴;一个巴布工程师的神奇画板,上面用黑色波浪线写着他的名字——如果被擦掉他一定会哭的;还有他收集的数百根松针(是枯死的柔软的松针,因为新鲜的会扎手,现在可能已经变成堆肥了)。我试着不去想他的衣服,衣服都被叠起来打包好,一定已经受潮变得皱巴巴。那些只是让我想起,他再也穿不上那些衣服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衣服都被叠了起来,努力不去想那些衣服将会变成其他人的烦心事。
注释:
[1]美国著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