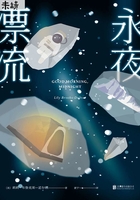二月的一个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我坐在一辆专职司机驾驶的小车的后排。司机和我在车里尴尬地沉默着,窗外射进来的强烈光线让我很难看清手机去确定我已经知道的消息:我要与他一起旅行的那个人,我此刻应该与他一起待在机场的那个人居然不见了。
我看着人们在东二十街的那家印度餐馆进进出出,我们的车就停在它前面,但我不是来这里吃咖喱的。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把我们的明星市场分析家鲁道夫·吉布斯给找出来,据我所知这里就是个淫窝。如果想赶上下午四点的航班,我就得在五分钟内把他给弄出来。
眼前的人穿梭如织,这让我处于持续的焦虑状态。我不能把一个成年人绑进车座上,用海盗游戏的战利品堵住他,把他带到我需要他去的地方。我和助理们一再确认计划,重复预订航班。我们有后备计划,但这趟旅行还是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令人束手无策的闹剧。如果吉布斯和我错过今天的航班,那么我们和一位客户的晚餐将会泡汤。
根据我在玻璃天花板俱乐部的调查,吉布斯可能就在这家餐馆上面的一间公寓里。这是一栋不起眼的白砖楼,大约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在街区开满美甲店和照相馆。吉布斯是个盖茨比式的人物,总是穿着英式手工缝制的西装,戴着领结而非领带。这个聪明的已婚男人经常能准确地预测到美国金融市场的动向,这令他得意忘形,成了一个花花公子。经济新闻频道采访不够鲁道夫·吉布斯。今晚我在南方最大的客户雷蒙·詹姆斯将在这场晚宴上带十个人来见他。不管他在这栋大楼里干什么,如果他不快点儿出来,不快点儿上这辆车,今晚全都会泡汤。我能处理得了飞机预订、汽车服务、晚餐预订、描画美元/欧元关系的曲线图的文字材料,但我控制不了鲁道夫·吉布斯。
“那么他和谁一起吃的午餐?”我一小时前问过他的神秘助理。她告诉我是和一个来自美国华平投资集团的客户。她不肯告诉我具体是谁,但我知道华平投资集团有相当多的人在那里四处探寻。我分析已知的信息,无果,又去找了他的助理。
“他是不是有个爱巢?”我问她。如果他有,我会吃惊。通常都是生活在郊区的已婚男人在城里会有间小公寓,但吉布斯是纽约人。如果晚上加班到很晚,郊区的已婚男人会去公寓睡而不是回家。但这些公寓被称为爱巢并非因为主人喜欢工作。
“他没有。”他忠实的助理答道,语气几乎透着骄傲。
“也许我要试试他喜欢的那家印度餐馆。”从她的欲言又止中我判断,她只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保守他的秘密。她只想让我走开。
“你知道那个地方?”她谨慎地问我。
“别的女人跟我讲过,”我说,“我会找到他的。”
我在办公室给阿曼达打过电话。“那个地方具体在哪里?”我问她。
“请做好记妓院清单的准备,”她讽刺道,“金不在办公室。我试着问下伯尔斯桥。”
我就是这么来到这个有可能是淫窝的地方的。我现在该怎么做呢?要在门上敲什么神秘的暗号吗?这家餐馆自然看上去是合法的。我下车去里面一探究竟,甚至假装去看贴在柜台上的显眼菜单。宝莱坞海报装饰着墙壁,摆放在角落里的是假盆栽,姜黄的气味飘浮在空气中。当我晃到柜台左边的一扇内门时,我注意到它比其他门更为气派些。这扇门上镶嵌着一面板的蜂鸣器,其外围是一圈闪闪发光的黄铜。每个蜂鸣器似乎都暗示和一间公寓或一个房间的联系,其中一个名叫“独一无二的内部空间”。会是那个吗?我迟疑着要不要去乱按一通,但“独一无二的内部空间”似乎极具暗示性。柜台后面的印度厨师瞅着我。
“如果你想用卫生间,那你得买吃的才行。”他说。他还想说些什么,但停下了。
一个手推婴儿车的女人想进餐馆,刚好另一个女人想出去。她们在门口进行了一阵礼貌的混乱,想要离开的那个推开了门,然后撑着门等那位女士和孩子进来。就在那个要离开的女人撑着门时,我注意到她身上数量繁多的珠宝首饰、她修长的双腿,还有那高得惊人的鞋跟。我预感到什么,跟着她走到人行道上。她对这个地方来说有点过于艳丽了。
“哦,打扰一下。”我说。她皱起眉。她太年轻了,不该显得这么苍老。
“我在找,呃,我的上司。”我撒谎道。
“我不认识你的什么上司。”她说着继续走,或者说是重重地踩着鞋子走着。
“他妻子要来这里找他,”我说道,“所以我想先把他从这里弄出来。”
她长长地看了一眼我和我的职业西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有点生气,但并不令人信服。我继续撒谎,试图判断出她是从哪里来的。俄罗斯?肯定是东欧的某个地方。
“我上司的老婆。”我跟着她沿着这个街区走着,“我需要他现在就跟我走。他在这里会被逮个正着的。她是个刻薄的泼妇。”我补充道,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我从来没见过吉布斯的妻子,但我打赌她不是个泼妇。
“你会失去他的生意。”我补充道,使出浑身解数打动她。
“我也许能帮你,”她说,“但我不知道你老板的名字。”
我刚想说鲁道夫,但赶紧停住了。吉布斯绝不会用自己的真名。
“哦,呃,是……”
“迪克逊还是雷曼先生?”她问,完全知道我的问题所在。她似乎没了耐心,就像我在浪费她宝贵的停工时间。
我思索片刻。她并不是真的问那个,对不对?这些男人用他们公司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别名?真的吗?雷曼究竟有谁在这里?我突然觉得并不害臊进去了。我好奇得发疯。
“哦,是迪克逊先生。肯定是他。我可以进去找他吗?”我问道。我得去看看这个地方里面到底是什么样。
东方集团女士已经转身快步走进餐馆。她朝我挥舞手臂,示意我等着。我照做了,不想惹恼她。我爬回到车后座上,不到三分钟吉布斯就走进了阳光里,手里慎重地抓着一个过夜的包,脚步有些跳跃,有个袖扣没有扣好。他看上去像个刚离开健身房的男人。他只停了一会儿找我,然后笔直朝车子走来,对司机挥手表示不必麻烦下来给他开门。他滑进我身边的后车座,身上散发着刚沐浴过的香气。
“伊莎贝尔!”他喊道。“你看起来有点浮肿,宝贝。你准备好今晚会面的分发资料了吗?”
我对他极为恼火,但同时又大大松了口气,以至于我说话都有点儿不连贯。
“好吧,是的,在刚才的一小时里。”
“很好。你也处理好了这次旅行的午餐费用?我想是的,对吧?”
他掏出一个皮文件夹,拿出一张卷曲的账单和信用卡收据。
“请六个华平投资的人吃的午餐”,他在费用报告的顶端写着。价格?1800美元。
与其说那是他陪客户的费用,不如说是我陪他的。是这样吗?账单看起来好像钱是在餐馆消费的,这家餐馆,这个地方在生意最好的时候也不可能做出这么多的酸豆和咖喱。
“我们在机场买点儿东西吧,”他说,“我不吃飞机上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