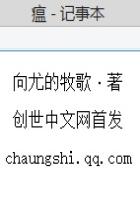碧花跳了出来,叉着腰指着吴氏大叫道:“什么叫就是从我们卷舒阁拿出来的!吴姨奶奶扯谎想要污蔑我们家姑娘也得说个可靠的谎话。”
又三言两语解释当日发生的事情,怕自己姑娘被平白泼了一身脏水。
“那日你觍着脸来求姑娘赏你点冰肌膏,可我们姑娘忌讳吴姨奶奶有身孕,叫你自己去看了大夫用药,院子里那么多双眼睛瞧着,是吴姨奶奶记性不好,还是当咱们卷舒阁里的下人眼都是瞎的。”
卷舒阁外,闻声赶来其他奴仆,她们不敢掺合,只能探着个头张望里面的动静。
围着吴氏的下人也七嘴八舌说着。
“是啊,吴姨奶奶,你可不是记错了……”
“怕是自己用错了药,还不快些去看大夫。”
容沨也沉声道:“说得对,吴姨奶奶有空在我这儿闹不如快些让大夫看看,你若再胡搅蛮缠我只能叫祖母来处置你了。”
吴氏怒气冲冲,即使脸烂掉了,也依旧可以看出她铁青的脸色,怒骂:“都说咱们府里的四姑娘惯会做人,谁知道心肝儿都是黑的,肚子都藏着腌臜货。”
她手里拿着剪子指着容沨,到有几分一往无前的狠劲儿,又恶狠狠地冲其他人道:“谁敢拦我!我拉着她一同死去!都给我让开!”
容沨声音发寒,半眯着眼睛盯着吴氏:“我说了,之前我不曾给过吴姨奶奶什么冰肌膏,也不知道你手里的冰肌膏是从什么人哪里得的,非要说是从我卷舒阁拿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云宵眼疾手快夺下吴氏的手中的剪子,吴氏挺着肚子凭着一股儿狠劲但少了几分灵活。
吴氏瞪着眼睛想着之前在花厅听丫鬟议论的话,她的脸烂了怕是好不了了,到时候他就是生出个公子又有谁在乎。
她整个陷入魔怔中,忽地大叫一声,剪子一转在云宵手背上划了一道血口子,剪子又落回在吴氏手中。
“四姑娘你真是阴毒至极,你怕我生下孩子会抢夫人的地位,又记恨和我结怨,所以才要害我!”
云宵见吴氏胡乱蛮缠,听不进去一句话,捂着伤口冷声道:“我们家姑娘说了,不知道吴姨奶奶口中的冰肌膏是从哪里来的。”
吴氏把火气转到云宵身上:“你们一个个奴才养得贱骨头,小娼妇,你们是卷舒阁的人自然都是帮她,那冰肌膏就是我丫鬟从你们卷舒阁拿出来的。”
但吴氏前后说话,根本逻辑不通,容沨心下一沉,手隐隐收紧,她这是着了别人的道了。
“把吴姨奶奶请去祖母那儿!”
丫鬟婆子两人上前纷纷钳住吴氏的手臂,云宵又再次把她手中的剪子给缴获下来。
吴氏张着嘴,骂得难听,只顾自己心里痛快。
“住手!四姐姐院子里的奴才好大的派头,对主子都敢动手,也不怕哪天就翻了天。”
容涟慢条斯理地从大门走进院子,她眉眼含笑,但笑意不达眼底,她都帮吴氏算计好了,却不想是个没脑子的,闹了半天什么也没做成。
容沨冷嘲道:“奴才怎么都翻不了天,倒是吴姨奶奶不是在妹妹的仪月楼闹,却是一副事不关己,说风凉话的模样。”
容沨心中已有八分肯定这事儿和容涟脱不了干系,她微微抬起手,一反常态,故作感伤:“我与五妹妹是亲生姐妹,可始终没有半分亲近,往日我斥责五姐姐确实是你自己做错有碍侯府脸面的事儿,倒是你人小气量小总爱不分青红皂白来为难姐姐。”
一哭,二婊,三绿茶是容涟和周氏惯会的拿手好戏,今天见别人用了,脸色一变。
吴氏眼珠子一转,挣脱不开,便放声哀嚎恨不得整个侯府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冤屈:“我命苦啊!得苍天怜悯好不容易怀了侯爷的孩子,可谁知道被歹毒之人所害,有苦难言啊!”
其他人嘴角抽抽,看吴氏厚脸皮的模样,哪里像有苦难言,倒是四姑娘这里……
容涟柔柔一笑:“吴姨奶奶必然不会信口胡说,况且冰肌膏又不是寻常生药铺子都能配的便宜货,吴姨奶奶怎么可能得。”
此刻屋外,“六姑娘。”
容涵连忙上前见容涟咄咄逼人,暗藏杀机,她一低眉,又转身往别处去了。
容涟抬手碰了碰自己的珠钗,不经意道:“我记得前几日四姐姐得了祖母的赏,里面就有一盒冰肌膏,说是让四姐姐在擦上一道把手腕处烧伤的疤痕给除干净了……”
容沨目光凌厉,似寒星冷剑,清亮的声音几乎没有一丝温度,带着威严:“祖母给的赏赐是在吴姨奶奶走之后才得的。”
“我不曾打开,也不曾用过,不知吴姨奶奶是走的什么门路从我这里偷的,照五妹妹的意思,是说祖母……”
容涟脸色惊变:“四姐姐慎言!”
容沨长袖一甩:“该慎言的是五妹妹。”
“呦!可真热闹。”屋外的下人纷纷散去,只见秦妈妈走了进来,但脸上并无太多笑意,她略微扫视了下周围的人,心里大概有了计较。
“老夫人让老奴去仪月楼去寻五姑娘,五姑娘不在,叫老奴好找。”
容涟低着头,讪讪一笑。
秦妈妈又冲容沨行了一礼:“正好四姑娘,五姑娘和吴姨奶奶都在,老夫人有请。”
吴氏心下一阵慌乱后,陡然又升起一股子力气,挣开婆子的手,跟着秦妈妈一同回了寿安堂。
寿安堂内,吴氏一看见容老夫人扶着肚子就猛地跪下,也多亏她从前身子骨好,不然换谁都经不起她这样折腾。
吴氏哭得鼻涕眼泪横流,抓着容老夫人的衣角叫唤:“老夫人你要给婢妾做主啊!四姑娘这是要害死婢妾!”
容老夫人盯着吴氏的脸,眉眼一皱,秦妈妈会意上前将吴氏扶了起来:“吴姨奶奶可别再哭,脸上的伤可经不起折腾,老夫人已经着人把大夫请到了寿安堂,姨奶奶跟老奴一起去瞧瞧。”
吴氏止了哭声,关系自己的脸,她也不由紧张了起来,犹犹豫豫又狠狠地看着容沨,半推半就的去了隔间。
容老夫人摆了摆手,容涵默默退在身后,屋子没半晌没有人言语,气氛凝滞如冰。
容涟一进屋子便瞧见容涵正细心地给容老夫人捏着肩,她倒是明白了祖母在佛堂念经哪里会怎么快得消息,原来是有耳报神,不经从胸腔冷哼一声。
她小心翼翼开口:“不知祖母让秦妈妈去仪月楼唤孙女有何要事,六妹妹也在,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容老夫人脸色发沉,怒拍桌子骂道:“秦妈妈不这样说,难道还要看你们在卷舒阁给我打擂台唱戏!仪月楼离卷舒阁也不近,老婆子也不知道你是成日无所事事有闲心跑到哪儿为吴氏申冤抱不平。”
容涟跪在地上,避重就轻,委屈道:“孙女只是见卷舒阁的丫鬟婆子拿住了吴姨奶奶,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有所闪失才进去多嘴了几句。”
容老夫人缓了缓语气,却仍然有气:“你倒是好心,秦妈妈教你那么久的管家一点长进也没有,吴氏闹得天翻地覆不把她钳制住,难道还由得她胡搅蛮缠。”
容涟咬了咬牙,低垂着的眼眸看见旁边和她一同跪着的容沨的衣袂,脸色发青。
“孙女糊涂。”
容老夫人训完容涟后,又转而看向容沨:“吴氏说的话可真?”
容沨镇定道:“孙女冤枉。”
容老夫人沉默半晌,只见一丫鬟畏畏缩缩地走了进来,正是吴氏的丫鬟喜鹊。
“喜鹊你来说是怎么回事儿。”
喜鹊磕了个头,身子抖如筛糠,脸色发白。
“回老夫人,那日姨奶奶去向四姑娘求冰肌膏未果,便叫奴婢偷偷从老夫人赏给四姑娘的冰肌膏里挖了一点出来,姨奶奶也确实问了大夫说,若有冰肌膏擦脸,能治好她脸上的红肿,可几日过去后,脸上红肿不但未消,反而开始结块儿,里面还有脓水,不过一日脓水破了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容老夫人沉声审问:“那冰肌膏确实是从四姑娘的卷舒阁拿来的?”
喜鹊以为容老夫人心疑她说谎,着急地辩解:“是婢子亲自去偷的,老夫人若不信可问卷舒阁当日值班的下人,吴姨奶奶离开后,婢子借姨奶奶丢了耳坠的由头又回了卷舒阁。”
“我确实不信四丫头会害吴氏。”容老夫人转动着手中佛串,一字一句道。
喜鹊惊声哭了起来:“婢子不知,可姨奶奶自从脸上红肿后,就一直担心自己生下孩子不能恢复失了侯爷的宠爱,才会去向四姑娘求冰肌膏……婢子,婢子也不知为什么用了冰肌膏会成了这个样子。”
顿时所有矛头都指向容沨,容涟心里一阵畅快得意。
容涟弱弱道:“那吴姨奶奶也不可能为了陷害四姐姐把自己的脸害成这个样子。”
容沨将袖子往上挽了几分,赫然可见烧伤处的疤痕比手腕其他的肌肤要红上一些,像是涂了一层浅浅的胭脂。
“祖母赐给我冰肌膏是想让我除当初烧伤的疤痕,冰肌膏是什么东西五妹妹比我清楚,祖母把东西送来后,我不曾打开过,也未曾用过,不然这伤疤也不会还是这个样子。”
容涟微微仰头,细细说道:“祖母,不如叫大夫验上一验,查查吴姨奶奶用的冰肌膏和四姐姐卷舒阁的冰肌膏是不是一样的。”
她偏过头看向容沨,笑得发寒:“这样既能弄清楚吴姨奶奶到底是因何东西毁了脸,也不会冤枉了四姐姐。”
她倒要看看,这次容沨还能怎么样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