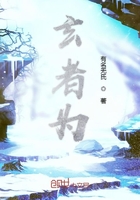以后的日子里,我逐渐的淡忘了心中的悲伤,只是在有意无意突然记起时,悲伤会再次涌上心头。我已经从那个萎靡不振的时期跨过了,摆脱了悲痛和复仇的束缚,我又重新蜕变成了单纯善良的小姑娘。我只是在心底慢慢地打算着以后的路子,慢慢地想着法子来重新报复那些在这次事件中的漏网之鱼。现在的我累了,我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谋划一切,让我们都暂时的安享一阵吧,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平静的,我不停的对自己说着。
脱去了谋略和心计的我轻松了很多,我终于可以暂时避开那种时时费神又胆战心惊的日子了。
飘红姑姑见我慢慢从悲痛中走出,便开始进行她最新的计划。她似乎和我想的一样,她也不想放过那些漏网之鱼。也许是为了联络更多的人,也许是要重新进行布阵,她暂时的离开了普济寺。只是,她走的时候告诫我:千万不可与外人接触,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她的离去不仅带给了我短暂的轻松,更让我在这个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得到了意外而动心的安慰。
苏彦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关心,甚至在我们那次出去散心之后,变得更加殷勤。我似乎有些被他感动,因为我的身边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过,只是我不确定这份感动会演变成什么。
我俩一起去普济寺后的深山中采药,我背着药篓,他拿着小铲,我俩一棵一棵的辨认着,一颗一颗的采挖着,装满药篓;我俩一起去山上看日出,看着天边的红日慢慢地向上移动着,一点一点的出现,我躺在他的怀中,看着红日,看看他,高兴地笑着;我俩一起坐在庭院之中下棋,人随棋动,可是他的眼光却直直的盯着我看个不停。
我俩幸福的朝看早霞,晚观夕阳,霞光映在我的脸上,夕阳照着我的头发,我只是幸福的甜蜜的笑着。我多想以后永远可以有人陪着,朝看霞色,晚观夕阳,直到脚步蹒跚,直到牙齿掉光。
苏彦,你真的会成为我的归属吗?我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唯一吗?我总是不停的问着自己,可是却始终没有确定的答复。
可是就在我对以后的幸福生活充满憧憬的时候,就在我对自己的归属有着确定的时候,就在我想着摆脱曾经一切的时候,他出现了。让我忘却了以前幸福的曾经,让我对规划好的未来产生了怀疑。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在我心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想。
他是在我正沉浸在我和苏彦的幸福之中时突然出现的,他的出现超过了我最荒谬的想象。那天我正和苏彦在山上采药,可是我突然抬头时,却发现在山顶云深雾绕之处,有一个飘飘的白衣身影。一瞬间,我以为那是我的幻觉,是出现在梦中的幻觉。那白衣飘飘,像极了予洛最后的身影;那白衣飘飘,也像极了子遥那股飘逸。我不可置信的再看一眼才敢确定,那确实是一个白衣身影,那不是梦境。我偷偷看一眼苏彦,可是他竟没有发现,他还在低头辨认着药草。我微微舒一口气,再次向那个山顶望去,可是此时却只见云雾,不见白衣。我不相信的再次遥望着寻找,可是,却迟迟找不回刚才的影子。我又叹一口气,心想着: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苏彦听着我叹气,发觉了我的异样。他温柔的问着我:“蕊儿,怎么了?”蕊儿。多么美的名字,可是我却没有真正拥有它。蕊儿,只有很小的时候坐在父亲腿上撒娇时,父亲才会这么叫我;只有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听她讲故事时,母亲才会这么叫我;只有在晚上和姐姐说悄悄话时,她才这么叫我。
杨西蕊,这个名字阔别了多少年。我只记得,在我进入普济寺后山时,我就再也不是当初的杨西蕊了。飘红姑姑说:“从此,你就叫画蘋吧。”是啊,画蘋,是不同于杨西蕊的。
听着他这样叫我,我有多么的伤怀,如今疼我的人都不在了。只有他,苏彦,还和当初一样,用他的一切来疼我。我深情的望他一眼,道:“没事。”此时,无论是谢予洛还是凌子遥都是没了意义的。因为,刚才的那一切都是幻觉,那只能是永远的幻觉。
可是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样简单,因为那真的不是我的幻觉。
在那天夜晚时分,我听到了阔别多时的凄婉绝美的箫声。我知道,幻觉从此都已结束。那是你,真正的你,凌子遥。
那箫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我便更加确定,因为只有你才能奏出如此的音韵,只有你才能将箫声演绎的如此高人一等。那箫声抑扬顿挫间,全是深情。更令我惊讶的是,那调子正是我们合奏的曲子的音调。
你还记得那次相遇吗?我们同奏一曲,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将曲子里的悲欢演绎的淋漓尽致。你看穿了我,看出了我曲子中暗含的忧伤,你轻轻地问着我:“你的曲子明明是彰显欢乐之意的,为什么其中会有隐约的愁思呢?”那时候,你如同是我的知己,在那个相遇中给了我心灵的安慰。
只是你忘了那次吗?那冰凉刺骨的话语冰封了我的心,从此,我再也不敢奢望任何的你的好。因为你给我的,只是那一次,对我就足够了。我永远忘不了,你的鲜血一滴一滴的染红衣袍。那是为了我啊。想至此处,一滴清泪滑过我的脸颊。你不该这么快就遗忘的。
我努力的回过头去,任凭泪水沾满枕头,浸湿着我的发。那悠扬的箫声穿透了我的耳膜,一个一个的音符如重锤一样狠狠的敲击着我的心。
子遥,真的是你吗?我是不相信的,你怎会到这普济寺中,你是大昭的王爷啊。你为什么这样,你应该是憎恨我的。你是知道的,我是刺杀你父皇的杀手;你是知道的,是我害你胳膊受伤的。我似乎习惯了你的冷漠,你的无视。你现在到来是为了什么啊?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死,你怎么知道我会在普济寺安身的?你不会是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吧,还是你想弄清楚我的一切在全面的对付我呢。我不敢想象你是因为思念我而来的,因为从那一次冰冷的话语开始,我就再也不敢奢望你那温柔的话语和柔情的眼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