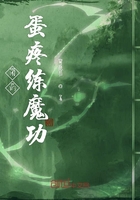吕洞宾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梦里他丢了所有的一切,通天彻地的修为,功名利禄,还有自己的挚爱。
突兀地他从噩梦中惊醒了,一伸手,一双白皙如玉的双手直入他的眼,这是他一千多年苦修剑道棋道而刻意保养的双手。寻常武者在修习武艺过后会忽略掉对手部的保养,那样反而更容易留下暗伤,吕洞宾从刚开始休息的时候就有注意到这点,故而他最宝贵的便是他这双玉手了。
吕洞宾对着玉手发着呆,身上的衣服早就不是自己的了,而周围的环境也很陌生,一切都不是梦,都是真的!
“我是谁?我在哪?”吕洞宾嘶吼着,才刚刚恢复元婴初期的修为从他瘦弱的躯体中喷涌而出,丝毫没有顾忌周遭雍容华贵的摆设,仅仅是片刻,便把这古朴典雅的厢房给摧毁得支离破粹。
凌冽地剑气骤然奔向那仅存的屏风,却见一层薄薄地风流缓缓护住了这脆弱地屏风,洪亮中厚地声音缓缓从屏风后传出。“醒了啊?”
却见屏风后慢慢走出来了一个身材中等,国字脸,带着一双透露着寒意的蚕丝手套的青年人,尽管他未发出气势,但是他的威压隐隐透露出了危险的气息。告诉着吕洞宾,以当前的修为,对上此人绝无胜算。
来人虽有威压,但是却好似关心地问道:“这厢房可还满意?”
“你到底是谁,叫寒凉过来,我要亲手宰了他。”元婴初期的剑气喷涌而出就朝着陈伯道的脖子削去。
陈伯道却是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捏碎了这记无形剑气。修炼风属性灵力的陈伯道,早在风流方面下过苦功,但凡是一丁点气流的变化都瞒不过他的双眼,若吕洞宾还是凡仙对上陈伯道自然是碾压,但是现下吕洞宾仅仅只有元婴初期的修为,擅长的方面又被陈伯道克制,这会陈伯道才胆敢这番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吕洞宾面前。
“寒凉死了。”陈伯道开门见山地说道,低沉的语气让吕洞宾原本的愤怒平复了一点。
“他怎么死的?”吕洞宾追问道。原本愤怒的脸上一下子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不可思议地神态。
“我杀的。”陈伯道的声音跟他的灵力一样低沉中带着寒意。
“你杀的?”
“是。”没有多余地追问,来人既然从寒凉地手上将他救下,又将寒凉给杀死,自然对他没有敌意。
“死得好,死得好啊!!”吕洞宾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几岁一般,像个小孩子一样鼓着掌,眼泪却又从他的眼睛里一列一列地流出,哽咽地声音里丝毫没有复仇地喜悦,反倒是一种不愿流连尘世地落寞。
“恩公,敢问您尊姓大名。”吕洞宾忧伤了片刻如同一梦方醒一般追问起了陈伯道的名字,身逢此劫,业务怪他一时无礼数。
“陈伯道。你就不想知道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陈伯道早有准备似的反问了一句。
“我昏迷了多久?”吕洞宾问道。
“五天,你死后第二天,六位来路不明的真仙席卷皇都,当日灵力波动仿若天崩地裂一般将七星重楼门前的大街给摧残了好几遍,可惜最后一个都没有再从皇都走出去。”陈伯道无情地回答道。当日自从云房道人进入皇城就被他察觉了,虽然他知道那边气流的异样定是有高手活动,但他也深知枪打出头鸟的道理,故而他装成没事人一般躲在七星重楼地厢房中窥探。
哪知那日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高手活动,没一会就是几股强大地力量在大街上碰撞,平日自认为仙人之下第一人的陈伯道在这几股力量面前却是连窥探都不敢继续了,只是后续听到了重楼内好似有人商议大事一般讲述了当晚的经过。
“他们现在在哪!”吕洞宾突然暴起,死死揪住陈伯道的上衣发了疯似的问道。
陈伯道却是轻轻把吕洞宾给退了回去,“你这态度,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求人问话,最好还是态度放尊重点。”言语间霸气尽出,丝毫不在乎吕洞宾这尊曾经的剑仙。
吕洞宾此刻也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忙赔礼道歉道:“鄙人未有礼节,给您赔礼道歉了,望先生海涵。莫要责怪。”
这会可算是收回了死死揪住陈伯道的双手。陈伯道右手整了整微微变形的上衣,这才缓缓跟吕洞宾说了起来。
“六位真仙据悉都已经被压入死牢,穿了琵琶骨,毁了丹田,修为尽失,秋后便要被问斩。”陈伯道的话语如同石破天惊一般,一道惊雷砸在了吕洞宾的心上。
“要是当日知晴真的出事了,就算我陈伯道豁出去这残躯,将这片天地搅得天翻地覆又如何。”陈伯道在内心里暗暗地想道。俗话说独在异乡为异客。原本世界里打得不死不活地两个生死仇敌却是同样进了这不知名的世界,反而是除了对方再也无人值得倾诉与深交,这番反而挂念担忧起了顾知晴。
他哪知道什么六仙,什么穿琵琶骨毁丹田,只是他隐隐觉得这上古八仙除却已故的圣皇应该是同进同退,除却吕洞宾刚好余下六人,若是数量对上,那便八九不离十了,至于那下落更是他胡编乱造,反倒是顾知晴深夜游荡被关进了大牢做了替死鬼还有些可能,这会他又不再是以往那个神仙以下第一人,跺跺脚都能让人间天翻地覆地陈伯道了,当然只有凡仙境的吕洞宾可以帮得上忙,思索了几天,这才有了这套请君入瓮地说辞。
“这怎么可能?皇城哪有那么高修为的修真者,哥哥姐姐们那么厉害,倾巢而出以后怎么会被一网打呢?”吕洞宾双手抱住了脑袋无助地说着。
陈伯道一见吕洞宾这副模样,连忙再下一记猛药:“你若是去晚了,倒是七仙只余剑仙一人可莫要怪我,人世无常,哪有什么举世无双的修为。”说着竟是转过了身去,仿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般的就要出门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