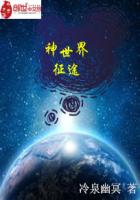太阳的光线从天外一点点渗透进来,更照进似被血雾笼罩的村庄。血腥味一点点被隐藏,他正在逐渐失去嗅觉。那一束束光的丝线顺着他的呼吸封闭了他的鼻子,他知道月亮那个告密者使用了他的权利,除了他没人知道今早的太阳比往日早了许多,这是个只有他知道的秘密,所以它发生了也没法有发生。这是个事实!
天真正亮的时候,他只能转身离开。陆陆续续的有些人家的灯亮了,他必须离开。一个整夜不归的教书先生很容易变成一个叵测的人。他要赶在大家起来前离开,回到村长的院子里,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他或许已经变成一个叵测的人,只因为他在这里个村里游荡了的一夜,并最终站在了这里,更因惧怕他人发现而转身离开。他已经是一个叵测的人了。
床上的人还没有醒,太阳的光已经越过窗棱直接照到了地面上,烫的它的前蹄忍不住来回挪动。在那光之前,它似乎感应到了那人的存在。可怎么可能呢。凌晨,在一天最黑暗的时刻,那个人恰巧就在门外,更令它心绪难忍的是那人并不知道它就在这院墙里面。就竟那人为什么会来?他又知不知道自己就在这里?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信使,那人又怎么会是为了它而来?而它此刻所有想像都是因为他或许今日的凌晨在那里驻足过,原因不明。它此刻现在这样的心绪里无法自拔。一再的否定又一再的鼓躁,持续不断的纠结,更令它的四蹄无法在一个位置久呆。而这样的情绪更不知道何时是个头。
床上的人还没有醒,太阳的光已经将它整个笼罩在内。若是男孩醒了,他定会看见身披黄金铠甲的自己。或许那时,借着男孩将醒未醒的混沌姿态会直接了当的拧断它的脖子。因为那人出现了,它再次披上了那件铠甲。可这铠甲瞬间又脱落了,因为它不确信了。它想它的眼珠应该是琉璃色的,它可以直视着太阳的方向,不同于男孩,它不仅能直视太阳的方向,更能看清那阳光下一丝丝脉络分明的网,那网罩在男孩身上,将男孩整个包围起来。想到这,它心上似乎被什么轻轻拨动了一下,男孩不再是男孩,男孩变成了一个茧,而茧里孕育着男孩的希望,更是太阳的乐趣。男孩将自己整个交出,为了他心中的那个带着浓浓欲望色彩的愿望,兴许那就是希望的样子,而它的颜色一定是红色的,它的颜色绝不会是暖黄色的。因为它看见了,它直视着太阳,看见了它深处的颜色。男孩看见了那暖黄色。所以男孩此刻睡的一片安详,而它,则带着种种不安,在这里,在此刻,险些将足下的土地踏烂。它该怎么办。
床上的人还没醒,它脚下的日光爬过了屋脊,男孩一半在阴影里一般在太阳里。它的眼睛此刻肯定是黑色的,晶莹剔透,有泪水溢出那黑色的双眼。它实在看的太久了,看的太阳也离去了,即便它仍在那里,看的世界也变了,即便它本在那里。男孩似乎真的好梦正酣,自由又何时才能酣睡,而那个人此刻又在哪里坐着什么?它此刻心里的波澜全部归属那个人。
“你怎么在这?“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令它精神为之一振。
“是你?“它有些懊恼的轻轻踏了一脚,刚刚的声音险些吵醒了炕上的那个男孩。这才是最恐怖的。很多时候你看见最后的结果,却不知道半途被惊醒的是什么,是鬼?是仙?鬼有鬼道,仙有仙路,对于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也一样。
“是我,你还没说你怎么会在这里?“蚂蚁似乎执意想要探究这其中的缘由。
“我被那个男孩带过来的。“这一声里的懊恼尤胜先前。
“那你想离开吗?“蚂蚁思索了一阵后说道。
“你能带我离开?“它的马脸透着喜色,眼神里却有些狐疑。
“不能。“蚂蚁的声音很清脆透亮,回答的更是干脆彻底。
“那你问我是什么意思?“它的语气里除了失落还带着一丝不满。
“我只是想知道你还是不是原来的你。“蚂蚁显然并未将对方的神色看在眼里。
“那你证实的怎么样了?“它不承认话里竟带着一丝幽怨。
“你还是原来那个你。“蚂蚁的语气很肯定。
“差一点!“
“嗯?“蚂蚁并不觉得自己猜错了。
“我是说差一点我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了。“它有些抑制不住脸上的笑意。
“那差了哪一点?“蚂蚁此刻很好奇,这是少有的。
“差了今晨那一刻的光。“一副马脸上露出的笑容也许只能用开阔形容,这也是开阔这个词第一次用来形容笑容。
“那一刻的光?那一刻的光又怎么了?“这个人总是带给它惊喜与好奇。
“今晨的光早来了一步,那里站着一个我喜欢的人。“它将这话说出口,便证明它已经信了自己那些胡思乱想,或者它必须信了自己那些胡思乱想。
“那你喜欢的人长得什么模样?或者谁又是你喜欢的人?“它总觉得这样问并不准确,考虑再三却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来。
“他自然是独一无二的。“那话里的自豪连它自己也没有发现。
“所有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知道对方会认同它的想法。
“对,所有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他,是处在所有人中间你一眼便看的见的那样的独一无二。“它希望对方能明白它想说的话。因为它还需要对方帮它给那个男人传达信息,一个准确的信息,排除了胡思乱想的信息。
“我不懂。“它更疑惑了。
“是味道,是味道的独一无二。“也许这次对方会懂吧,它有些不确定了。
“味道?怎样的味道算独一无二?“它问的很认真,认真到你会觉得它一辈子似乎都在追寻这个问题,然而这不过是临时起意而已。
“唉。。。。。。“这要怎么解释?
“你也不知道?“它觉得这个人应该是知道的才对。
“我知道是知道,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说该怎么你才能懂。“想到这它忍不住再次哀叹,它们的距离太远了。
“也许这才是你我之间的距离!“它的叹息沉的浮不在半空被更多人听到,只能顺着重力落了地。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眼前的并不是那大多数人。
“你也是这么想的?“它不曾想它们会有共鸣。
“也?你也这么想?“它更是诧异的。
“啊!如今我知道怎么让你分辨味道了。“它不由的打了个响鼻,不过却谨慎的控制着音量。炕上的男孩时刻令它警惕。
“什么?“对方的话转的太快,令它那一根弦的神经打了个结。
“我说我知道怎么让你分辨那个味道了。“这次它的声音都忍不住提高了一些,当然它仍是克制的。
“哦!怎么分辨?“它知道这时并不是纠结的时候。因着那瞬间的共鸣,它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它。当然这也是它的临时起意,虽然在前不久它还是个想看戏的看客。这时它又不得不想,兴许上次它便已经是局中人了,只是它自己不自知而已。
“你见了他便咬他一口,如果他的血是甜的是温热的是让你感受到蓬勃生机的,那就是他,错不了,那就一定是他。“它可以很肯定的告诉所有人,那人的血就是甜的温热的企鹅生命力旺盛的。
“那,那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它虽然这样问着,可是心里却在想难道所有人都要它咬上一口吗?
“你告诉他我在这,我在这个男孩家徒四壁的房子里。“这句话它想说了那么久,如今终于有一个人可以讲这句话带出去了,带给那个男人。
“他是那个村长家的教书先生?“不知为何听到这里它竟然想起了那天看到的那人。如果是他那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即便只是看着它也是相信的。不过如果有机会它仍是会咬上一口,它要尝尝那甜味,感受那温热,更要体味一下生命的蓬勃,这些都是它从没感受过的。
“你,你知道他?对的,对,就是他。啊,你见过他的,我怎么忘了你见过他?“它竟有些语无伦次了,甚至连声音拔高了都没有注意到。
“就只有那一句话?“它并不喜欢对方此刻像个傻小子似的模样。
“对,就这一句,就这一句他就懂该怎么做了。“如果他不懂,或者他不来,那些便不是它能看掌控的了。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它有些忐忑,不知道该不该问出口。
“你问。“上次是交易,这次也是交易吗?它不太喜欢,很不喜欢,在那一刻的共鸣之后。
“你为什么也会那样想?你还没有回答我。“它终于还是问出了口。
“什么那样想?“它承认人在陷入自我意识时对于周遭发生的事物所给予的回馈要慢上几拍。可不能否认的是它很开心,是它小人之心了。
“你知道的。“它看着对方明显一愣,眼神里散发出来的光如此耀眼,那是它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它,它整个身体,包括它整个一生,都不曾拥有如此耀眼的时刻。此刻那份久违的嫉妒再次啃噬着它那更佳瘦小的心,可它甘之如饴,只因那光照在它的身上时的暖意,而迥异于太阳炙烤般的酷热。
“我知道,可我似乎也并不知道。“它又陷入了无法诉说的囧况。
“不知道吗?“语气里掩饰不住的失望。
“那你知道吗?“它是诚恳的,及其认真的在问。
“知道。“它鲜少如此坚定的回答任何问题的,可这一刻这是它唯一能给出的问题,它的心就是这样说的。当它这样说出口的时候,它觉得自己心里亮了一束光,一束还很弱却散发着不灭亮度的光。
“我也是知道的,可我不是道怎么说给你听。“它由衷的说着自己的心事。
“我知道!因为在回答你之前有那么一刻我也是这样的。“它其实要承认自己也是存在一瞬间的犹豫的。
“那如今呢?“它期待着对方的回答能给自己一些启示。
“因为你我存在的世界差的太远了。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天差地别,当我们同时看一件事物的时候角度不同,看到的事物也不同,最不同的是这件事在我们思想上所诱发的深度。大概是这个样子。“它努力用不甚连贯的甚至存在语言逻辑错误饿话语来表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它要将这想法完完全全摊给它,让它看的透彻。
“我,我似乎也是这样想的,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哈哈哈!“它很开心,对方的描述在它心里掀起波澜,席卷着它的思绪,更冲击着它笨拙的唇舌。
“你也是这样想的?“它拔高了声音道。它要承认,它也很开心。
“喂,我们这样有缘,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它迫切的知道对方的名字,更想永远记得对方的名字,似乎有什么在催促它,还是什么在引导它。
“我也不知道你的!“它似乎并不像对方那样迫切,可它知道告诉对方名字和知道对方名字两项里似乎前者更吸引它。
“我。。。。。。我叫小白。“它的语气有些低落。
“这真的是你自己的名字?“怎么会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时却如此游移呢?连卑微如它也从不会这样念着自己的名字。
“他是这样叫我,我从来没有名字,他叫我小白,可还有另外一个小白。“它第一次将这件事说出口的此刻才意识到自己对这件事的介意。
“对方和你一样对他很重要?“两个小白是因为没办法区分吧!
“还可以是这样?“它从来不层换过角度来想,那果然是自己看不到的角度。
“嗯!我觉得是的!“它是真的这样觉得,因为它不仅认识眼前的它,更认识那个男人。
“我很开心,谢谢你!“它的谢谢很郑重!
“不,不用谢谢!我更应该谢谢你!“这是它第一次听见如此郑重的谢谢,落在心上沉甸甸的,那是一种令人舒服的重量,不像以前那样轻飘飘的,轻的它整个身体都空了,轻的它整个思想也都空了。
“那,我们就都不要说谢谢了,怎么样?“它的马脸配合着微笑竟也显出一丝所谓的浓情蜜意的感觉来。这真是一个奇迹!
“嗯,不需要谢谢!“此刻它突然觉得自己仍旧是那个自己,它永远到不了对方的高度,它仍旧站在那山脚下仰望,它还是那个卑微的自己。它空了的身体,空了的思想在一瞬间又充实了,然后便落在了熟悉的那篇土地上,可它知道此刻的它仍旧与过往的它不同了,它是它又不是它,此刻它看见的世界比以前的大又比以前的小。一个人若是只有自己它的世界便会很小,而一个人在承认了自己无能之后世界变会豁然开朗。它突然有些急迫的想要离开,好好看一看这世界,想来会比过去有趣的很。
“你要离开了吗?“它知道这是明知故问,它在一瞬间感受到了对方身上的变化和那种想要离开的急切,它之所以会问出口是因为不过一夜的光景它便感到了寂寞,它有些舍不得这唯一认识的朋友离开,对,它们此刻应该算是朋友了。
“嗯!“它一时竟不知道怎样道离别,曾经别人不曾和它道离别,如今它仍旧不擅长道离别,将来也不会变的。
“那,一路保重!“这样说是对的吧,它想,因为那些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一定会将消息带给那人的。“它嗫嚅了良久,终于憋出了一句话。
“不,与那无关!“它是真心的且纯粹的希望对方能好而已。
“什么?哦,不,我,我知道!“它有些语无伦次,不过它知道对方会懂的。有些话懂不懂或许与那些话本身无关,而与那个倾听的人有关。
“那,很好啊!“它又用那样一张脸露出了微笑,竟也奇异的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让周围空气也恍惚失去了先前暗潮汹涌的不安感。
“那,我要离开了!“它终于将离开说出了口,话落的瞬间就变成了事实似的,压在它心上沉甸甸的。
“好!“离别的最后又该说些什么呢,保重已经说过了,旁的它又一时想不起,它们都不是擅于离别的人,它离别的少,而对方则离别的太多。
这一次蚂蚁没有再说任何话,因为它知道自己无话可说,更知道再说便不好离开了,冲动过后总是不停的退缩。
它也没有在说什么,因为它知道自己太过寂寞了,它想对方离开替它将消息传给男人,可它又想对方能留下来,留下来再陪陪它,它们在说说话,再,再怎样呢,或许再静悄悄的相对语言也是好的。
那蚂蚁真的很渺小,可因为它走的极慢,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能看到它的背影,很坚定,与上次它们分别时迥然不同。它不由得猜测着,是因为自己的委托吗,它将这看的很重吧,也或者它对外面的世界看法不同了,它真的有些好奇,为什么呢,它想也许是因为它此刻无事可做,也或许是因为它此刻想让自己无事可做。它唯一清楚的便是它如今只剩下自己了,这是一个不需要它看见却又毋庸置疑的真实存在的它自己,在矛盾的中心地带遭受着拉扯的它自己。
蚂蚁能感受到背后那炙热的视线,与太阳的光截然不同,那是带着深切期盼的目光,而非戏虐的观赏的甚或无情又鄙夷的目光。它不知道对方是想让自己快些走,好早些将对方所在的位置告诉那个男人,又或是对方希望它慢些走,这样它也还不算离开。可它知道,无论是哪一种,它也只能快些再快些。在这里在这一刻转个弯就好了,对方就再也看不见它了,转个弯就好了,自己也就真的能看一看这世界了。它不停的对自己说就在这里转个弯吧,转了便万事大吉了。
等蚂蚁终于离开了男孩家的屋子时外面已经黑了,因着月亮的光华,这天虽黑了却仍旧泛着些微的光。这夜的月很亮,这夜的风很大。这夜的月比以往都亮,这夜的风比以往都大。这世界已不是它认识的世界了。
蚂蚁是黑色的,是黑且渺小的。这夜的月亮照在它的身体上,它爬过的足迹一览无余。它从未感觉到这样大的风过,因为它太渺小了。你要知道有时越大的风越与渺小的东西无关。可今夜的风那样不同。它第一次感觉自己竟同时失去对那几只脚的控制力,它们在试图一点点离开地面,随着风不知道被吹到哪去。它知道肯定不是男人在的地方,更不是任何它想去的地方。它们不会恰巧令它如愿的。你说如果是呢?如果是,那不过是戏还没有完,它们还没有尽兴。
月仍旧照着它的足迹,风还未把它吹起,它仍旧艰难的前行。地上扬起的尘土刮的它只能艰涩的将双眼微眯成缝,不仅是眼睛,它的整个身体都处在这艰涩中,它的脑子都不能幸免。它甚至在想,若是它死了,它有没有灵魂,它的灵魂是不是可以将那消息传递出去,那个男人又能不能听懂一个灵魂说的话。它觉得那男人一定能,因为灵魂只与灵魂才能对话,它知道那个男人肯定能。
天黑了又亮了,月亮隐没在太阳的辉光里,风依旧猛烈的吹袭者,不禁没有半点减弱,甚至能看见它肆虐时空中那黑色的朦胧身影。天亮后它反而不易被看见了,因为太亮了,而它又太渺小了。
一片树叶落在它的头顶,它艰难的爬出了那片阴影。突来的光迷了它的眼,比风沙更令它不舒服。它有些分不清方向,不得不耽误更多的时间在这上,等它重新找到方向时已不知过了多久。
第二篇树叶在不远处相继落下,又是恰好落在它的身上。之后便是三片/四片/五片。。。。。。无数片,它走过的路成了一片绿茵场。它知道若是自己足够高,回身望去便能看见自己一路走来的轨迹。
突然一颗树木被连根拔起,想来那是风的英勇事迹,兴许它又可以继续吹嘘,吹嘘它用一颗树砸死了一只蚂蚁。
它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