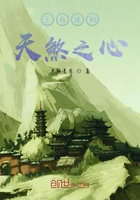小文丧气地回到教室,打开课本想用心学习,可是那些该死的数字似乎也在故意嘲笑她,变着法同她捉迷藏,她实在不会。“难道离开老师我真地就不行吗?”小文实在是很不甘心。但现实又无法改变。她负气地把课本一扔,趴在桌子上痛苦地想着:“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我真的不愿再这样苦熬下去,我何苦受这分子罪?即使回到家中面朝黄天的日子也比现在舒服百倍。何况爸爸已给我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又何忙必这样苦自己?”小文变得更加松松垮垮,而在别人眼里,她只是一位快乐、自在的女孩。
又过了一个月,班主任吴老师找到曲小文说:“曲小文,你的腿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小文知道,他已经对自己的成绩失望到极点,不会再提关于成绩的事了,但他既然问自己的身体肯定是有原因的,但一时也没想到吴老师为什么会这样问自己,便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那就好,一楼的宿舍是不允许让学生住的,因为你特殊的情况,所以让你暂时先住着,既然现在你的腿康复得差不多了,那就搬回原宿舍吧。”吴老师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了,小文因为这一段时间心情差,早把自己住一楼的事给忽略了。”班主任老师这样一说,感觉自己是应该回班里的宿舍了。于是就答应了。
小文从办化公室里回来后,就去了她们班的宿舍,她们班的宿舍在二楼。却没有想到,原来的空床已经没有了,因为进入高三后,班里来了大量的复课生,就把宿舍占满了。如果小文搬回来,只能到四楼去了。而现在虽然她的腿恢复了些,但如果要是爬到四楼,还是非常吃力的。于是她便找到班主任说,班里的宿舍已经没有空床了,她必须搬到四楼去,但她现在来回上下四楼还是非常地吃力。班主任对她很冷淡地说:“曲小文,你在一楼住这么长时间,已经是很特殊的情况了,再说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得经过校领导的同意。”
小文看到班主任的冷淡,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只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她知道,如果这件事找朱博睿解决,肯定要容易得多,但她并没有去找他,还是把自己的东西吃力地搬到了四楼,每天就这样吃力地来回上下四楼。
小文现在住的是混合宿舍,基本上都是复课生。宿舍的东北角空床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位女生。小文一般也不会理会这些事,因为她喜欢独来独往,并不喜欢同陌生人打交道。她当然也不会理会那个多出的女孩。只是有一天晚上小文才知道她在朱博睿任课的班里复课,而且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
一天晚上,小文回到宿舍拿出自己的日记。小文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深深的低谷,谁也不会再理睬她,而且处于高三的冲刺阶段,同学们都在拼着命地学习,为明年的冲刺做准备,也只有她是个“闲人”,天天就这样不急不躁,只知道玩,没有一点压力。可是她是多么伤心啊,可是谁又能理解自己呢?她除了写点日记向自己诉诉苦,还有什么办法。
一天下了晚自习后,小文看着自己的日记,正伤心着,听着她对面下铺的同学对上铺的同学说:“小丽,麻烦你把这道题给我解一下。”说着她把题递给了上铺的同学。上铺女孩接了过去,看了几眼,毫不费劲地做了出来。
“你还真行。”下铺的女孩佩服地说。
“那当然了,名师出高徒嘛,有这么一位出色的老师作向导,我再愚笨,那不太对不起老师的威名吗?”说着得意洋洋地看了小文一眼。
小文与这位女孩并不熟,她不明白这个女孩为什么非要瞪她一眼,继续看自己的日记。但不知为什么,她竟对她们的话会那么在意。
“噢,我知道了,你们班的数学任课老师是朱主任。以前我总认为他是学校的领导不任课,没想到你们这么有福气,摊上了一位领导任课。看来他的课教得很不错吧。”下铺女孩说。
听到‘朱主任’,小文的心仿似被扎了一下,更关注她们两个的谈话。
“当然啦,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那位女孩说着爱慕显于形色。
小文看了心里酸溜溜的,忙把头埋得很深,装作什么也没另有听见。那位女孩继续喜形于色地说:“他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好哥哥。我经常去请教他,真是太佩服朱哥的智慧了。”她说着,眼中不自觉地闪出钦佩,爱慕越来越重。小文越听越觉得心酸楚楚的。
“你怎么可以喊他哥?”下铺女孩好奇地问。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看他是领导,很平易近人。他愿听,我愿喊,那又怎么样?”上铺女孩毫不示弱地说。
“他乐意听?这是真的吗?”小文的心里充满了茫然。
“你们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下铺的女孩说。
“才不是呢,我到这所学校来复课,没通过任何关系,是我自己找来的。朱哥很欣赏我的勇气和志气,非常热情地帮助我,省了我许多手续,并减免了部分学杂费,还把我安排到他任课的班级,我太幸运了。”她说着又得意洋洋地瞟了小文一眼。
小文的心已变得惨白了,她一遍遍地问自己“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做?是我让他太失望了,没能做到名师出高徒?可是老师您知道吗?让我听这些话,真是生不如死啊。”
下铺女孩似乎被上铺女孩朱哥朱哥喊得不耐烦了,抬起头来冲她喊道:“别整天朱哥朱哥地喊,真是酸死了。”
“那又怎样?我就是乐意。”上铺的女孩蛮不在乎地说。并又故意瞟了小文一眼。小文看到她得意的眼神,顿然升起了一股愤怒,也瞅了她一眼,再也不想听她们讲下去。赌气把日记扔到一边,用被子蒙住了头。
“她会喊老师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小文眼前一片漆黑,心也空荡荡的。她想哭,却不知为哪般。“老师您不知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吗?怎么可以容许学生喊您哥呢?我听着都肉麻啊!您知道林黛玉为什么听到贾宝玉和薛宝钗成亲后拼命地折磨自己?一个人赖以支撑的支柱都倒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您真的忍心看着我走林黛玉的路?”小文的意志被催垮了,一晚上她无法入睡。痛苦地折磨自己。她瞪大眼睛,想在这漆黑的夜里看清楚一切,可是一切又是那么茫然。
第二天,小文赖在床上不愿起身。直到快上课了,她才无精打采地从床上起来,简简单单地洗了脸,向教室走去。
走在路上,小文碰到了高一时的同学程冰,她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分班后,程冰分到了理科班,朱博睿担任她的任课老师。虽然分班后她们的交往少了,但见了面还是很亲热。她们边走边谈,不自觉地扯到了朱博睿的身上。
说到朱博睿,程冰的神色变得很黯淡了。她失望地说:“高一时,朱老师在咱们同学中的形象多么好,他平易近人,同情弱者。可是从高二到现在,他越来越让人失望。作为一位学校的领导,他以权谋私,尤其在收容复课生问题上,做了许多手脚。他把复课生都集中到我们班,我们班的同学都对他有很大的意见,许多同学都在背后偷偷地骂他,说他很多坏话。”
程冰还有意无意地提到了朱博睿和那位女孩的事情。小文听着,每一句话都像石头砸她的心。她不愿听下去,程冰说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是感到心里压了太沉重的悲苦。她真想此刻是一颗鞭炮,痛痛快快地引燃,爆炸得无影无踪。也就没有烦心的事了。
程冰看到小文的神态不对劲,害怕地问小文说:“小文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小文微微笑了笑说:“没什么,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总打不起精神来。”
程冰忽然意识到她不该和小文讲这些话,毕竟她在高一时也了解小文和朱博睿之间的关系。小文又是很敏感的,她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刺激到小文,怜悯地说:“你怎么这么不好好地珍惜自己?回去照照镜子,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知道你很要强,总把痛苦放在心里,你可不能再这般地折磨自己了。”
小文笑了笑说:“没事的,好好休息就会好了。”
她们边说看边去了各自己的教室。走进教室,小文趴在桌子上再也没心思学习了。身体的痛苦,精神的松懈已变成了两根毒蛇,无情地吞噬着她的一切。即使她不求死,但只要老师看到她这样一位不争气的学生,一气之下开除她,那也是小文求之不得的。她还真想本本分分地做一名农家女,或一位平凡的工人。
小文趴在桌子上已三天没做任何事了,她开始感到烦躁不安。也许天性的坚毅不允许她这般做,但强烈的逆反又使劲地压抑她的不安。可越这样,不安的情绪就越重。她不禁冲动地拿起课本,但不久又赌气地扔到一边。趴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