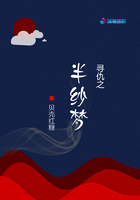何路通见状,哼哼笑了两声道:“美人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不过是晚课倦了,过来走走。”伸个懒腰,从院墙上跳了下来,轻轻落在地上,眯着眼睛走到凝烟面前。
这边地牢里,完颜翎和断楼也已经听到了何路通的声音,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凝烟轻声道:“副掌门。”低头拾起饭盒就要走,何路通一把按住道:“急什么,这饭盒好生精致,我来看看你送的是什么饭食。”说着便伸手打开饭盒,只见里面两个空盘、三个空碗,旁边的木桶里都没有,只几枚吃剩的鸡骨头。
何路通看见凝烟提着饭盒入内,还以为她送了什么好东西,成心要找些把柄,可是这七天七夜里断楼昏迷不醒,只能勉强进些流食,这一醒来自然是胃口大开,凝烟手艺又好,送的饭食吃的是一点也不剩。他拈着两根手指翻了半天,却连一粒粘在木桶上的饭粒都找不到,只得悻悻作罢道:“这个小娘们,还挺能吃。”随手一甩,将饭盒的盖子丢在了一边。
完颜翎听着他说话,暗想:“这何路通也真是蠢货,我一个人怎么能吃得了这么多。不过也幸好他不聪明,要是让他知道断楼醒了,不知道又要有什么麻烦呢。”
凝烟捡起饭盒盖子,对着何路通微微一屈膝道:“副掌门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告辞了。”正要转身离开,何路通却道:“等等。”走到凝烟面前,似笑非笑地伸出手道:“眼下夜深人静,可不能辜负这大好月色啊。”凝烟并不说话,只是向后退了两步,冷冷地看着何路通。
何路通被凝烟的眼神看得十分不悦,哼一声道:“不过是个贱人生的烟花女子,跟我在这里装什么清高!别人碰得,我堂堂嵩山派副掌门就碰不得吗?”
凝烟全身都颤抖了起来,咬牙道:“何副掌门,你要自重!”
何路通哼一声,手里铁球啪的一攥道:“自重?今天我还就不自重了!烟花柳巷我去过不少,你这样的也不是头一个!”说着腾得一指点住凝烟肩头穴道,凝烟身子一软,两手的饭盒和木桶都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何路通一脸淫笑地走了上去,正要将凝烟抱起,突然地牢里传来断楼厉声吼道:“何路通,住手!”
何路通一惊,手里停了下来,暗想这小子居然还能醒过来,却哪里知道是凝烟偷偷送去了汤药。他这一愣神,只听嗤的一声细响,一粒小石子从地牢天窗中飞出,打中凝烟肩头,解开了穴道。凝烟身体一软跌坐在了地上,想要逃开,却又担心断楼和完颜翎的安危。
何路通走到天窗边,向里面道:“臭小子,我还以为你一动不动变成了僵尸,没想到不但醒了,而且还恢复了功力,真是小看你了。”
断楼的功力实际上并未恢复,但是刚刚已经掌握了内功出招的法门,这不过几丈的距离,用盈虚洞天指徐徐发力,解开穴道倒也不是难事。不过听何路通这样一说,便顺着他道:“区区三招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胸中提息,声音朗朗送出,显得中气十足。完颜翎在一旁道:“臭矮子,不许你再为难凝烟姐姐,不然我们跟你没完。”
何路通听断楼说话的声音,似乎比七日前交手时更加精力充沛,倒是有些忌惮,心想难道赵掌门那三招竟恰恰打通了他的什么重大经脉关节,使得他内功不降反升?这种事情虽然极为罕见,但江湖之大,也不是没发生过,再加上刚才他那一指隔空打穴,何路通对与断楼的话倒是信了七八分。
心中虽然这么想,但他一向自恃身份高贵,岂肯嘴上服软?便冷笑一声道:“我为不为难这个侍女,是我自己的事情,关你何事?”完颜翎道:“是不关我事,但算着日子,赵掌门闭关也该出来了,他老人家眼里可是揉不得沙子,我要是把你今晚所作所为这么一说,你这副掌门的位子恐怕也保不住了吧?”
完颜翎这七天来照料断楼,和凝烟闲来无事便会聊些派中趣事,知道赵怀远是极为正派的人物,何路通却是个风流好色之徒,而且专找个子高挑的女子,派中女弟子和侍女多受其扰,只是慑于他的武功地位,敢怒不敢言。而且,何路通素来以替嵩山扬威为名行走江湖,常年在外竟挣下不少好名声,因此赵怀远对于他这等龌龊之事竟是一概不知。
何路通对于此等威胁不以为意,笑道:“你说了又能怎样,掌门是信我还是信你?更何况我堂堂嵩山副掌门,就是直接向掌门要这个女子,他也不会不给我。”
再聪明的人也对付不了不要脸的人,完颜翎气急败坏,却是毫无办法,只是口中道:“你……你……”。何路通得意道:“我什么我?有本事你出来杀了我啊。只可惜这牢门乃是玄铁铸成,你和那个臭小子功力再高,也出不来,更杀不了我!”说罢哈哈狂笑。
断楼听着他的笑声,冷冷道:“我是杀不了你,可是我能杀得了我自己!”
这话一出,几人都是一惊,何路通有些不明白,问道:“什么?”断楼道:“我可是听说,赵掌门的要求是我们两人既不能跑,也不能死,这样万一有一天我大金发兵来攻,可以做个筹码。要是我现在就死了,你还能交差吗?”
何路通微一沉吟,开口道:“看管你们,原本就不是我所管之事,就是死了也该问责程斐那老头,与我何干?”断楼道:“何副掌门,人死之前总有最后一把力气吧,我要是临死之前,把手指头砍断,再在墙上写上‘何路通杀我’五个字。你记恨翎儿咬你手指,此事谁人不知?如此一来,你猜赵掌门他会不会信?”
何路通脸色一变,手指隐隐作痛,向着天窗里指着道:“断楼,你小子少在这里威胁我,我就不信,你还能为了这样一个女子,赔上自己的性命?”
话音刚落,只听地牢里“咚”的一声响,像是什么钝物狠狠地撞在了墙上,接着便是完颜翎的惊呼。何路通大惊,这小子要是一头撞死了,再写个什么血书,自己这关系就真的撇不清了。回头吼道:“快开门!”
凝烟也是吓了一跳,担心断楼的生死,哪里还用何路通催?急忙上前,从怀里拿出那枚窄木条插在铁门上,又将旁边的一块砖头按了一下,铁门隆隆打开,何路通掩着鼻子,急急忙忙地走了下去。
今晚正是月圆之夜,月光透过天窗将整个小室照得极为明亮。何路通和凝烟进去一看,只见断楼满脸血污地躺在完颜翎怀里,墙上一大片血水,滴滴地沿着墙面向下流淌,完颜翎哭着用衣襟擦拭他的额头,整张脸在月色下显得惨白。
凝烟顿时泪如雨下,扑上前去连连唤道:“断楼公子?断楼公子!”几声之后,断楼悠悠转醒,对着她和完颜翎点点头,目光直盯着何路通。何路通背着手,脸色阴沉道:“好小子,算你狠!”断楼勉力撑起身子道:“以后,还得让凝烟姐给我们送饭,你不许干涉,不然的话……”何路通狠狠地甩甩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断楼看着何路通离开的背影,听见哐当一声门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书院,忍痛道:“哼,这笔账先给他记下,早晚有一天,我也要在他脑袋上狠狠敲一下!”
凝烟仍是止不住地流泪,抽噎道:“断楼公子,你何必为我如此……”断楼笑道:“要不是凝烟姐多日以来的照顾,我只怕此时还是一个醒不过来的废人。那何路通狡诈阴险,不给他见点血,他也不能相信啊。”
完颜翎见他如此,甚是不忍,嘴里只是道:“傻瓜,大傻瓜!”伸手扯下一块裙摆,细细地为断楼包扎伤口,忍着泪水道:“凝烟姐姐你放心,从今以后那个臭矮子绝对不敢再难为你了,天色晚了,你快回去吧。”
凝烟嘴唇微颤,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便深深地低了下头,回身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从天窗外丢进来一个小陶瓶,瓶身上写着“花宫散”三字,却是没人进来。
接下来几天,何路通果然再也没有来过。凝烟依旧每天送饭送水,可每次都是一句话不说,只是进来将饭盒放下,而后便走了出去。两人吃完时候,她再默默地进来取走碗筷饭盒,任完颜翎和断楼怎么讲笑话、做鬼脸,她都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两人都是心思细腻之人,凝烟的心思,他们自然也是明白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断楼为了能尽快逃出去,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坐练功。好在他练过了一段时间的盈虚洞天指,虽然当时不通法门,只会硬逼内功,却为他现在练习将丹田放空、四下分布内力打下了基础。完颜翎内功稍浅,便从入门开始,每天两人就这么打坐调息,也无人打扰,竟是进步神速如此便又过了几日。
却说何路通,他虽然因为害怕断楼自尽给自己惹上麻烦而罢手,心中到底十分不痛快,逮住机会就要训斥凝烟一番,凝烟却比平日更加沉默,一句话也不还口,等何路通骂完了、骂累了,她就行个礼离开,让何路通气急败坏。
这一日,何路通正在大堂中整理服饰,打算一会儿去跟门下弟子交代些事情。赵怀远父子明日就要出关,届时少不了要检阅一番。自己代管门派这些时日,可不能让说出什么不是。
他正要出门,一个小厮来报,拱手道:“副掌门,外面一个僧人求见,说是来替他师伯来问些事情。”何路通皱皱眉头道:“僧人?还替他师伯来问事情?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僧人什么样子?”小厮道:“长相小的没看清,但是挺年轻的,穿得破破烂烂,像是个苦行僧。”
“苦行僧?”何路通更加奇怪,想了想摆手道:“说不定是哪里来的讨饭游方和尚,你们给两个钱打发走便是了。”小厮道:“小的正是想打发他走,可是他说一定要完成师父交代的事情,说什么都不肯走。小的无奈,这才来禀报。”
何路通怒道:“笑话,一个和尚,就敢在我嵩山派门口耍赖撒泼吗?我去看看!”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回身坐在大堂椅子上道:“算了,你去,让他进来。”
小厮诺了一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一个清瘦的灰衣僧人走了进来。何路通看看他,只见这个年轻和尚约摸不到三十岁,长身玉立,剑眉轩目,只是眼中全无光彩,让一张原本俊秀的脸全是愁苦之相,何路通看得也浑身不自在。
这僧人站上大堂,双手合十,问施主安好。何路通起身拱手还礼道:“这位师父请了,不知师父在何处修行?”僧人道:“小僧不过是一个忏悔一生的人,哪里有什么修行。师父派我来,是想问一下,近日传言,江湖第一邪派血鹰帮阴谋要大肆抓捕女真人,从而搅扰金宋边境,有人说贵派也参与了其中,半个月前引来了一批女真人,其中两个人还被关了起来,不知可有此事?”
何路通脸刷一下子白了,微怒道:“这种事情纯属污蔑,你又是从何而知?”僧人道:“几日前我跟随师伯四处游方,路遇一批女真人。听他们说,是被贵派引到了登封县内,是两个贵人作为交换,他们才被放了回来。师伯以为此实乃不义之举。但嵩山素来是名门正派,不应当与血鹰帮同流合污,因此今日特派弟子来问一下,是否确有其事?”
何路通冷笑道:“好大的口气,听这意思,你是来管教我的?你师伯又是谁?敢管我们嵩山派的家事?”一边说话,一边手里铁球转了起来。僧人不为所动,答道:“师伯法号,忘苦。”
“铛啷啷”两声,何路通手里的铁球掉了下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