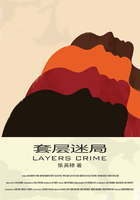在江南一隅,有一座山,名叫乌有山。乌有山得名何时已不可考。只是那山秀丽绚烂,主峰挺拔,高高矗立,嶙峋而上,远远望去,像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宝塔,直冲云霄,似与天际接壤。主山四周又盘亘着八十一座小山,叠峦相连,延延绵绵,起伏万千。那八十一座小山峰又一致朝向主峰,似有万山朝贡、众星拱月之势,巍峨壮观,却是奇异。
乌有山另有一妙处,若是夏天,风和日丽,每天清晨,山峰上紫雾缭绕,氲氤腾漫,笼罩着半个山腰,恍如仙境一般。传说,古代一个大旅行家游于此地,驻足眺望,为眼前奇异景象所迷,流连忘返,竟不知归路。后人为纪念这位大旅行家,特地在山脚下塑一石像,迄今还在。
据当地的老人讲,这山上出现紫气,是因为这山有灵气。相传上古时期,舜帝巡狩于此,不幸身亡。娥皇、女英两位妃子追随而来,闻此噩耗,伤心欲绝,哭泣不已,日积月累,那掉在竹子上的泪珠日久结痂,斑斑驳驳,以后长出的竹子也是如此,后人为纪念两位妃子又称此竹为“湘妃竹”。
由于乌有山地处荒僻,树木葱翠,旧时又常有凶禽猛兽出没,所以一直以来人烟稀少。后来那些野兽被人大肆捕杀,逐渐减少,直至绝迹。人们贪恋这里的天然秀色,来这里居住的人也多起来。当地的人又大力发展旅游业,本来秀丽怡人的自然景致,加上人力的斧斫细雕,又有良工巧匠精心打造的几处建筑,更是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巧夺天工,与那自然风光浑然天成,旖旎夺目。远近的游客慕其名,接踵而来,络绎不绝。
乌有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村庄,叫子虚村。据地方志载,子虚村起源于明朝末年。那时连年战乱,烽火不息,税赋深重,百姓苦不堪言。为躲避战乱与税赋,百姓到处流浪,他们或三五人,或五七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见这里有荒可垦,有地可种,便安定下来。几百年后,已繁衍成一个有数千人的大村庄。
由于子虚村的人都是四方迁徙而来,姓氏盘杂,有十几姓。张姓是村里人口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支。仗着道路带来的方便,张德贵就在离城不远的郊外开了一家卷烟厂。那卷烟厂有好几十亩地宽,光是请的工人就有几百个。不出几年,张德贵的手头宽松了,日子过得惬意起来,也不忘一方水土,润物育人。张德贵自己拿出钱来,在村前的大河上修了一座丈把宽[2]的桥。村民此后不用再挤渡船,方便很多,心里感谢张德贵慷慨为人,致富恤贫,特地在桥的进村一头为他塑一尊石像,还请当地一位名士题字“德育后人,以和为贵”。
张德贵为村里修桥以后,自己也在村里建了一栋独院别墅,里面假山、亭阁、奇花异草等,应有尽有。张德贵每日饭后闲走,总觉得这院子里还少了一样什么,后经朋友点醒,张德贵才恍然大悟,原来差一条小溪。于是,他忙叫人从村前的河上游开一个口子,掘一条小溪,把河里的水引进院子里。院子两头用铁网拦住,放了鱼,架上桥。每到烈日炎炎的夏天,趿[3]着鞋,端张小板凳,坐在溪边的树荫下,垂着钓,吸着烟,饧[4]着眼,看着淙淙流过的溪水,张德贵心里总会漾起一丝自得:想我这一生总算对得起列祖列宗,没有丢他们的脸,反给他们增了许多光。子虚村几百年来,恐怕还没有第二个在四十几岁就挣得这份丰厚家业的。如今这份家业别说自己这一世花不完,就是留给儿子、孙子,他们也不见得能花完。想到这里,张德贵又顿时刹住笑容,泛起一丝哀愁,轻叹一声气,自言自语说道:“要是秋生那小子长半点劲儿,争半口气,我这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
张德贵正在喃喃自语,不远处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红色短裙,上身裹着一块蓝色轻薄纱衣,趿着鞋,正慢慢地走过来。张德贵两眼望着小溪,正在胡思乱想,不曾注意有人走近。那女人走到张德贵后面,一只手轻轻按在他肩上。张德贵转过头来,见女人惺忪着眼,似是刚睡醒的样子,微微一笑,说:“婆娘,你来啦?”那女人轻轻一笑,说:“刚睡醒,出来走走,却见你在这钓鱼。刚才见你望着水面的样子,又见你这张苦脸,想你在想什么发愁的事?”
张德贵望着女人那张略显疲惫的脸,多少思绪涌上心头:想当初,自己还是个穷酸的小后生,婆娘不顾家人反对与劝阻,坚决要嫁自己。结婚以来,日子艰苦,却也相濡以沬。多少年来,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始终不离不弃,如今挣下这万贯家财,女人昔日的娇媚与容颜早已逝去,岁月的痕迹已悄悄袭上来。张德贵感到一阵酸楚,又有一阵欣慰于怀,轻轻笑了笑,说:“秋生这小子这些天没见他人,也不晓得去哪儿了?”张德贵婆娘说:“不提这小子还好,一提起来我就气。这几天连他个魂儿也没见着,整天跟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外头瞎混,晓得的人倒不说什么,不晓得的定会说这小子没老子,没娘,没人管教。”张德贵又叹了口气说:“子不类父,也怪我当初疏于管教,才纵得他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我的错。”张德贵婆娘说:“你也别太自责,我看别个家的孩子也没怎么管教,不是好好的,哪里像他这般样子。前些天我托林家嫂嫂帮我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子家,想给他讨个亲[5],管束他一些,收收他的性儿也好。”张德贵点点头说:“这个主意倒不错,横竖[6]是要讨的,早些讨回来也好。”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刚才说的林家嫂嫂是哪个?”张德贵婆娘说:“你怎么就忘了,几年前,咱们还住那土屋的时候,她还来串过门,我们托她办了好多事情呢?”张德贵略一深思,哈哈笑起来,说:“就是这婆娘,有意思得很,说话又有趣,只是好些年没见她过来走走。哪天你有空请她过来坐坐。”张德贵婆娘说:“可不是,那天我去她家跟她说秋生的事,问她这些年怎么就不过来坐坐,吃口茶,谈谈白话[7]也好。她却说,‘我们这些人的鞋儿是泥、祙儿是汗,进来一站脏了你的地儿,矮身一坐又污了你的桌儿、凳儿。身上的灰尘被风一吹,也够你忙上半天,哪里还好意思去。’我说,‘嫂子你太见外了,当初你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如今上门来坐坐,又有什么要紧,还怕少了你酒饭不成?’她笑了笑说,‘既是张家嫂子这般说,哪天我有信儿上门复你就是’。我出门还特地叮嘱她好歹过来坐坐,不然就显得生疏了。”张德贵夫妻讲了一会儿话,见日头快要落山,收拾东西回屋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