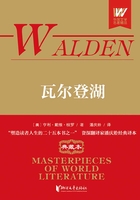刘成章
望不尽似水流年,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但是,我的如同树皮一样粗糙的额头里边,常常闪现着我的一双花蕾般的小脚片子,和那小脚片子上穿的一双老虎鞋。
一切,都是母亲讲给我的。
那是一九三七年春天,像故乡延安的天空掉下一滴普通的雨星,像那山山洼洼冒出一裸寻常的草芽,鸡不叫,狗不咬,我,降生了。我的曾祖父是个泥水匠,祖父是个钉鞋匠,二叔为别人磨面;父亲在当时倒算是有点光亮的人物。当个小学校长,很早就暗地参加了革命,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穷书生、普通的党的支部书记而已。我,就是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我躺在铺着破纱毡的炕上,像一颗刚从泥土里刨出来的洋芋蛋蛋。
转眼满了三十天。家虽穷,按照当时的风俗,“满月”却是要过的。爸爸的工作忙,但在爷爷的催促下,还是请了一天假。在师范上学的三叔也回来了。年仅二十岁的妈妈满怀喜悦,把我抱在怀里,拍着我的光屁股,一阵儿喂奶,一阵儿换尿布。亲不够,疼不够,爱不够。她特意用红纸为我扎了个大红火蛋儿,踮起脚跟,高挂在我仰面望着的上方。这是我眼中的第一颗太阳,妈妈捧给我的太阳。
一家人欢天喜地,锅瓢碰得叮当响,又炖羊肉又炸糕。从我家烟囱冒出去的淡蓝色的青烟。也带着缕缕香气。阵阵笑声浸泡在明丽的阳光里边。外婆,外爷,亲戚四邻,该请的都请了,该来的都来了。他们给我送来不少礼物:小锁锁,小镯镯。槟榔锤锤,花帽帽……他们争着把我从妈妈的奶头上抉过去,搂在怀里,举在面前,啧着舌儿,说着话儿,逗我玩。
虽然在此刻,在我家的这个小天地里,我简直成了一颗小星星;但是放在延安城,放在整个陕北高原,我倒算个什么!我家虽然热闹,算起来,并没有多少人晓得。
然而,就在这一刻,一位妇女,一位一年多前刚刚给毛主席做过鞋的妇女,风尘仆仆,走进门来,又把她亲手做下的一双老虎鞋,给我穿在小脚片儿上。她还送给我一身红花绿叶的小衣衫。
她是谁呢。
你想想那首有名的“东也山,西也山”的陕北民歌吧!你想想那个被无数老革命都尊称为大嫂的人吧!
她,不是别人,而是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同志。我父亲曾在永宁山、在志丹伯伯手下工作过,和志丹伯伯、和她,有着亲密的友谊。我家的热炕头上,曾经多次回荡过志丹伯伯的笑语。我过满月的当儿,志丹伯伯牺牲不久,同妈妈忍着巨大的悲痛,伴着窗前黯淡的麻油灯,一针针,一线线,为我赶做了满月礼物。她本来有眼病,此刻,一双眼睛熬得布满了血丝,红红的。
她抱起我,亲我的小脸蛋,任我把尿水撒在她的衣襟上,给我穿上老虎鞋。这金丝银线绣成的老虎鞋,这照亮我幼小生命的老虎鞋!
老虎鞋是一派保安民间风格,像窗花一样的风格,朴实、粗犷、传神。大红为主,配以金黄,间杂黑、白、紫,色彩热烈鲜明。老虎鞋上带着同妈妈的手温,带着革命母亲对下一代的希冀。
这老虎鞋穿在我的脚上,一屋婆姨女子全都围拢过来,这个摸摸,那个看看,全都惊羡不已。连正炸糕的姑父也挤进了人群。
奶奶急了,忙喊:“看你那油爪子!”姑父知道奶奶的脾性,不敢执拗,端来瓦盆忙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样,才争得了摸一摸的权利。他的憨厚神态,逗得大伙儿都笑了。我的穷家破舍,因为这双老虎鞋,平添了无限喜气。
这老虎鞋穿在我的脚上,一身乳气的我,似乎也感到了,看见了,懂得了,滴溜溜地转着笑亮的小眼珠,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扑扑腾腾地蹬打着胖腿小胳膊,向妈妈,向爸爸,向普天下,宣告着我的骄傲和幸福。因为这双老虎鞋,我一辈子都感到很满足了。
这老虎鞋穿在我的脚上,虎耳高竖,虎须颤动,虎牙闪光,挟带着永宁山的雄风,播扬着永宁山的正气,仿佛只要长啸一声,就能掀起人们的衣襟。我这块只会哭叫的嫩肉疙瘩儿,仿佛立时长大了,威武了;我的一双嫩得像小萝卜一般的小脚片儿,仿佛立时变得能踢能咬了。
这双鞋,饱含着多少深情,给了我多么厚重的祝福啊!
这一刻,我想,不管人们留意没有,延河一定是在歌唱,百鸟一定是在欢舞;历史,应该记下这一笔。自然,这绝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一位不平凡的妇女,因为同妈妈。
我自愧没出息,这辈子没有为人民做出多少贡献,无颜去拜见同妈妈。但我对志丹伯伯和同妈妈的心意,却是深挚的。我曾经以自己笨拙的笔,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了几首歌颂志丹伯伯的诗,就是为了表达这种心意。
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还有一点想法,是为了自勉。我应该时时记起,我的一双脚,是穿过同妈妈亲手做下的老虎鞋的。
那是我此生穿的第一双鞋,山高水长的老虎鞋。我应该在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刷新自己的精神,增添一些勇于革新、勇于进取的虎虎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