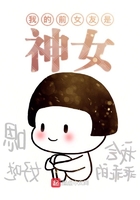道家是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和终极关怀的一个文化流派,它以“道”来统摄自然、社会和人生三大层面,追求三者的自然平衡,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道家文化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我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民情、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先秦道家的文化精神
(一)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今属河南鹿邑)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在周王朝藏书室任职,掌管史册典籍,后离周赴秦,在函谷著成《道德经》(也叫《老子》),后隐居秦国。道是老子宇宙观的核心。他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以上均引自《道德经》)
综合上列论述,老子的道,具有下面三大内涵。
第一,“无”与“有”的统一。道是形而上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它既是万物之所出,又是万物之所归。“无”是无名,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作为万物的本原,它是抽象的,正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道德经·第十一章》)。道还是实存的,正如同树种一样,具备长成大树的潜能。“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道德经·第三十二章》)
道是万物之始,万物之母,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世界万物形成、变化、运动的总规律。
第二,“恒”与“变”的统一。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和总规律,指的是万物之间固有的本质的联系,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质,更不是造物之神,也不是有意识地创造万物。万物的形成完全是自然流变的结果。“道生一”的“一”,是指从混沌中分化出来的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无数个基因胚胎,“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一生二”的“二”,则是指天地阴阳两个方面。“二生三”的“三”是阴阳天地互相作用而形成的冲气,不同的冲气形成不同的具体事物。而万物又是运动变化的,循环往复又互相转化,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四十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
第三,“无为”与“自化”的统一。自然、无为是道的本性,也是天、地、人的本性。自然不是人的主宰者,人也不是自然的掠夺者;人对自然不能任意改变,人对人也不应强制****,而应“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天地人都应自觉恪守自然之道。“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老子把道作为宇宙观的最高范畴,能自觉而严格地区分可道之道与恒道的本质区别,并以道来贯通天、地、人三个层面,表现出对宇宙本质的终极性探寻,开辟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全新道路,具有合理的唯物内核,它打破了人们对天的敬畏,推倒了天的人格神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老子是入世的,又是无为的;是民本的,又是天真的。他这样来表述自己的社会观: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以上均引自《道德经》)
入世并进而治世是老子社会观的目标,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是“法自然”,“以道立天下”,就像烹小鱼一样,不能用大火,更不能多翻动。只有统治者真正做到清静无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老子始终把统治者看成是社会****的真正制造者。因此,只要统治者真正做到无为、好静、无事、不欲,老百姓自然会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然而,统治者一向把老百姓看成不稳定的因素,并制定种种防范措施来规范其行为。对此,老子针锋相对地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统治者用来管制百姓的德、仁、义、礼等种种法令条例道德规范,其实正是他们自己丧失道德仁义的直接结果。老子从根本上指出,人道对天道的违犯在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赋税的沉重,逼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当超过他们的最大包涵力时,必然会“轻死”铤而走险。统治者对此往往采取更加严厉的高压政策,老子警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老百姓到了不惧威压的时候,就是一个王朝覆灭的前兆,千万不可逼得老百姓无处安居,无法生存。可以肯定地说,老子对压迫与反压迫的矛盾的认识非常深刻、非常透彻,在他的社会观中,有比儒家更彻底的民本思想,而且也是他最早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均思想。
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老子为统治者开出的治世良方是“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统治者不应该把自己看成伟大的万物主宰,“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第三十四章》)。必须懂得柔能克刚的道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式的管理要比山式的管理好得多,有时曲线比直线更短些。
不过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却犯了一个幼稚而天真的错误,因为厌恶人欲横流的社会给百姓造成的苦难,因为感慨物质文明的提高给人心带来的创伤,就让社会倒退并永远维持在结绳记事的原始状态,而忘记了大国只需一个指头就可以从地图上抹去无为的小国,使它的寡民沦为奴仆。这是老子社会观的严重缺陷。
(二)庄子
庄子(公元前360?—前280?),名周,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一说在今安徽蒙城)人,与孟子同时,家境贫穷,曾居住陋巷,以织屦为生,任过漆园吏,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现存《庄子》33篇,其中内篇7篇,乃庄周自作,外篇15篇及杂篇11篇,或以为庄周后学所作。
司马迁曾说,庄子“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全面继承了老子的宇宙观,并且在本体论和道与物的关系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这就是说,道是宇宙万物的总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从混沌之前到无限的永远。“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庄子·渔父》)
庄子在老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本体论的方向迈进,明确地指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天大地大,没有道大,阴阳之气中也同样贯通着道。道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宇宙万物,“覆载万物”,“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
同时,庄子还在道之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理”的范畴。理不但是宇宙万物固有的、自然的天理,而且是具体事物本身特有的物性,这显然具有泛道论的色彩,解释了宇宙万物的多样性。而人就可以通过实践和悟性,“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性”。庖丁解牛之所以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就在于他完全把握了牛的内在结构,这就为人体悟规律、运用规律提供了范例。
庄子的社会观与老子基本相同,从根本上主张治国以道。他说: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
古代的帝王圣人之所以入定在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境界,是因为只有帝王做到这一点,社会才能充实安定,人民才能各司其职,各种事物才能按照自然的规律运转,帝王也才会从忧患中解放出来,颐养天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道作为贯穿天、地、人三个层面的根本原则,“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天地》)。只有“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相反,如果“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庄子·胠箧》)。
与此相联系,庄子以为一切人为的法律伦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同道背驰的。他曾猛烈地抨击儒家的仁、义、礼、乐,认为孝悌仁义,忠信贞廉,都是自勉以役其德者的,这些都是限制人的自然天性而役使人的真性的行为,只有对财位名誉一概置之脑后的人,才能达到至贵,使“道不渝”。“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庄子·人间世》)名是相互倾轧的根源,智是相互斗争的工具,都是最可恶的凶器,绝不应该将它们推行于世。帝王圣人垂拱而治,就是顺应了自然之道,符合了人民的意愿。“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马蹄》)至德的上古之世,人民可以保持朴素原始的生活状态,素朴而民性得。
庄子社会观的重要贡献是,他毫不留情地剥离了上层统治者的神圣光环,撕下了他们灵光可鉴的冠冕,还其大盗积贼的本来面目,揭穿了他们评判是非所采用的双重标准。在《胠箧》中,庄子揭露了田成子弑君窃国却自比尧舜的罪行,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小偷小摸被治以严刑峻法,窃国大盗,却被人歌颂。诸侯并不是广行仁义才成为诸侯,而是以最不道德的手段才坐上了诸侯的宝座,于是成了是非的评判者,成了永远有理的仁德之人。
庄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宗法制社会之中,诸侯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断进行着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西周以来沿袭下来的伦理道德又规定着人们的政治和宗法义务。于是,伦理标准成为统治阶级驱使百姓充当战争炮灰的重要工具,这就是传统伦理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庄子为什么排斥否定当时的伦理道德,大力倡导“绝圣弃智”,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在理想社会的构想上,庄子和老子犯了类似的错误,他没有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希望回归到上古的至德之世,让人们再去过古朴原始的生活,与禽兽同居,这是不可能的。
道教是中国本土最重要的宗教。道家的学说为道教提供了理论武器,道教又以特有的宗教形式,演绎、实践、发展着道家的思想和精神,应该说道教是道家学说的一种存在形态,但它又不是道家本身。道教内部的派系复杂纷纭,教义、教规也有区别,同道家的距离也有远有近。要之,养性者最近,炼气者次之,服丹者又次,符箓者稍远。道教是以道家学说为基本理论,吸收民间信仰和各类方术,以成道升仙为目的的宗教。早期道教的代表人物是张陵、张角、张鲁等人。张陵于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在鹤鸣山声称受太上老君之命被封为天师,首创了天师道。陵死,其子衡继之,衡死,张修继之,呼应黄巾起义,被刘焉收编,最后被张陵之孙张鲁杀死并夺了教权,又与四川鬼道联合,立五斗米道。张角在汉灵帝建宁(168—171)年间创建太平道,以黄老之学为号召,以治病为手段,为后来的黄巾起义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
魏晋时,道教在北方继续发展,并流传到江南,形成许多教派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是葛洪、葛玄等。
南北朝是道教发展的成熟时期,北魏的寇谦之和南朝的陆修静、陶弘景改革道教,参照佛教的戒律、科仪和形式,形成足以同佛教抗衡的宫观式道教。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以“佐国扶命”为己任,是典型的上层士族教派。陆修静的灵宝派在整理道书、建立道经体系、制定科戒和斋醮仪式方面有重要贡献。陶弘景的上清派在养生、炼丹、医药和建立道教神仙体系方面成就突出,对后世科技和医学有重要贡献。
唐宋时,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道教得到更大的发展,建立宫观二千余处,在炼养服食和符咒科教方面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内丹理论极其丰富。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马承祯、吴筠、钟离权、陈抟、张君房、张伯端等。
金元时,由于********的加剧,道教也相当活跃。肖抱珍的太一教,刘德仁的大道教,王重阳、马钰、刘处玄、丘处机的全真教,周真公的净明道都是影响较大的教派。特别是全真教势力最大,强调三教合一,性命双修,注重内丹修炼,逐渐成为官方宗教。
明清道教停止发展,教义也没有什么拓展,教团的腐化也日益严重,失去信任,逐渐显示出衰微的趋势。其间比较出名的是张正常、张三丰、王常月等人。
二、道家的理想人格
随着时代的变迁,道家的理想人格也在调整变化,但总的倾向是顺任自然、长生久视、修性养生、超迈逍遥。老子说: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以上均引自《道德经》)
就思维方式而言,老子的人生观是内倾式的。它通过对人欲望的克制,心灵的净化,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此来完成合道的一生。正所谓不识道,不足以成智者;不用道,不足以驰骋人生。
老子崇尚的人生理想是“长生久视”。他相信人生只是一个有限的时间过程,要尽量设法让自己长寿。长生,就是高寿,年龄大视力却好,才是健康的长寿者。而真正的长寿是对道的高度体认,“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得道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得道之人,不是权势显赫的人物,而是“赤子”、“婴儿”类的真人。他们无知、无欲、无为,真正达到“精之至”,“和之至”,处于纯真、朴实、自然的状态,却不被外物所伤害。相反,贪生使气,纵欲使强,看似很壮,却很快会由盛而灭。只有“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才能“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要想达到这样的标准,首先,必须采用自足的生活态度,因为五色、五味、五音等令人心跳的人间享受,其实都是对人的挑逗和蛊惑,应该拒绝物质和精神的诱惑,满足于清淡简朴的生活。不知足是起祸之端,知足者才能常乐。知足才不会招致屈辱,适可而止才不会遇到危险,从而达到长生久视的境界。其次,要学会守气,学会关闭自身的感觉通道,学会心斋坐忘,真正达到忘我、忘他和忘忘的境界。“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道德经·第十章》)这一段话就是让人的精气专守一窍,吐纳运气像婴儿样平和,清除杂念净化心灵,达到一尘不染,无为而治,宁静柔弱,明白事理,淡泊自然。还要进一步“塞其兑,闭其门”,封闭切断同外界的联系,甚至“用其光,复归其明”(《道德经·第五十二章》),运用内视返照的办法来修炼。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五章中曾形象描绘了悟道者的举止风貌和定心自养转入清明的境界。
老子内倾式的人生观追求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浪漫化的人生,可以让人们在紧张纷争的生活中平抑内心的躁动,寻找灵魂的港湾,也可以让人们在逆境挫败中得到精神抚慰和生活的勇气。不过,老子的人生哲学中,那种不求上进、明哲保身的成分是应该批判和警惕的。
庄子的人生观基本上与老子相同,以道为坐标追求清净、自然、无为。所不同的是庄子更强调人的精神超越和绝对自由,以达到与天地精神合而为一的境界,强调养生之道,形成了逍遥人生的独立体系。
庄子认为,要想达到逍遥人生的境界,必须从外内两个方面进行克制和修养。对外的克制就是人对外在于自身的各种欲望的自觉克制,包括物质享受、名誉地位、知识能力和是非观点等不同的内容和层次。
在《天地》中,庄子把“五色乱目”、“五声乱耳”、“五臭薰鼻”、“五味浊口”、“趣舍滑心”看做“生之害”,谁如果追求这些享受,就等于斑鸠关在鸟笼之中,虎豹关在兽舍之中,失去自在和自由,成为物欲的奴隶。庄子借老聃的口说:“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运动、静止、死亡、生存、衰废、兴盛,都出于自然。只有忘掉外物,忘掉自身,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人们应该“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
在《骈拇》中,庄子尖锐地批评追求名利,把名声地位看作是骈拇赘瘤一样的负担。“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为了蝇头微利、蜗角虚名,为了所谓的地位和事业,扭曲了美好的人性,耗损了宝贵的精力,甚至赔上了生命的代价,是不值得的。
庄子认为,人之所以追名逐利,劳心伤神,同知识、智慧、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有知便会区分优劣美丑并求优逐美,这就打破了心的宁静,最终导致国无宁日,人无静时。《应帝王》中倏忽为浑沌开窍,结果导致七日而亡,其寓意就是要人们保持古朴、原始和混沌,放弃对“知”的学习和探讨,因为人生有限,知识无涯,人根本不可能穷尽知识,更不要说知识本身就是天下大乱的深层动因。“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络、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庄子认为,人根本就不应该以是非为念,以生死为忧。“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庄子·达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因此对生命“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庄子·大宗师》)不考虑脚的大小,什么样的鞋子都是合适的;不顾及腰的粗细,什么样的腰带都是恰当的;不以是非为念,心灵便可以得到安适。生与死,就如同白天过了是黑夜,都是极正常的现象。获得是因为适时,丧失也是顺应。能安心适时顺应变化,哀乐也就不会侵入内心,不以生喜,不以死悲,淡然而生,坦然而死,不忧死而乐生,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解脱束缚。
内修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另一个方面。要想真正达到与天地精神合而为一,除了摒弃人生的种种诱惑,排除纷纭世事的干扰,还必须修炼内功,做到坐忘、心斋,达到死而不亡,这是人生近于道的更高档次。
在《大宗师》中,庄子借颜回经历的三个阶段来回答什么是“坐忘”的问题。第一个阶段是“忘仁义”,第二个阶段是“忘礼乐”,第三个阶段是“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这里庄子并不是要求人们真的废掉自己的身体器官,而是要让器官形同虚设,对外界的一切引诱无动于衷,心灵空虚到没有纤芥之尘,同道融合为一。
在《人间世》中,庄子借孔子回答颜回的提问说明了什么是“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就是说,人不应只停留在用感官感知世界的初级阶段,而应用自己的心来理解外部世界,进而用空明的心境容纳世上的一切,真正达到道的自然境界,不以物为念,不以人为念,不以己为念,不以念为念,把人变成道的外化物。
“死而不亡”是庄子人生观的最高目标。“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庄子的死而不亡,并非如后世道教所说的得道成仙,长生不死,而是指一种置红尘生死于度外的生活境界。他认为生死是自然的变化,有生则有死,无生则无死。因此,要想做到死而不亡,首先要做到无生。对于不回避生死问题的人来说,不可能做到无生,而只能做到“外生”,即不以生为念,不以世俗的活法指引人生的行为,从而达到无古无今、不死不生的逍遥境界,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绝对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