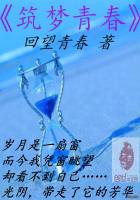祝瑞娟
我一边写字一边听你说话,担心你会觉得我不用心招待你,便不时地抬头对你笑,结果你还是生气了,甩手就走。我憋了一肚子火,跟在你身后不做声。
恰逢李靖,她从没见过我这副神色,问我怎么回事。我开始暴走,故意对着你的背影狂吼了一声:“神经病!”这一喊太过用力,压迫到整个头颅,除了血浆之外的所有液体瞬间都迸了出来,一秒钟的晕眩之后脑袋轰鸣。
李靖跟在我身后不做声,我隐约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声问怎么回事,李靖狂吼了一声“神经病”,再后来接二连三接三连四生生不息的狂吼——“神经病”不断传入我耳膜,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脑袋轰鸣或者是骨裂的声音,除了“神经病”的纯粹狂吼声外,其实挺安静的。
正如你一样,我也不回头看,但我想我们这支队伍一定很壮观了。
夜幕降临,摆夜宵的摊点从星星之火开始燎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归家的必经之路上会出现这么一堵高墙,靠墙立着一顶卖夜宵的伞篷,你手抓伞篷钢架脚踏着墙壁轻松翻过,李靖对我说:“你也可以。”我就试着攀上钢架,果然,伞篷向后倒下。摊贩很及时地冲过来扶稳了伞篷,我顺着伞柄安全滑下,心有余悸地想到自己摔地后的疼痛,机械地拍着屁股上的尘土,等着摊贩来骂我,虽然摊贩已然是个老头,还拄着拐杖,但也一定有力量滚红了脸撑粗了脖子扯嗓门,可他竟然什么都没说。而这时候,我发现我的队伍只有我一个!
一对正在吃夜宵的父子不满地瞟了我几眼,大的掸去裤子上的灰尘后用力揉搓大腿,小的埋头吸面条,我猜应该是我倒下来的时候撞到大的了,趁着他们还没开口骂人,我赶紧开溜,就在溜出他们视线的最后一步,我转身向那个爸爸深深鞠了一躬。
“留下吧,30元。”大的终于开口,小的仍在吸面条。
无耻!我暗暗骂着,甩手便走。
“一!二!三!”
我每迈一步这对父子就记一次数,又好像是我在随他们划一的号令踏步。到底是谁附和谁?我羞愤极了,软倒在滚烫的水泥地上,汗珠泪珠敲击着地面,激起一团团水蒸气,就像老头把滴着血水的鱼丢进烧红的锅里那般的景致……我告诉自己快起来快离开,奈何浑身乏力,身后那阵雄性的哄笑快要将我湮没……“五!六!七!”我不但不能让别人闭嘴,竟也更换不了自己的步调。
“32元!”
老头很严肃地撑开13个手指,跟他们讨价还价,像鸨母一样。
“39元,这可是我出过的最高价了。”
“130元!”老头不肯松口。
大的把屁股从椅子上挪开,拧起老头的衣领,像渴睡的野猫般低吼:“我他妈的不要了。”
老头开始紧张,对着大的背影说:“那就32元吧。”
大的没有回头。
老头软倒在地,“你回来,我贴钱给你,你回来……”
大的终于回转身,嘴角淡淡一扯。老头一手撑地,一手绷直拐杖,哼哧哼哧地蛇形般扭起身子……我冷眼看着这场交易,事不关己似的。
大的走到老头跟前,一把抓起他,拍平他肩头的褶皱,说:“39元。”
老头点点头,哈下腰,猛地把拐杖向大的裤裆处挥去。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的裤裆是那么奇特,神似袋鼠妈妈的育儿袋,包裹着小袋鼠的袋子被红绸缎捆扎成长筒状,绸缎的尾端还吊着一枚古老的铜币。
老头的拐杖继续甩过去,大的既不吱声也不闪避。他太老了,没甩几下,就气喘吁吁地又一屁股坐地,老泪纵横。
“打完了吧……”
我在想大的接下去是不是要说“该轮到我打了”,而这时他迎面快步向我走来,一把拎起我回摊位。经过老头的时候,大的没有扔下钱,只扔下一句:“我给她找个更大的。”我盯着愈来愈小的老人,不哭也不叫,听天由命地闭了眼。
我以为大的会一把把我扔在地上,没想到他只是愣愣地松了手,我的脚尖触地,接着脚掌着地,最后脚跟踏地。我疑惑地睁开眼,看到的竟然是这样一幅景象:一只黢黑的猫缠着小的脖子和肩头,小的两手扯着黑猫打着转拼命挣扎,却怎么都甩不开它。
大的像被点了穴道一般呆立着,我相信小的最终会安全的,因为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死去的事情离我太遥远。就像看电影一样,我静观其变。
可是情况不对了,小的尖叫声低了下去,他带血的喉管暴露在摊位白炽灯热辣的光线下。“出事了!”我冲上去,怕伤着小孩儿,只好拧住黑猫颈后的皮,可它越咬越凶,我狠下心来,双手卡住猫脖子,越掐越紧越掐越紧……我多希望猫赶紧松口,这样我就不用掐碎它的喉骨,那么我的周围就不会有死亡。然后我觉得好笑,这种状况下,要么就是他死,要么就是它死,我别无选择!
不管小的疼不疼,我肆无忌惮地撕扯着黑猫的脖颈……渐渐地,我看到猫脖就像我爱啃的鸡脖一样,里面有好多管子,一根根裂断……一直到最后一根管子断了,猫头终于与身体分离,殷红的血全流在板凳上……
我从丧心病狂里恢复神志,大的仍呆立在原地,我一巴掌甩在他左脸上,一巴掌甩在他右脸上:“把他妈喊来!”
大的转了转眼珠子,顺从地转身走了。我像那个老头一样一屁股坐地,有点疼。
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灵魂。如果人有灵魂,那么动物也应该要有。
今天我弄死了猫,关爱孩子的人们会感激我,甚至会赞我慈悲,那么如果我救的是猫呢?关爱猫的猫和人敢站出来为我说话吗?我完全有更加人道的方式处理猫,而那时候我更多的是借救人的名义进行病态的发泄。有谁能真正明就里?
你疯了吗?
我没疯。
你疯了吗?
我疯了。
说疯了的人是真没疯。
大的带着女人来了,女人在距离我们三四米远便停了脚步,看着我们三个和板凳上的血微笑,我和小的异口同声喊道:“妈!”
我惊异地看着小的,小的惊异地看着我,我问小的:“这是你后妈吗?”
“亲妈!”小的斩钉截铁,猛吸鼻涕的声音真像吸面条。
我心力交瘁,泪从左眼滚出来,“这个场景,即便是几十年之后想起,都会令我伤心不已。”我对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说。
我总是对那些真善美有所怀疑,因其反面才是生命的本源。有些事情,怀疑了、分析了、解剖了、无孔不入了,就灰心了;自嘲了、冷漠了,就刀枪不入了。用客观逻辑去逻辑这些主观情感的结局是什么?自保?报复?沉默?决绝?形而上?
这时候,我尤其想念你,你气我不专心待你,就证明你是专心待我的,那么你是神经病也好,不是神经病也好,你都回头看看,看我朝你的方向跑得多快!耳边的头发被汗液凝成一缕,像利器一样划破空气,原来“呼呼”的风声也可以这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