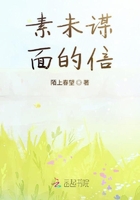七年前的那夜,你说:“不要送,我明天一早就走,我会回来看你。”
你怕看见我哭。我重重地对你点头,答应不去送你。但第二天,我比你更早到了船码头。
我经过神龙庙。庙里跪着村里的老婆婆,她在为她将要远行的儿子祈福。我在庙门外,看着她无比虔诚的背影,嘴里念念有词。我没有走进去。心里有些许感动。
太阳还没升起,海面起着雾。雾使劲抱住渡船。多年后,我怨恨过自己,当初为什么不走进去,跟那老婆婆一样求一求菩萨的保佑?
我站在风里。风从不确定的方向吹来。乱舞的长发打在脸上。身体不自主地战栗。我在害怕。我死盯着渡船不放。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萦绕着我,它将渡你去彼岸。我再也听不到你的箫声,再也不能够为你跳舞。
你从身后抱住我。
“带我走吧!”我在心里喊。你的身体与我一样地在风中颤抖。我知道你听得见。只有你能听得见我心里的呼喊。一转身,我便看见你满脸是泪。
我张开口,我想对你说出那件事。我知道,只要我说出口,你一定能为我留下来,或者带我走,你不会就这样放心地丢下我。
那个早晨,我这样想着。我这样想过,哥哥。但是我还是没有说出口。我没有勇气。
你的母亲,拄着拐杖站在我们身后。她用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瞪着我。她在生气。我知道她不喜欢我,和村里的那些老人一样害怕我。
她的拐杖敲得地面“咚咚”响。她说:“颜禾你快走,别误了船班,你叔叔在那边等你。你要听你叔叔的话。”
是的,你是颜家人。你就得听颜家人的话。你的母亲把你托付给你叔叔,靠你叔叔引你步入光明的正途。
我的话,你不能听。我只会害你。我来这个世上,是来讨债的。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命中注定是要来这世上害人的。
我无力地松手,把你放开。就像雾最终抱不住船一样。
你走向渡船。没有回头。你的双肩在风中颤动,我知道你在哭。你的背影在我眼里渐渐模糊。
突然有一个骇人的景象跃入眼里。你变成了父亲。我被这幻觉一样的念头吓了一大跳。我紧紧抱住双臂。
我不敢回头看,我怕一回头便看见你母亲。如果让她知道我刹那间升起的怪念头,准会用她的拐杖戳死我,诅咒我快点去死。
你上了渡船。我没有等到船开,我无法再站下去。我怕我幻觉一样的预感,和预感一样的幻觉会再次出现。它令我害怕,让我感觉到彻骨的寒意。
我没有回家。我沿着海边从小路上走,去了那块地。你一定知道那块地的。就在我家后面的山坡下。那里有一棵桂花树。是父亲种下的。
每年的桂花时节,父亲会带着我去打桂花。父亲在树上,我在树下。我用尼龙薄膜铺在地上,等父亲用树枝将桂花一批批打下来。
金黄金黄的肉桂,落在尼龙薄膜上,也落满我一身。我故意不换衣服,每次打完桂花,就跑去找你,让你闻我身上的香。
十四岁那年父亲走后,你替代了父亲。你在树上,我在树下。你在打桂花的时候,我就坐在地上一遍一遍地想父亲。我的衣服上、头发上落满你打下来的桂花。你说:“桂花这东西真是怪,越近越闻不到香味。”
我已沐在桂花香里,被你打下的桂花雨淋湿。说这话时,我有点走神。魂在远处游弋。心里很满又很空。就像满树的桂香,你明知它存在的浓郁,却拼了命还是闻不到一样。那种感觉特别怪。
你说,你也很想在院子里种一棵桂花树,推开窗就能闻到香。我说,不用开窗也能闻到,桂花香自己会从窗缝里挤进来。
你笑笑,说你母亲不允许你种。桂花树不能种在院子里,桂花树有树神。到了夜里,你母亲怕一开门便撞见树神。
我慷慨地指着我家的桂花树,说把树分给你一半。你诡秘地笑笑,转头问我:“那树下的东西是不是也分给我一半?”
我羞涩地逃开了,心里灌满喜悦。你知道父亲在树下埋过一坛酒,那酒叫“女儿红”,等我出嫁的那天,挖出来款待客人用。
但那坛酒,却跟我一再擦身而过。它跟我无缘。
哥哥,还记得那一次吗?在那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去山坡下,坐在桂花树下乘凉。你突然说,你想摸摸那坛酒。你的脸微微红着,呼吸变得急促。我偷偷看你一眼,不吭声,心开始激烈地跳。
那晚,我们累得满头大汗,但我们没有挖到那坛酒。我们找不到具体方位。也许我们挖得不够深就放弃了,也许那坛酒已被错综复杂的树根盘踞,我们没有力气再继续往下挖。天已晚,晚饭时间到,母亲的叫唤声,从家里的后门口远远地传过来。
但是那晚,我们一点都没有怀疑过那坛酒的存在。就像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我之间那份爱的存在。
你去地里摘来一大把指甲花。紫红色的小碎花,像一个个闪亮的水晶,你用狗尾巴草把它们串成一串,当项链挂在我脖子上。那晚,我已经是你的新娘。
但是,你走了。我的心坠入深渊。无形的恐惧压着我。没有你的村子,天是灰的,阳光发了霉。
我迫不及待地想逃离那个家。逃离那狭小逼仄的人影憧憧。我要到城里去找你。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你。
也是一个早晨,阳光破雾而出,我登上渡船。我终于登上渡船。那只船它载过你。走进船舱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离你不远。
在岸那边,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来送我。他们在哭。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母亲哭。她的哭,心里装满混乱的情感和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一生下来,她就对我有轻微的仇恨和恐慌。她巴不得我离开。永远不要回家。
其实,我一直是个无家的人。自从你离开我后,我始终在寻找家。但家并不存在。母亲的子宫,也不是家,只是将我降生于世上的一个过渡物,而且即使这样,也还回不去。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来城里找你,其实就是在寻找家。你已是扎根在我心里的不可动摇的家。
我找了你七年。七年的寻找换来一场空。其实也不是空。我总在不远处给自己一个假定,假定你就站在前方,张开双臂等着我。就这样,让自己一程又一程满怀希望地走下去。
“我总算找到你了!”
——这样的幻想,每每惹得我鼻子一酸。仿佛你就站在不远处,等候着我靠近。然后紧紧抱住我,再也不分开。
到杭州后,我没有急着去看莲花。我盼着有一天,你会带我去。我记着你的那句话,你说过你终有一天会带我去看西湖里的莲花。
我在一家廉价的小旅馆里住下来,向旅馆老板娘借来一本这个城市的电话簿,找到所有的建筑单位。逐一打通电话。几天下来,所有的电话都说没有颜禾这个人。我开始按着地址找,打不起出租车,只能挤公交、走路,我在每个建筑公司门口等。我想总有一天,你会从一个大门里突然走出来,走向我……
但是,直到我把身上的钱差不多都花完,再也不能在这个城市存活下去,你还是没有出现。
我已精疲力竭。可我不能回家。我不想就这样放弃。我需要一份工作,我要养活我自己。
我帮人洗碗、擦地、带孩子、卖花、送报、送盒饭……那一段日子里,我已记不清楚,我到底干过多少短工。天天累到喊不动累为止。每时每刻都被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所控制。
但是,我却喜欢上了这份陌生和自由。我发觉在这个城市里,我可以隐藏起所有的历史和过往。不需要戒备,不需要说明,也没有人再会提防我、害怕我。哪怕我真是狐精投胎,也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就是一粒灰尘,可以微小而自由地活。
我一步一步地走着,一天一天地度着光阴,所有的苦与累,都已成为过去。永远过去。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诉苦的人。但每次想起那段日子,我仍然会止不住泪水涟涟,伤心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将我淹没。
哥哥,我没有怨你。也不想恨自己。一切都已过去。我也不想忏悔什么。我只想跟你来说说话。今夜,我是来收脚迹的,为你,也为自己。
那么,请你坐下来,好好看着我,听我说。在我开始回忆这段消失的岁月时,我想象自己也是一只魂。你应该能听见,我曾经疯狂又痴迷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迷失了心,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我自己。
2000年的深秋,西湖里的莲花早已枯萎了。我没时间去看,错过了它的花期。
我在一家叫“万乐迪”的歌厅里做服务员,负责向每个歌厅包房送茶点和酒水。本来,那里的老板是想让我当“歌女”的,陪客人唱歌。
我拒绝了,我说我不会唱歌。
老板说,又不是让你真的唱歌去!
当歌女不去唱歌,去干什么?
当时我真的不明白。
但是现在,我全明白了。我已看透了整个世界。所以,我感觉到冷。
即使此刻,我坐在阁楼的旧藤椅上,依然是冰冷的。这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破旧的电扇,上面积满了灰尘,我没打开。我怕声音扰乱了自己,会感觉不到你。
我还是先套回那件宽大的睡袍吧。我不想让自己裸着身体去展开那一桩桩不堪回首的记忆。那里面夹杂着的不光彩和不体面,也许会让哥哥你忍不住闭上眼睛,皱一下眉的。
让我先来告诉你吧,在这七年的城市生活中,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女子。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了。我只记得这个城市的天气有些凉了,我已添了衣服。
那个夜晚,我和平常一样端着酒水推开一个包房的门。我记得那个门牌号是512。
一个女子裸着上身,五六个醉酒的男人,粗鲁地狂笑着,目光个个淫猥。其中有一个站起身,上前捏了捏那个女子的乳房。嘴里吐出一口烟雾,眼里盛满轻薄之意,说:“这么小,也出来卖!”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阵势。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个男人立即冲着我喊叫,怪怨我酒水送得不及时。
我涨红着脸,极力掩饰内心的惊慌,将酒水送至茶几上。
茶几是玻璃做的,上面溅满了水,很滑。手一抖,一瓶红酒摔跌在地上,酒瓶破了个洞,像一个伤口,往外汩汩地冒着殷红的血。
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在我身上。那些目光都是一样的幸灾乐祸,一样的隔山观火,有一种终于可以找点事出来做做的快乐和轻松。
我不知如何是好地站着,只觉得脸在烧,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那个女子打破了这个局面。她一边穿回衣服,一边开口说话,神情中没有丝毫的慌乱和尴尬,就像是看一场毫不生动的电影片断。
她说:“我已让你们看了,该给我钱了吧?”
有一个男人说,“你太不性感,否则就带你出去,给你双倍的钱。”
那女子也不生气,向他们摊开一只手心。意思是:她只要索取她该得的那一份。
男人给了她两百块钱,然后掉头转向我。一对眼睛在我身体上下求索,似乎想要找到什么答案似的。
他问我:“愿不愿意跟我出去?只要你跟我出去,我不会亏待你!”
我不知道他叫我跟他出去干什么?我已被吓坏了。
我看见正欲离去的那个女子,慢慢回过身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刻在我心里。她很深地看我一眼,然后慢慢走回来,像下了一个决心那样,把两百块钱放在茶几上,轻描淡写地说:“她不是这儿的‘歌女’,酒钱我替她赔给你们。”
她就是虹霞。我要跟你好好说说她。
这七年来,是她帮助我一起找你。然而,又是她,让我们咫尺天涯,永远擦身而过。
那夜,是她替我解了围,把我从刀尖上救下来。她用她裸身赚来的两百块钱买去了我的心。
想来也奇怪,那一瞬间,我感觉她与我离得很近。那种近,有着温暖真实的质感,互相可以交付内心。
就这样,她闯入了我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每当我回忆起和虹霞的初次见面,义无反顾地把所有的情感都向一个陌生人倾泻的时候,我便会想起我父亲。父亲曾对我说过,不要太相信陌生人,就算对身边最亲的人,也不能太相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亲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脸肃穆。肃穆中带着难言的伤痛和悲愤。
父亲为什么会伤痛?他悲愤什么?那时我太小,来不及将一切都弄明白,父亲就撒手走了。
但我在一路行走的过程中,并没有记住父亲的话,或者没有时间去想起。我把父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在“万乐迪”歌厅门口,我曾看见一个背影很像父亲的男人,头发有些乱,衣服一样旧灰。我很想他能够转过身来。就像多年前,父亲站在屋檐下,听到我的脚步声,便会转过身来,朝我露出笑容。那一次,我好像记起过父亲的话,但依然没有放到心里去。
那么多年,我总在想父亲。我知道父亲爱我。我爱的,他也爱。父亲也爱你。他喜欢我跟你在一起。但是父亲的眼光还不够远,他没有看见我们会这样无缘无故地分开,错过一生。如果父亲能预知,他一定不会让我把爱放给你。
如果父亲能够预知,那么,他也一定不会把爱放给母亲。但父亲已经无法回头。母亲是他生命中唯一爱过的女人。但却背叛他一生。
父亲的死,一定和母亲有关。长大后我一直这么认为。虽然我毫无头绪,也找不出证据。但我相信直觉。我相信直觉有时候比任何证据更准确。
我越来越怕那份直觉。有时候心底里的直觉,就是一种预感。我总是能预感到噩运,而不是好运。
是不是噩运特别让人揪心,才会产生出一种更为强烈的感觉?
小时候,我最怕失去父亲。夜里做梦,总是梦见父亲走了,走到我再也寻不着的地方。每次哭醒过来,仍心有余悸。
父亲说,那是因为我太怕失去他,才会做这样的梦。
父亲真的走了。走到我再也寻不着的地方。我觉得我的梦境和预感,是对父亲的诅咒。是我的诅咒让父亲离开了这个人世。
还记得父亲走的那天流鼻血,黑红黑红的,像一抹魂魄,挣扎着从父亲鼻孔里爬出来,告诉我他不放心我。他对不起我。他把我一个人扔在人间。让我从此成为孤儿。
那天父亲的魂已离了身,他一定已看到我身后的局:我命中的男人,注定要一个个地离开我!
如果父亲生前就能预知,我注定在失去他之后,还会失去你。父亲他会不会不死?会不会因为舍不得我,而为我活下来?
渔船未靠近码头,便遭台风袭击。船撞在礁石上,裂了身。跟父亲同船的几个人,都说父亲和他们一样紧抓着缆绳和船板。其实台风并不凶猛,不一会便平息了。人人都抓着船板,慢慢游回了岸。但父亲却没有上岸。有人看见他放了手。父亲让自己在海浪里浮沉。
就算没有缆绳,没有船板,父亲的水性很好,身体结实得像牛,渔船出事的地方离岸不远,父亲怎么也能游回来。但父亲放了手,他没有游回来。
那天把父亲打捞上来的人,对父亲的死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父亲是个水性极好的人,他们不停地摇着头,叹着气,表示他们的惋惜和难以理解。
——我恨父亲!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自己选择了放手。一定是落水的那一瞬间,突然激起了他积郁多年的伤。他知道他的伤口已永远不能愈合。父亲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让伤口永远消失。
那天你抱住我。你说不能这样怀疑父亲。一个人不会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但我感觉到你的身体也在剧烈地抖。
就像此刻,想起父亲不明不白的死,我仍然会止不住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