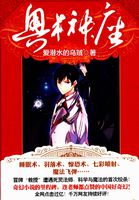我今年已满60岁,按中国的旧式说法,已是“花甲老人”,回顾今生的这一甲子,不胜唏嘘。我们这一辈人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磨难,在前30年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是现在许多年轻人不了解,也是想都想不到的,每当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有那么多的学习与事业发展机会,有那么多的生活乐趣,可以充分体现自我,由衷地感到生活在当今的中国年轻人是100多年来中国最幸福的年轻人。他们现在肯定还是会有许多忧虑,学习、工作、婚姻、购房……但有一样他们是不用担心的,那就是——吃饱肚子。
1959年,我小学毕业,考入了当时的成都第21初级中学,21中位于成电的校门口附近,所以同学大都是成电的教职员工子弟以及东郊企业的子弟。由于从小就生活在大学的围墙里,无忧无虑,不知天下还有疾苦,更不懂世事艰难,但随着我进入初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现在要回顾一下那段历史,50年代自朝鲜战争结束,中国正处于一片欣欣向荣的建设高潮,社会安定,物价稳定,每个人都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当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年轻人都向往考大学,学习工科以建设祖国。1958年,疯狂的运动开始了,那就是——大跃进。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认为靠行政命令、群众运动就能在短期内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提出了要超英(国)赶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有生产资料像土地、牲畜、家具统统归公,农民各家各户都不开伙,集中到公社食堂吃饭,而且不收费,敞开肚皮吃。记得当时学校考试,有一道题是“人民公社有什么好处?”答案之一就有“吃饭不要钱”。庄稼也不种了,去“大炼钢铁”,为什么呢?因为要超英赶美,钢产量那年要达到1800万吨,钢铁厂生产不出,就号召全民炼钢,于是城乡到处建起奇奇怪怪的火炉,把各种铁器砸烂,用木柴与煤企图炼出钢来,炼钢是要用焦炭的,否则温度达不到,怎么能炼出钢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人能说真话,否则就是政治立场问题。记得当时大学生挨家挨户,砸每家的烧饭炉子,取出铁质炉桥(当时没有煤气,各家都烧柴做饭)去炼“钢”,我母亲说,你砸了炉子,我们怎么做饭呢?好在学生们手下留情。可怜的是无数青山、千年古木,顷刻间被砍去炼“钢”,结果是炼出一堆堆无用的铁渣。除了大炼钢铁运动,各地的浮夸风开始盛行,当时有句口号叫“放卫星”(苏联在1957年发射成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鼓舞很大),在城市各企业在“打擂台”(即自报完成产值任务的会议)会上,你报完成工业产值100万,我就报200万,他就报500万,上千万,上亿,就像现在的拍卖会,如果按兵不动不乱报,就是保守、右倾、不相信群众,而农村,原本只产几百斤稻谷的农田,变成了上万斤、10万斤甚至20万斤的亩产量,看谁的卫星放得高,《人民日报》上有张照片,成熟了的稻子,可以托起一个小孩!
而在这种疯狂与愚昧的气氛中,居然还有著名的科学家为了跟上形势,还从什么光合作用、水分含量、土地成分等要素计算亩产万斤是可行的!既然亩产上万斤,公粮上交也就要成倍翻,大炼钢铁及全面铺开的各种浩大基本建设抽走了青壮劳动力,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法收割,加上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农村那点积累哪里经得这么吃!粮食吃完了就吃种粮。到了1959年,全国(大陆地区)性的饥荒爆发了,从乡村到城市,食品的匮乏到了空前的程度,城市每人每月定量只有21斤大米,2两猪肉,所有的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由于票证太多,只有用编号,某号购香烟一包,某号购花椒一两。城市里有点保障凭票供应最基本的粮食,可怜农村在敞开肚皮吃了几天饱饭后,便陷入绝境。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于1959年进入成都第21中,开始我的初中生活。刚进入初中没几个月,我家里又发生了变动,原属高教部管辖的成电在那年被划为由国防科委管理,也就是主要为国防工业服务,我父亲是无线电系(后改为2系)的系主任,家里有众多海外关系。原重用我父亲的院领导又被打成右倾分子,受重用的知识分子一下变成被怀疑的对象,自然不再适于在成电任教。最初通知我父亲调到东北齐齐哈尔一个机电学院,我父亲当时已50多岁又是南方人,到冬季可达零下几十度的地方工作,怎么吃得消,经反映后,上面决定调是一定要调走的,但可换个地方,调到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床厂附属的一个中技校,当时打了个“机电学院”的牌子(也是大跃进的产物)。我父母离开成都,我怎么办?父母考虑到那时德阳的中学教育质量不如成都,决定把我留在成都,继续在21中学习。这就意味着我将离开家庭的呵护,在学校做寄宿生,当年我12岁。父母在离开成都的前一天下午,专门到学校我的寝室看看我睡的高低铺,摸摸我睡的床垫(草垫上铺一床薄棉絮),又找到我的班主任张老师(一名复员军人,人很正派)再三拜托。时隔近半个世纪,父母对我的那份关爱之情,历历在目。
在饥荒年代住校,首当其冲的就是吃不饱,其他同学都有家、有父母照顾,无论如何总要好一点,记得当时每人每月定量为21斤大米,每天为二三三,即早上二两,中午和晚上各三两米饭。现代青年要控制体重,减肥,认为应该够了呀!要知道那时每人每月仅二两猪肉,二两菜油,分摊到30天,每天没有什么油花花,长期下来,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就算某天能猛胀一顿(例如假期回家吃菜稀饭),也只是“胀”的感觉,而没有“饱”的感觉。处于发育期的我更是觉得哪一天有饭能吃饱,那才是天下最大的幸福。当时在学校食堂,是用一搪瓷盆蒸饭,分量够不够,学生也无从知晓,反正饭是软中带稀。蒸好后炊事员用一个竹子做的格子,把饭按成扇形的8份,搭伙的同学8人围成一桌,都是一群小饿鬼,都希望自己那份最大。用钢笔在饭桌上飞转一下,停下来笔头指向谁就成了第一个切饭的人。可以选看上去最大的那份。不但如此,在用竹刀切饭团时把竹刀往两边略带倾斜,这样得到的分量会更大些。第一位切完后,依次类推,可怜的就是最后那个人,他的饭团不但从上看面积最小,而且两边都遭到切割,像一块三角形倒立的西瓜瓣,在盆中几乎都立不稳了。所以,下课铃声一响,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教室,直奔食堂,避免当最后那名倒霉鬼。为此,还受到不少同学嘲笑!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在终日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为了吃什么花样都有。现在想起来都是笑话,当时,不知哪位科学家发明,说是小球藻蛋白质有多少,营养怎么高,可以食用,什么叫小球藻?就是找一个大玻瓶,撒泡尿进去,加上水,在太阳下晒几天,就会有一绿色藻类长出来,把它过滤出来,就是小球藻了,无奈分量太少,像一些绿色粉末,怎么充饥?又提倡什么瓜菜代粮食,甚至用树叶代粮,还开现场会交流。市教育局来了一帮人,学习吃什么呢?把嫩桑树叶用面粉裹上,放到油里去炸熟,当然好吃,但本来就是大饥荒,哪里有面粉与油去炸呢?可见什么现场会造假之风是有传统的。记得有一位老师,在某次打牙祭时啃剩了一块骨头,为了物尽其用,在每次蒸饭时(老师是自己拿米交给食堂代蒸饭)都把那块骨头放在饭上,企图把剩余的油脂再蒸出来。问题是那块骨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利用,变成了一块毫无油气的钙质,终于有一天炊事员忍无可忍,把那块骨头扔出了厨房。
学校为了改善生活,还自己喂了几条猪,但人都吃不饱,哪有什么残羹剩饭给猪吃!可怜那几条猪瘦得像狗一样,几根肋骨都数得清。学校要我们学生去“打猪草”,即外出给猪割青饲料,猪又不是牛,不吃草,只有去农民地里偷几根萝卜回来交差,常常是交一根萝卜给猪吃,自己吃一根填肚子,还要冒被农民追打的危险。
最麻烦是星期天,学校是不开伙的。我就只有自己用一个罐头盒,加点米进去,找点树枝,自己蒸点饭吃,菜是没有的,用家里带的用少许菜油炒的盐撒在饭里当作下饭菜,弄得与小叫花子一样。除了这些,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自己洗衣服、缝被子,现在想起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样过的。
那么当时社会上又是什么状况呢?由于户口制度,农民也不能进城,社会治安也还良好(至少在城里是这样),很少听见有抢劫杀人的恶性事情发生,深更半夜在街上行走也没有人来抢包。最多是在街上边走边吃馒头会给饿得发慌的人抢去而已。我有一次生病在宿舍未去上课,突然溜进一个面带菜色的人,抱了一床同学的被子就走,我追出去,吼一声,你干什么!那人也不跑,把被子往我怀里一塞,连说:“你拿去,你拿去。”想来也是一个饿昏了的人。现在连人民币都有制假的,但那时图案简单的粮票及大量副食品票证,还没有听说有制假的。
由于营养不良,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这种病先是腿部发肿,手在小腿上按一下就会有一个个窝,最后全身浮肿,人就死了,其实治疗很简单,加强营养,吃饱饭就行了,所以药房里有一种叫“康福散”的东西(也不是药)卖,成分就是细米糠、黄豆粉及少许蔗糖,搅成糊糊吃,只不过价格较贵,还要凭医生证明。
那么饭店里卖什么呢?当时所有馆子都为国营,再小的苍蝇馆子也是“区属国营企业”,由区饮食公司管理,卖的是“烩饭”。即一碗用水煮的半稀饭,上面油花可圈可点,要不就是白饭,菜是一点像空心菜之类的青菜,二两一碗,粮票照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四川还出了一个使老百姓雪上加霜的事,即一夜之间突然宣布四川省地方粮票作废(当时粮票分为地方与全国两种),使千省万省而节余了一点粮票的百姓欲哭无泪。可见当时缺粮情况之严重。但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的各级领导,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一些食物配给,如:国家级领导人每户每天保证了一斤猪肉;部长级每月另有4斤猪肉;行政17级—13级的行政干部每月就只有2斤黄豆、1斤白糖了;一般百姓就只有自己设法,如那时新疆、西安地区情况较好,不少人就跑新疆去寻活路,比如我认识的一位乳业界的老板,家里成分不好,当年就从山东跑去新疆,为吃一口饱饭,从做大饼开始,多年奋斗下来,现在已是资产上亿的大老板了。而西安食品供应较成都好,不少成都人来往于成都西安之间做点小生意,但当时也是违法的,称为“投机倒把”。所以,老成都都知道,说某人“跑西安”,就是“投机倒把”之意。记得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商店里有些糖果点心出售,称为“高级糖”及“高级点心”,所谓高级糖只不过是现在都看不到有卖的最次的硬糖,每斤5元钱,几乎是当时一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而高级点心就是加了点糖的面饼。不是一般人所买得起的。
初中岁月,除了饥饿回忆之外,也有许多趣事。记得我们的英文老师是个“右派”分子,学校不准我们叫他“老师”,而只能称作“先生”,但叫“先生”有点别扭(1949年以后大陆已没有某先生称呼,都叫同志),学生直称为“teacher”,这位teacher教书认真,我现在英文还能张口“胡说”,还是那时打的底子。另一位老师当过我们班主任,名为高天寿,学生私下取了外号叫“矮地胖”。不过这位“矮地胖”对学生挺好的,现在也不知还在不在(正是由于这个外号,我才记住40多年前这位老师的名字,其他的都不记得了)放学后,其余同学都回家,为数不多的住校生或是打球,或是到附近小河里游泳。晚上睡觉前讲鬼或是带点色的故事(一般是年纪较大点的学生),要不就唱歌。我记得男生一唱歌,隔壁本来叽叽喳喳的女生寝室便安静下来在偷听呢!肚子虽饿,但一帮初中男生调皮捣蛋的事还不少。我还做了个矿石收音机(现在年轻人不知矿石收音机为何物,即用一块晶体矿,卡一个细针在上面,拨动细针至矿石某点,再外架一个天线,配上一个可变电容器,就可以收到电台的广播了,挺有趣的)。
1962年下半年,当时的成都大学(即现在的西南财大)要办理科,设有物理、化学及数学系,上面又把我父亲从德阳调回至成都任该校物理系主任,这样,我父母又回到成都。同年9月,我又考上成都的三大重点中学之一成都九中读高中,加上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粮食及副食品供应大为改善,结束了我的“小饥民”生活。
所以,几十年来,我从不浪费粮食,最不能容忍员工在食堂倒剩饭,甚至在请客应酬时也希望大家吃完饭菜或是打包带走,这些习惯都是来源于那段艰苦的日子。有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不是“人上人”,也不想做“人上人”,只想平平安安自由自在过一辈子。但吃苦的经历对一个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改一下这句名言:“吃得苦中苦,方为做事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独生子女多,一生下来没吃过苦头,什么事都得顺着他,以后怎么面对这个竞争的社会!我真是担心。
希望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也希望大家事业有成。更庆幸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1959年至1962年的这段经历,永远不会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