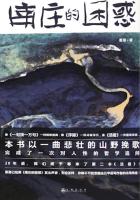那天我在护士站和小黑一起吃着午餐,就问起老李头的病情来。其实老李头没比我早几天入院,而且我和他在确诊这方面的经历还有些相似。
他被他儿子撞了的当天就送到了这里,大概比我要早个两天左右。老李头岁数大了,从前好喝酒好抽烟,又经历这么大的车祸,身体几乎就没剩下什么没毛病的零件了。他最重的伤是在腰上,尾椎骨是碎了,整个脊柱都差点断成了几节,医生说他是运气好才没落下个残废。但好消息还没传到他耳朵里,其它的毛病就又被查了出来。三高,糖尿病,脑血栓,痔疮,前列腺炎,全来了,最要命的还是肺。他老说他胸口又闷又疼,这次才发现是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大拇哥,估计是难得治了。这次车祸还不仅仅是伤了腰杆,似乎大脑的震荡也是不轻,这可能就是他夜里魔怔的原因。
小黑在医院里呆了有一段时间了,可这样麻烦的事情也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大的岁数,身边没个亲人,身体没处好地儿,似乎真是死期将至了。连同我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很难在挺得过来了,现代医学发达,可值得了病,治不了命,阎王爷估计是太想老头了。不过我心里暗自赌气,倒是想和老头比比谁更能熬,或许是我走在他前面也是说不定的。
但是从那以后,我再见老头,总是能感觉到一股辛酸。特别是每天的黄昏,当他那佝偻的身形孤孤单单地立在逐渐变冷的空气中,我就开始想象他感受。恍惚间,我好像成为了他,手用力的扶着凳子背,肺部艰难的呼吸着每一口空气,头脑发胀,双目昏聩,腰杆勉强支撑着身体,肚子一直叽里咕噜的叫着。因为每一次大解都疼痛,所以干脆减少饭量,膀胱肿胀,随时有想要小便的感觉,但杵在马桶旁又只能勉为其难的挤出几滴。从窗户缝里吹进些凉飕飕的风,开始害怕夜晚的到来,当然是自己知道自己到了晚上就无法控制言行,怕被别人当傻子看,但太阳往下掉落和自己疯癫这两件事都太难阻止。窗外的景色算不上怡人,但似乎可以暂时的让人忘记心理和生理的痛苦。盯着马路上一辆又一辆汽车驶过,回忆的潮水势不可挡,从前的苦痛和幸福不由分说的纷至沓来,劈头盖脸的向摇摇欲坠的腰杆压来。儿子,女儿,媳妇,父母,自己,人生匆匆而过,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日益显现,如今死亡就放在面前,自己甚至可以闻见身体里逐渐散发出来的腐臭。偏头望望窗户上映出的自己的模样,陌生又苍老得可怕,记忆中的自己兴许还是一个满身力气又高大的小伙,是什么时候自己变成了这副模样?岁月可真是残忍且毫无同情的心理…
究竟是怎么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是毅力,可以支撑着一个年老的身体依旧要同残忍的现实奋战到底。我实在不能想象。只是看着他的弱小单薄的身躯,我好像可以帮他分担一些不易。
“那精神科的医生对他有鉴定吗?”
我一边嚼着怎么也嚼不烂的一块红烧牛肉,一边抬起头问小黑。这红烧牛肉实在可恶的很,让我简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咀嚼能力。但是没有办法,医院的食堂做菜总是爱耍马虎眼,生怕多煮一会儿牛肉会疼似的。不过说起来方才跟老李头打的也是和我一样的饭菜,不知道他那副化石一般的牙口能否嚼得烂橡胶牛肉。我先前仔细的观察过他的牙齿,一颗一颗好像清末吸了鸦片的民兵,又丑又站不直。这么想来,他应该会选择不去咀嚼牛肉,而是直接吞了,毕竟他是又馋又没耐心。我看了看自己饭盒里的牛肉,大概有大拇指大小,就不知道他吞不吞得下去,可别搞得像《东成西就》里的段王爷吞泥丸一样。
“我还特地去问过精神科的专家。”
小黑回答了我,又把她碗里的清汤鸡夹来给我。
“怎么说?”
“似乎是有毛病的,但具体的…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面露难色。
“这不等于没说吗?还专家,糊弄人呢?”
“也不是,人家也有难处嘛,我也不好跟你说得太明。”
“这啥意思?病人没难处,医生倒是有难处了,总得知道是个啥毛病吧,要不咋治?一到天黑就犯毛病,隔三差五还给你学一个猴子捞月,又不是马戏团出来的。你等着,我去找找那个专家!”
说罢就把饭盒一摆起身要走,却又被小黑拉住。
“你干啥去?找人麻烦?可别。”
“怎么会,你当我医闹啊?我崔某向来都是以理服人的嘛!”
“也是,就你现在这体格,去了怕是也只有吹胡子瞪眼睛的份!”
她就一笑。
“你少看不起人,我军体拳可不是…”
“好了好了,”她把我又拉了坐下,把饭盒提给我,“其实也没啥。就是你刚才说的,要知道是什么病才有的治,问题就在这里。”
“什么意思?”
我问她。
“我们,不想再给他徒增烦恼了,他的病已经够多。”
我那天在外面呆到很晚才回去病房,因为一看见老头,我就心里提不起劲。我在想,即使我身体没啥毛病,可以顺顺利利的活到个七八十岁,但最后的结局不是仍然没有区别吗?人年少的时候话多,想法也变得快,既是快没命了也似乎可以保有一些乐观。但那些年老又命运不济的人,好像有的只是无休无止的忍耐和煎熬,从前的回忆也变得面目狰狞,开始变本加厉的施暴于人。而命运这玩意儿又是无比的难以捉摸,活下去,也就意味着概率不变的风险时刻相随。
那天傍晚,我让小黑搀扶着我,跑去医院门口的餐馆里,狠狠地点了几道硬菜,又悄悄摸摸地顺了一瓶百威啤酒(这个件小黑都不知道),然后兴致勃勃的想给老李头一个惊喜。只是等我回到病房,才发现他已经睡了,十分安静,没有闹腾。他蜷缩在凌乱的病床上,没盖被子,四肢和脑袋又黑又干的露在外面,整个人好像一根被炸糊了的猪肠子。